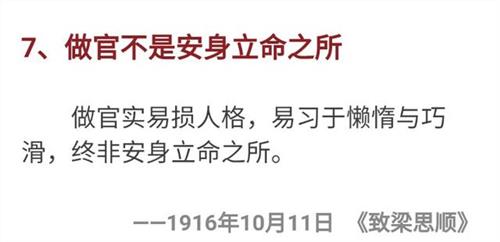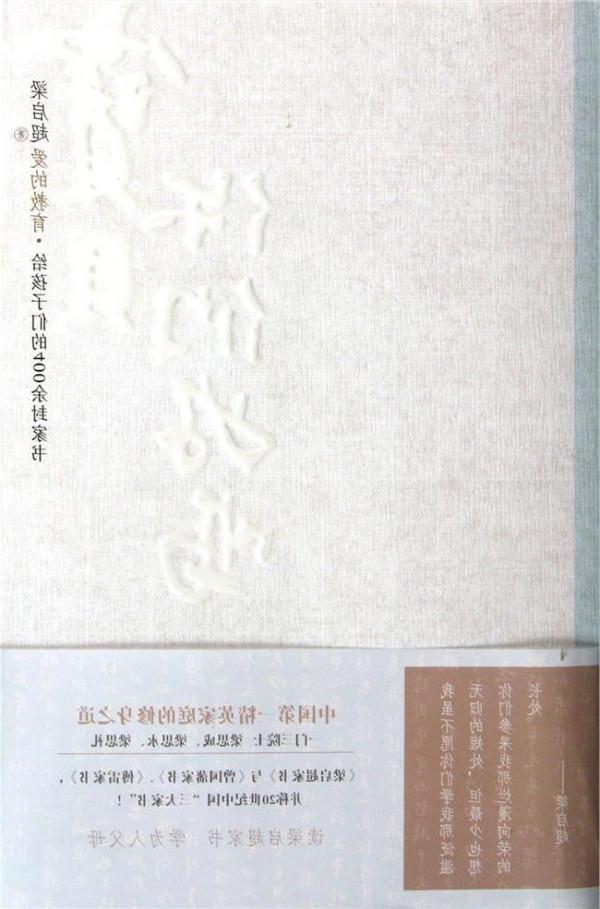梁启超与王桂荃相爱 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1889年9月,十六岁的梁启超在饱读了经史子集之后,踏上了正式的科举之路,参加了三年一次的广东乡试,考中举人第八名。这还不算,更幸运的是,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李端棻(贵州人,字必园,同治癸亥进士,历任云南学政、刑部侍郎)见梁启超品貌才学俱佳,便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这正应了古人的一句话“书中自有颜如玉”。
1891年冬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李蕙仙原籍贵州,1869年(同治八年)生于永定河署。她是京兆公李朝威的幼女,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由于父兄在京城做官,李蕙仙自幼生活在北京,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李蕙仙大梁启超四岁,但属大家闺秀举止端庄、知书达理。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同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
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李蕙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李蕙仙自23岁嫁给梁启超,至56岁病逝,33年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尽心尽责,任劳任怨,成为梁启超的贤内助,事业上的好帮手,被梁启超称为“闺中良友”。
梁启超一生奔走于国事,或忙于著述立说,或忙于四处演讲,与夫人聚少离多,难得有时间顾及家庭。作为妻子,李蕙仙十分理解丈夫,主动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在事业方面,李蕙仙也竭尽全力支持丈夫。
梁启超早年因“家贫无书可读”,李蕙仙便将嫁妆卖了为他购的一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华,与康有为并称,光绪帝久闻其名。
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官话。
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也就得心应手了。“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以十万两银子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及其家人,面对此李蕙仙毫不畏惧,“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率全家老小避难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时李蕙仙便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静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由此可见,梁启超事业上的成功是与李蕙仙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在梁启超的身后站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她默默地用她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梁启超这棵时代的参天大树。
对于夫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梁启超感激不尽,认为他俩是“美满婚姻,百年相爱”。梁启超与李蕙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蕙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乳癌),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向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癌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千古名文——《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今我失君,双影彷徨。”
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由日本横滨乘船,赴美国檀香山。他此行是受保皇派委托,为“武装勤王”筹款,并发展自己的组织。梁启超在檀香山的那段岁月,却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夏威夷之恋”。
檀香山当地有一侨商女儿,叫何蕙珍,芳龄20,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四年,英文极好,主动担任梁启超的英文翻译。一日,何家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并邀请了美国名士当地名流数十人作陪。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少女特有的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
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一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
梁启超心中不服,却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如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显然梁启超此时已意乱情迷、坠入情网,几近痴迷。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作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哉?”梁启超的此番话可谓振振有辞,金石之音。
又过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方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
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
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叙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吟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蕙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蕙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蕙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
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此时已全然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
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再后来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再次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不近人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1924年,51岁的梁启超开始撰写中国诗歌发展史。然而此时夫人李蕙仙患乳腺癌,病势沉重,梁启超不得不停止写作。半年后,即1924年9月李蕙仙去世。李蕙仙病故后梁启超的生活主要依靠小妾王桂荃照顾。
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曾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
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的几乎所有孩子都对王桂荃的感情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鸡毛掸子捆上铁丝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1968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