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多言的政府 许纪霖:有原则地拥护政府的傅斯年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作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
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的后半生,几乎大半的精力都在与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搏斗。
陈沧波将这场斗争,形容为“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士大夫阶级没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识,天然与既得利益者势不两立。傅斯年,很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
豪杰气背后必要有凭籍,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籍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籍,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
到二十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是凭籍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新的知识道统,到二十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离开了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
这位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为:“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
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负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责任,那就只有以知识为凭籍,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了。到40年代,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动脑筋,要把他请他政府里面。
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爱国名士,还不是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还力阻胡适误入候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
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并非权宜之计,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有关。他相信,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发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永远在野,这也是豪杰气,这样的豪杰气,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性格,很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因为是国民党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对这个党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开首,就深有感触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他认定,国民党堕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于孔宋这样的腐败势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请孔宋走开,肃清既得利益。他以绝然的口吻说:“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
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拥有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没有像时下中国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将自由主义理解为“自由竞争”、“财产自由”、“发展至上”等几条向权势者或新富翁献媚的市场教条,他对欧洲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反思,认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因为与资本主义结合,一切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变质了。
“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四大自由”的罗斯福新政,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
他有一段名言,特别反映了内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中国是一个既无自由也无公平的国家,偏偏又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无法抛弃它、离开它,只有为了心中的理想去呐喊和奋斗。他对孔宋这样的误国势力恨到了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不惜豁出只身,与之搏斗。
同样为亲政府的自由主义,傅斯年与胡适是有点区别的。在20年代末,当胡适为人权呼喊的时候,傅斯年倒是埋首于象牙塔中远离尘世。到40年代末,两个人似乎倒了个位置:胡适越来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趋激进亢奋。傅斯年曾经说过:“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
程沧波也这样评论,如果说胡适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斯年就是“急进的自由主义者”。傅斯年主张“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但胡适却不甚赞同,他回复傅斯年说:“我的Anglo-Saxon训练决不容许我作此见解。
若从老兄所主张的‘法治’观点看是决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续,则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产党的‘清算’了。”至于对国民党和蒋的看法,胡适也自认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较国内朋友客观、宽恕,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
胡适未免天真、自信了一点,在这方面,还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蒋表面诚恳,实质是只懂压力,不知其它,特别是美国人的压力。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抗战爆发以后,蒋礼贤下士,常常召见傅斯年垂询国事,他成为最高领袖厅里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并不因此而膝盖骨发软,大唱“英明领袖”的颂歌。纵然皇恩浩荡,依然一身豪气,大施压力。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舞弊贪污,全场为之轰动。会后,蒋介石亲自请傅斯年吃饭,为孔说情。席间有这样一段精采对话: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得任,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国民党内士大夫阶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这场搏斗,说到底只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悲剧。政治的体制不变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纵然孔宋被赶下台,还会有新的腐败势力孳生出来。在这方面,傅斯年未免士大夫了一点。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
”他真的那么自信?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杰气,一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
这样的豪杰气,纵然于世无补,却弥足珍贵。它象征着在一个浑诨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不过,它在中国失传实在太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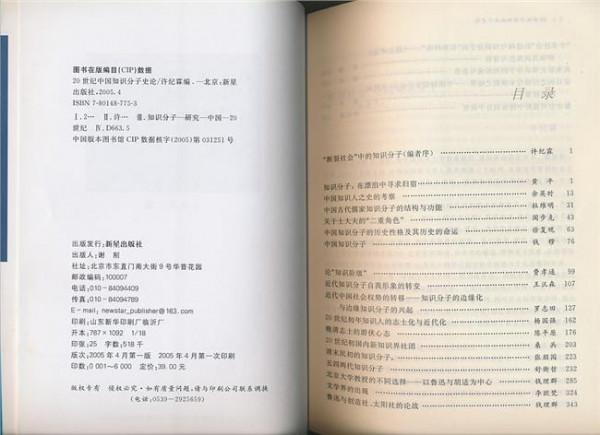






![>许纪霖辛亥革命 [讲坛]重温百年辛亥革命 许纪霖:新政是革命温床](https://pic.bilezu.com/upload/9/a0/9a03da4be1ce43d859a579f6432d4b78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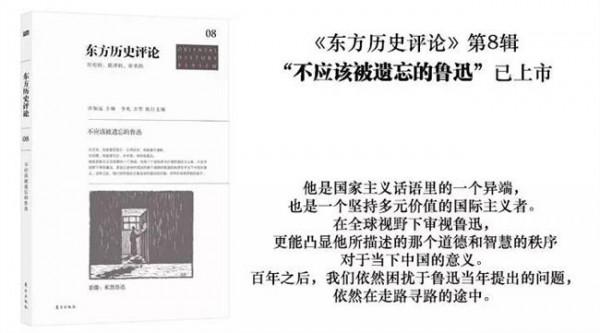



![>许纪霖反毛 [讲坛]精英等于贵族? 许纪霖:反思中西方大学教育](https://pic.bilezu.com/upload/0/f9/0f981c99e378d5a456dbcc465fadd5e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