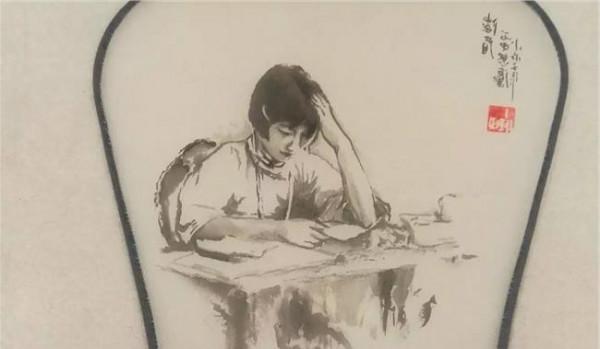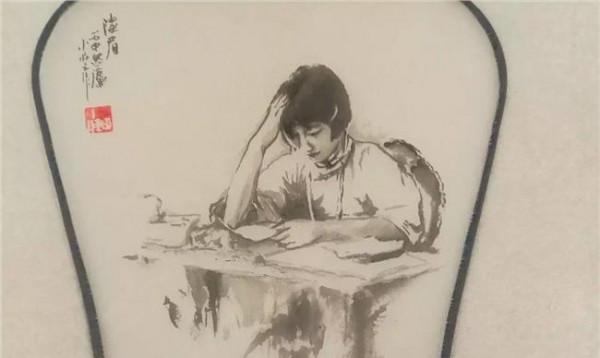凌叔华酒后 婉顺女性的写照——从凌叔华的《酒后》谈起
《花之寺》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她在当时创作的12部短篇小说。其作品大多是以细腻幽雅的笔触刻画高门巨族及中产阶级人家中婉顺女性的枯寂和忧郁的灵魂。提起她,一个不可不说的关键词就是“婉顺”。
这两个字,是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说的:“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 大抵是很谨慎的, 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 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 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
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 也就是世态的一角, 高门巨族的精魂。” 将“间有出轨”和“文酒之风”联系起来,我们不难想到她在1924年发表的成名作《酒后》。
在一次小型的家庭宴会之后,夫妻俩的朋友子仪在沙发上醉卧不醒,夫妻俩在火炉边细语密谈。在酒后的丈夫永璋眼里,小家庭的一切在这一刻都是那么的温馨甜美。于是,他拉着妻子采苕的手,不住地用华美的词句来赞美她。
可妻子却对丈夫的话充耳不闻,而是一直关注着醉卧的子仪,最后,竟向丈夫提出了吻一下子仪的请求。就是这样一个情节简单而又看似荒谬的短篇故事,其中却蕴藏了作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对女性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冷静而平直的叙事 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总体上显得较为稚嫩。
从叙述视角的角度来看,五四女作家中的大多数,如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和苏雪林等,都是以一种自传体或准自传体进行小说创作的。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采用,在她们的小说中占了较大比例。 而凌叔华在叙述视角的运用上,显示出了与其他五四女作家十分不同的路径。她直接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尤其是受到了契诃夫小说中客观化叙事风格的影响,选用了在限制视野的处理上比第一人称更有难度的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
在她的小说中存在一个“叙述者”,只冷静地记录人物的言论,描写人物外部动作,而不作主观的评价,不分析人物的心理。
这种叙述方式的采用,使凌叔华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近乎于冷漠的叙事风格,同时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空间用来思索和回味。“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地观察,平淡地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沈从文)。
这种风格在日本近现代小说中也是很常见的。曾经有译者说,日本小说中最难翻译的就是人的对话,不带主语也没有问号叹号,完全不知道应该是以何种语气说出口的。
在《酒后》一文中,我们虽然清楚的知道夫妻两人对话的内容,但对于其说话的目的与其内心的活动却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他真可怜!……亲爱的,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
” “哦!所以你要去Kiss 他,采苕?” “唔,也因为刚才我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她紧紧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应我。
” 永璋面上现出很为难态度,仍含笑答道: “采苕,你另想一个要求可以吗?我不能答应你……” 采苕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他的话道: “我信你是最爱我的,为什么竟不能应允我这要求?……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
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的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永璋连忙分说。 这几句对话是全文的高潮,我们看到的仿佛是夫妻两人平常似的交谈,但事实上两人的内心都是在激烈的矛盾着。
就是这种严格限于人物视角的客观的场面描写,看不到任何作家的主观评价和感情流露,使凌叔华的小说像一幅淡墨留白的山水画,其画中之意还需读者自行体会。
冲和而哀愁的笔触 日本文学从俳句开始便有“物哀”的传统,指对所感之对象表现一种爱怜和同情混成的心绪。
所以我们现在读日本的小说,总会觉得其中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凌叔华的小说中也有这样的一股淡淡的哀愁在弥散着,那是她对于中国传统女性命运深切的悲悯。
而同时,她又仿佛置身事外,不关己事一般,显得异常的平静。因此,这哀愁只是“淡淡的”,而不会过分地浓稠激烈。 凌叔华的笔触平淡冲和,却又回转细腻,余韵绵长,似涓涓细流一般润泽流经的土地。
她通过氛围的营造来构成叙事的情调模式。小说淡淡的叙事所营造的情调与氛围, 把我们带进一种寂寞、悲凉、感伤、苦闷的情绪之中。就连小说的情节都被浓郁的主观情绪淹没了, 从而情绪成为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被强调和突出。
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
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象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苕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 在叔华的笔下,采苕当着丈夫的面欣赏男性朋友的做法竟显得如此美好而合理。
叔华正是在女性狭小的世界中,用笔触去勘测着她们心灵与情感的深处。 与男性的世界相比较而言, 女性的生活是一种平淡的生活, 不参与社会的冲突, 这是由女性的社会角色决定的, 没有剧烈的外部矛盾, 复杂的人事关系, 她们的冲突是隐性的, 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感受着喜怒哀乐。
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的女性是真的、善的、美的,可她们一旦步入了婚姻的围城,便依然如笼中之鸟一般被束缚了。
她们诚然拥有独立思想,渴望自由,可也只能将才华施展于家庭之中,少被外人所知。而即使是家人,是丈夫,也只是欣赏她们作为温婉的妻子这一面罢了。凌叔华以和缓的叙事节奏,“描绘了社会大背景的屏风背后, 有着无限闺怨、焦困的女性世界”。
温和的幽默与反讽 “世界在她是狭窄的, 家庭在她却是最宽广的。
”(苏雪林)看似平淡的家庭生活,二人世界,在凌叔华笔下却总能够演绎出新的内容,让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却又陷入沉思。
凌叔华的小说,尤其是这篇《酒后》与其另一篇代表作《花之寺》,都较为巧妙地运用了幽默的笔触,婉转地讽刺了现代婚姻中的自由与“出轨”问题。 《酒后》中的反讽,主要是建立在丈夫的自我感觉与妻子的情感动向之间的相互错位之上的。
由丈夫视角展开的第三人称叙述,使文本只能表述丈夫所看到的表象,而不能深入妻子的内心。这样,当妻子终于说出倾慕子仪的心事之时,就使丈夫此前所有的“艳福独享”的良好感觉,顿时变成了纯粹的自鸣得意,而小说对男性以自我中心的自大与自误的调侃与反讽便由此形成了。
在《酒后》和《花之寺》中,小说文本所设置的反讽都指向了婚姻中的男性,对他们自命风流的见异思迁、男性中心式的情感自大予以了女性的调侃与嘲讽。
不过,这样的调侃与嘲讽并不会过于尖锐而使读者难以接受,而是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的。正如其好友徐志摩的评价:“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 而这也反映出了凌叔华对新式婚姻中男女情感问题的探寻。与传统包办婚姻相比,新式婚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基于男女情感的自由选择。凌叔华正是抓住了新式婚姻的这一本质,并进一步质疑:既然新式婚姻是建立在男女双方情感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一情感选择的自由在婚后是否应继续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否应有一个限度?又应是怎样的限度?这样的质疑,已经使凌叔华的婚姻书写直接切入了现代婚姻的根本性问题。
这涉及一个悖谬:现代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也正是它瓦解的隐患。而反讽,正是表现悖谬的最佳方式。 采苕渴望的那一吻,显然超出了当时异性朋友的交往界限, 并且还当着丈夫的面, 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一吻的纯洁性。
采苕的大胆正体现了当时女性个性的张扬。而丈夫在迟疑后,果断地应允了, 也看出丈夫对妻子的理解, 夫妻间的相互信任。但当采苕真的走到子仪面前时, 却由面热心跳转为平静, 放弃了自己的初衷。
最终采苕的个性张扬让位于潜意识中的传统理念。 五四时期毕竟还是一个转型、过渡的时代,完全的新与纯粹的旧都不能作为时代的典型画像,半新半旧才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生存状态。
凌叔华笔下的知识女性, 虽然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但现实的环境却不允许她们在行动上有所前进, 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凌叔华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女子真实的心灵写照,同时也为研究那个时代妇女的解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却依旧矛盾而困惑,无可奈何,作品中“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徐徐地叙述当时妇女的苦闷与无奈。在男女平等进一步得到认可,女子在社会上取得更多权利的今天,我们再来读叔华的小说,宛若重拾朝花,淡淡的幽怨之情仍旧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