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顺的师傅 孟祥顺:画家是画出来的
是黄润华先生带我去拜见了李可染先生。在李先生家里挂着一幅他自己的书法"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时至今日我还对这八个大字记忆犹新。在北京闯荡的近十年来,这八个字一直影响着我。
我家乡在小兴安岭。我是生在雪地里头的,母亲早产。我父亲的祖藉在山东,后来逃难到了关外。我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叫长胜屯,走几步就是大山、林海、雪原。这里有许多人以打猎为生。猎户家里挂着虎皮、豹皮、熊皮、狼皮……。这对于我可能正是视觉审美上的启蒙。
我们村有个民间艺人也会画老虎,我就跟他学过。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宣纸,什么叫毛笔,什么叫研的墨,没有。就用写大字报的墨水,还有,把锅底的灰括下来,研一研,然后再加点胶——猪皮胶。就这么画了。颜色当地有水彩色,还有粉笔。那时画了不少,当然也画老虎。记得还画了一套连环画"林海雪源"。
我爷爷是晚清的秀才,叫孟庆君但我没见过,只是留下了几件作品,梅兰竹菊,还有印章。当时听我母亲讲,爷爷的图章是自己刻的。我母亲反对我画画,为什么要反对呢?是因为我爷爷画画,诗、书、画、唱、弹都会,玩高雅,所以他不管这个家呀。辽宁千山有不少寺院,"龙泉寺"到现在还有我爷爷题的匾。
那是我正读三年级,十一岁的时候,村子里有户人家老有人生病,我们的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人不算多,但是巫婆倒有好几个。所以这家人就请了巫婆来看病,那巫婆作法之后说,是隔壁人家的房子出了问题,得驱妖避邪!怎么个驱妖避邪呢?就是得画个关公或老虎之类的,再朝着那个方向一挂,这样就能驱灾避邪了。
当时他们找不到这个画虎的人,结果就找到我了,求我说,你画一个看看。我妈说,那你就画吧。我就画了一张,还用我妈糊窗户的浆糊把它裱了一下。
这个画挂上以后,果然出现"奇迹",老人的病好了,孩子的病也好了。其实他们是饿了,吃了那个"灰菜",中毒。后来就传开了,说我画的老虎能避邪,传为村里的佳话。后来,我自己也画了好多老虎,什么上山虎下山虎,四条幅。画到什么时候呢,大概画到文革的中期。再到后来就是"搞创作"了。
我十六岁参加工作,在当地煤矿,从农村到了市区。我成了采煤工人,经过我艰苦的努力,摸爬滚打在井下,再加上我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挺深,不长时间就提干。当时,煤矿上的广播里这么说我:战地报道,孟祥顺战斗在火线,七天七夜不回家,轻伤不哭重伤不下火线。
还有挖地道,"深挖洞广积粮",我都有过战绩。那时候年轻,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诲,所以非常勇猛、能干。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就当上了工会宣传干部,然后当工会主席,当宣传部长,相当于副处级。
八几年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官场上我还不是个强手,屡屡受挫,该提不提起来,而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受到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忽然今年需要年轻干部(王洪文的时候),"四人帮"打倒,老干部上去以后忽然又说年轻干部不行,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也是当时中央的大气候。
那时候,我就稍微留个小胡子。后来又说到四十五岁的一刀切,下去。我就觉得不行,太累。这时我已三十多岁了,就确定辞官不做。所谓做官也仍在画画,搞宣传的嘛。我画过二十多米长的大型壁画,当然是临摹的。一个头像都两米高。
辞官之后,我就下海了,第一站去了海南岛,给台湾老板的广告装饰公司打工,不到一个月,由于我的才能出色,就成了他的副手,做副总经理。干了一年,公司挣了四百多万。但是我们俩的政治观点经常不一致。他受的是台湾国民党的教育,我受的是大陆共产党的教育。
做工作我可以听你的,我一个人超过了三四个人的工作量,个人的战斗力特强,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就睡了四个小时的觉,这样老板会不喜欢我吗?!我们俩各自的政治观点都转不过弯来,他说国民党怎么怎么好,蒋介石怎么怎么好,或者是国民党抗日死了死了多少,说大陆的"上山下乡",死了多少多少人。
我说你根本不知道大陆怎么回事,我说我就下过乡,我的三个姐姐都下过乡。我说你说得不对。在政治上我们俩天天争得面红脸赤。
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实力还行,觉得可以自己发展,我就写了个辞职报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的父母年事已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古人说:父母在,儿不远游嘛。回来以后,还是重新开始,我决定还是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广告装璜我也不愿意搞了,因为我己搞得厌倦。
干脆我还重操旧业,还是拿起我的画笔画画吧。画什么呢?这时我是受到华山川的影响,我是在书店里见到华山川的一个画册,山鬼与老虎。后来,当然还受到过刘继卣、冯大中的影响,但我一直不认识冯大中。
我就试验我还能不能画老虎,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我觉得画的还挺好。但是我又不愿意走别人的路,走华山川的路?走张善子的路?那又怎么办,对商场我又不能不顾及,因为我需要生活。
正经八百开始画老虎应该是1992年。我来到北京,找原来上学时的老师,看能不能给我指指路,在北京发展。所有的老师我都挨个去看了一看,想求他们给我指点指点迷经。可是他们都劝我回去吧,北京特别难闯,在北京你无法生存,你还是当你的官去吧。
他们对我泼冷水,泄我的气。我对几个老师尊敬是尊敬,但是我听着以后,很不舒服。从那天开始,我要立志,于是租房子,就在大兴县,郊区便宜。开始画画,画老虎,我谁也没靠,自己画,但是我走的路很正。
那时嘉德、太平洋的第二场拍卖会,我赶上了。当时我手里有李可染给我的字,给我的画,李行简、贾又福、姚有多等人在我上学时送给我的画,当时手上有三十多张。那时候,我当点小官,工会有奖金,常会发一些什么背心、裤衩,什么枕巾、被单,我把这些送给画家,然后他们送我画,那时候画不值钱。
我就是跟拍卖行说,我有这么多画,能不能拍卖?当时嘉德管书画的赵宜明、刘凯,我到现在还挺感激他们。是他们让我的作品在嘉德上拍的,他们说:李可染、周思聪的东西还可以,别人的就不要了,你的我要,你的很有特点,可以试着拍拍。
然后就拿去拍了,当时我坐在后面,什么托、举,这些市场运作我都不会的。只觉得心情紧张,叫到一百五十多号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开始在跳了,血压升高,当拍卖师说,接下来是一百六十三号孟祥顺《双雄图》,起价一千元,哪位先生跟价?开始!
就叭叭……一千,一千,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五,一千五,一千八,一千八,二千,二千,二千二,二千二,二千五,二千五,二千八,二千八,就在这个阶梯上升的时候,我的心都崩了。
我还从来没卖过这么高的价钱。我还知道了,我的画能卖钱,简直就是神了。一直拍到三千八,成交!
这位先生买到了,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说句实话,真是特别激动。我激动什么呢?我看到了我自身的艺术价值。同时我也知道我的生活有出路了,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拼搏有交代了,在北京可以呆,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我特别感谢原嘉德的赵宜明先生、刘凯先生。我的画能卖钱了,而且卖得很高,甚至当时有很多名家,我就不说具体是谁了,有许多我崇拜的名家,竟然流拍、竟然一千多元都不值,我的竟然三千八。这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就给家里打电话,全家上下都欢喜,我说我决定在北京发展。
一个人在北京,经常吃方便面,一箱一箱地吃,吃了就画。画了再睡……我还不想失去很多朋友,白天画画,晚上还跟同学老师聚一聚、聊一聊。
从此以后我画完了就送去拍卖行卖,越卖越高,越卖越高,从三千八的阶梯开始,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高,一直卖到今天,最高的一张是八万,这是拍卖会上的价格。当然,拍卖会之外个别成交,有过十几万,十八万,邯郸的一位先生买下,还有一个王先生二十二万买下。
我觉得画家的成长,成功,不是评论家评论出来的,是画出来的,是奋斗出来的。
我特别注重市场,因为你的画卖不出去,也是很悲哀的事情!一个艺术家市场不认可你,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我是清高,我是行为艺术,……是!是有趣味,你可以搁在家里自己欣赏,你可以自我陶醉,都可以!
但是人民大众不行,我呢,迎合了大众,这是我的独到之处。我能走到今天,有人说是打出了一个擦边球,走出了自己的路。有人还说我是当今绘画市场的"孟祥顺现象"。这确定有点离奇:第一,《美术》杂志上我还没有登过东西,全国大展我也只是得了几次奖,而那些获奖的专业户多了,可是他们到了市场,到了山东,到了广东,到了河北,到了大连,到了东北,到了北京,还卖不上价。
当然不是说他们的东西不好。有的画家画的也确实很好,——这一点我清醒得很。
我也到处讲,包括画虎的同行,包括画人物画山水的,我都说他们比我强。可是他们没有被社会认可。我让社会认可了,那么呢,我是个幸运者,我不说我是成功者,别人可以说我是成功者,但是我是幸运者;第二,在北京这个文化大都市里,发展机遇很多,人为的机遇,天赐的机遇,我都把握住了,这也是我的综合实力。
有的画家呢,闷在家里头自己画画玩清高,与世隔绝,觉得好象学古人的那一套,隐居山林一样,但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信息时代,市场时代,我见到过很多清高的画家,他们动辄就说:我不卖画,我的画怎么怎么,不是卖的,我的画是学,做学问。
但到头来,别人的画起来了,画价也起来了,能开上车了,能住上别墅了,他呢,后悔来不及了。
有一次,我介绍一个买家到一个教授家去买画,结果这个买家不相信,这么一个有名的教授竟然还住在一个六、七十年代分的房子里,没有钱,买不起房。就因为他的画没有被社会认可没有被收藏家认可,虽然有二、三十年教授的名。
我为他悲哀,我不愿做这样的画家。有人说画家史国良,电视台,什么所有的刊物,都占,那么为什么不占?!在这个信息时代画画得好,为什么不占?如果是我,我也占。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上。上比不上就是好,但不要太过。要把握住度。
在许多评论家与画家的文字里,都不愿意提到"市场"二个字,"买画"两个字,我这次恰恰在简列里专门列出表来。何年何月,卖了哪张作品,卖了多少钱。我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个这么做。别的画家总是详细列出什么什么展览,却从不敢说出他的画卖了多少,卖的是多少钱。许多人回避"市场"与"钱"的问题,我就恰恰要正视这个问题。我就不怕别人说我"俗"。
最近的一次大展,我送了二件作品。一张大虎头,在市场上肯定卖高价的,但却落选了。另一张叫《岁月开怀》,画一个老红军。也像虎头那么大(丈二匹对开),顶天立地,就一个人头,写实的,背景是大泼墨。这一张反倒入选了。我画的这个头像,是普普通通的东北人,也不戴头巾,也不戴这个也不戴那个的,是我写生过来的。
我喜欢画大画。小情调也能画,但就是不喜欢。我开始的时候是被瞧不起的,学历也不是本科生,而是进修生。后来通过实践我成功了,才有人反过来请我吃饭了,原来我请他们吃饭还不给我机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的综合实力增强了,市场、媒体认同我了,人家就瞧得起你了。
所以我就悟出一个真理:自强,多挣钱、多卖画。挣到钱的时候,别忘了画画,别忘了自己的想法。不能盲目地赚钱,我开始思考这个市场了。如果再拍的话,嘉德上什么,翰海上什么,都要考虑好。
下一步我要画自己喜欢的画。原来是没办法为生活,要画别人喜欢的画。再以后可能还想画一些不必考虑市场随心所欲的画,当然现在还没到这个境界。而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的文化底蕴比较浅,我没上过大学,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初中。
只恨自己学问浅,书也看得少。只好笨鸟勤飞,再慢慢学吧。空谈理论,谈古论今,谈学院派,谈艺术,这个我也谈不好,你让我画画行,你让我谈理论我谈不好。当然画家最终还得通过画来说话。
让画来感染人、打动人。关键还是画,大师不是你得来的,也不是你抢来的,而是别人认你的。卖画的价格也是一样,你硬说我的画要多少多少钱也不行呀。这画得值十万,给我吧,人家给你吗?这得人家自愿,喜欢你作品的时候才给你。作为一个搞理论搞研究搞评论的人,不能只局限于他们自己个人的喜好上,而是应该面对事实,从全方位广泛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市场你不走我不走,哪谁去走。你不走可以,却不能不让别人去走。
我不回避市场,我不学过去那些画家,穷困潦倒,假清高。画家的画就要给人看,就要卖,就要走向市场,就要走向大众,就要有价位。价位也是衡量艺术水准的一个因素嘛。这么多画家包括大师,我很少看到不要钱的不喜欢钱的画家。
只有范曾先生、冯远先生我看到过,就是不画自己不想画的,别人给再多的钱也不画。别的大多数画家,只要拿钱去了,还不是眉开眼笑的。不要玩假的要玩真的,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人看。不要表面做一套心里想另一套,没有意思,我就是我。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画画也一样,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怕人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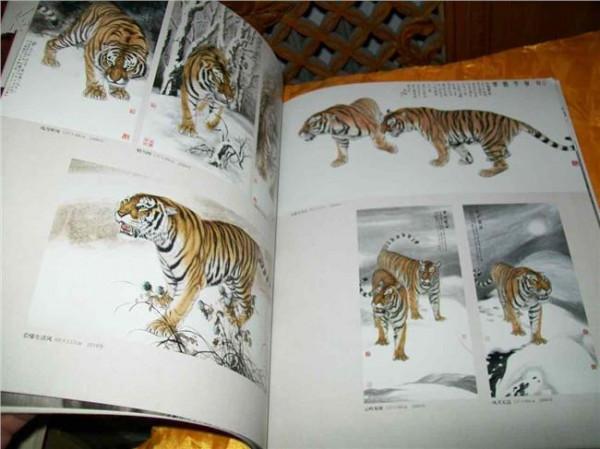










![孟祥斌照片 义无反顾:孟祥斌[组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c/c2/cc277f084c876a03e4ddc1f8525b2b6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