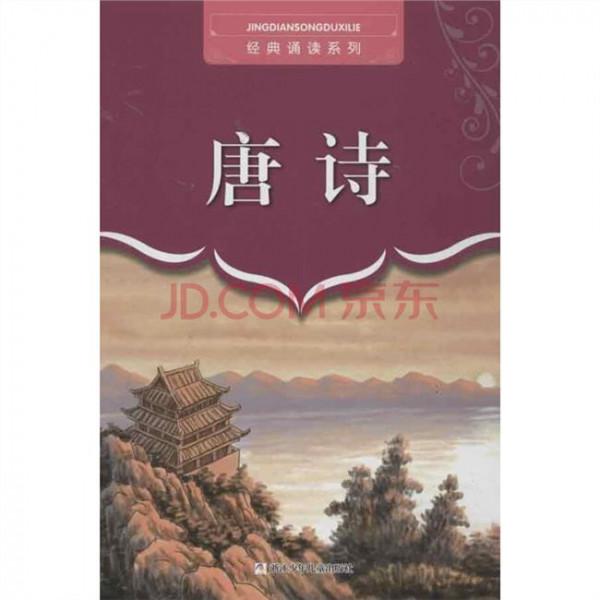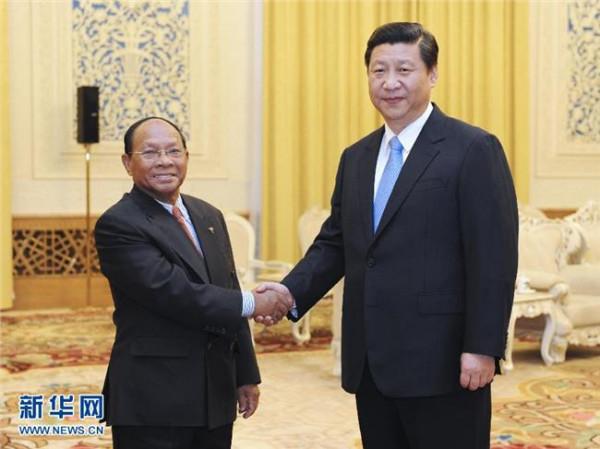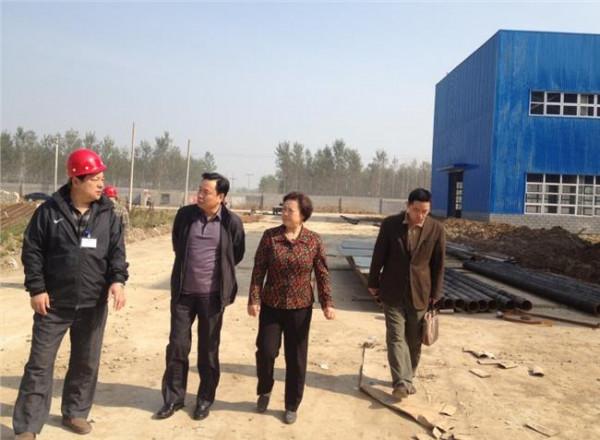傅璇琮唐诗 罗宗强:舍易就难舍热就冷——谈傅璇琮《唐诗学论稿》
序》中有深刻的论述,他说:“研究历史,一个不可缺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
”“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璇琮先生的研究正是走着这样的路。但是博通更难。博通不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而且需要有一种整体审视历史的能力。
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错综纠结、黯晦不明中看到症结所在,看到真相。璇琮先生的著作说明他是走着博通这条路的。我以为,璇琮先生以其精深与博通从事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已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里,文史本来不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搞文学研究的人只注意文学自身,对于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波荡,宗教与哲学的情形,社会的心态,与不同地域的风情等等不予理睬。而不顾及这些,事实上便也撇开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无法理解与解释文学的不同特点。
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承接文史不分的传统,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审视文学的特质,我以为是一种很好的治学途径,璇琮先生的成就就是很好的证明。
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大发展,但也曾经被彻底否定;同时,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也反复被讨论过,意见纷纷。这里提到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当然不会是大家都认可的最佳途径。
细想起来,自古以来关于治学的目的与方法似乎就未曾有过统一的认识。大略说来,每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社会风云激荡之际,志士奋起,治学的目的往往重在为时所用,略其小而取其大;而当社会相对稳定或者停滞时,则治学者常常更带着纯学术的色彩。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身处同一时代,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不同。当然这只是大略而言的。但由这大略的差别,也就生出来治学方法的不同,有种种的争论,有种种的是非褒贬。
我想,这种种的争论,种种的是非褒贬,是会还要永远继续下去的吧!对于学术的发展,对于民族文化的承传,种种不同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目的的是非功过,恐怕是只好留给历史去评说的。
但是有一点,不论何种的目的与方法,欲成大气候者,我以为有一点是必备的,那就是求实。虚荒浮躁者,虽可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费些小力气而获浮名于一时,但时光流逝,销声匿迹亦随之。求实则较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血汗较比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求实也真不易,需要有一种为学术献身、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与决心。璇琮先生为汝煜兄的著作写的两篇序言,真是使我感慨万千。汝煜兄就是璇琮先生所称赞的脚踏实地做学问的那种人,现在他已经过早地去世了!
青灯摊书,在贫困中匆匆度过一生,正是许多献身于学术的有志之士的归宿。去年去世的郭在贻兄,也是这样的一位。他逝世之后,每当我重读他的数十封来信时,便会怆然想起他墓志上的话:“卅载清贫,二子尚幼,可不痛哉!
”上天真也不公,浮猾钻营而富贵寿高者往往有之;而勤谨耕耘者,却常常贫寒困顿、英年早逝。季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后如何,本与己无干;生前艰辛,却确实需要有一番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而学术,也就在这种献身精神中得到发展。同时这种献身精神自身,也常常给献身者以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视艰难的学术之旅如歌如诗,虽鞠躬劳瘁而始终如醉如痴。傅璇琮先生年来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提倡一种求实的学风,我觉得这于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助益的。
他也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奖掖后进,激励同志;在唐文学的研究中作了广泛的组织工作,这同样于学术的发展大有助益。这两个方面,没有阔大的胸襟与学术的识力,是做不到的。
就以《唐才子传》来说,这样一部价值甚大而又问题甚多的书,从事唐文学研究的人离不开,而使用起来又须处处小心,实在非常需要对它来一番认真的清理。而这样大的工程,一个人的力量短期不容易做好。傅先生便组织同志,校笺这部书。
从我读到的已经出版的两册看,在国内外对此书的研究中,都是最好的。这类组织工作,对唐文学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帮助甚大。我们的学术界,近年来组织了许多巨大的古籍整理的工程,千秋事业,功留后世!
有许多学人为此默默奉献了自己的精力,令人钦仰。大约七八年前,有学者组织了相当多的人力,编写诗文鉴赏词典,对于诗人鉴赏水平的提高,对于古典文学遗产的普及,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受欢迎。但是后来,一本一本无甚特色,水平未见提高的同类性质的书便重重复复没完没了地出现,至今尚未见有告一段落的意向。
就我所知,不少学人都为此而苦恼,这类约稿,每年至少数起,不答应吧,必蒙架子太之恶名;答应吧,又得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
许多学人为此而团团转,这也是一种组织工作,不过这是一种于学术的发展大有害处的组织工作。主其事者,其实不过为一主编之虚名与一点眼前之小利,而从其事者,却不得不耗费精力于毫无意义的抄冷饭之中。
我不是说这类著作今后不应再出,我是说,一要有新水平、新特点;二不要牵动过多的学人,最好找三二同好,协力完成。我有些把话说远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想说,于学术的发展有益的学术组织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好的,它需要阔大的襟怀与学术的识力。而这,正是傅璇琮先生这许多年来默默的工作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