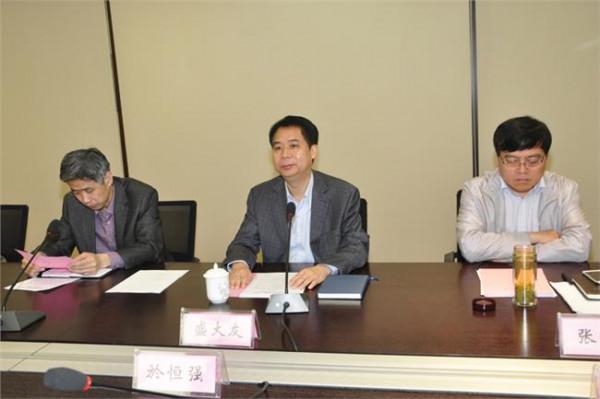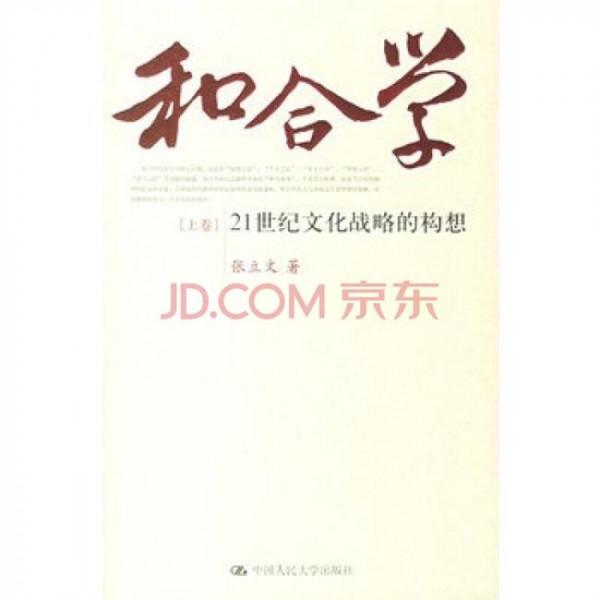张立文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纳西族和合文化)
讲求“和合”,崇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和合文化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和”《说文解字》解为“和,相应也”,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相互配合,和谐一致。
“合”解为:“合,合口也”,即口的上下唇的闭合,引申为相合、吻合之意。春秋时期,“和”、“合”两字开始连用,成为一个整体概念。《国语·郑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意思是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统一起来,治世安民。
《国语·郑语》中史伯回答恒公周为何衰败时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这里史伯将“和”与“同”对立起来,“同”排斥不同的事物,消灭不同的事物;“和”则“以他平他”,接纳不同的事物,允许不同的事物存在,“和实生物”就是金木水火土相杂而成百物。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不和合。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进行了研究,建构了一门和合学。他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真正活的生命”,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
他对和合的解释是,“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王育平,吴志杰认为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中“和”的含义有:价值观内涵是“和谐”;方法论内涵是“融合”;过程论内涵是“合构”。“合”的含义有:创生观内涵是“阴阳和合”;方法论内涵是“会合”、“聚合”;过程论内涵是“离合”、“合生”。
安辉认为中国“和合”思想具有三层涵义:异质元素的存在是和合的前提;动态的冲突融合是和合的过程;和合而生是和合的目标。 总之,中国“和合”文化中的“和合”指既承认不同事物之间有矛盾、差异性,又能使不同的事物同时存在,或相互吸取它方之长补己之短,促进事物自身变化发展的意思。
丽江纳西传统文化,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前的丽江文化,其文化具有和合文化的鲜明特点,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反映。纳西文化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出现和存在的,它是以本民族东巴文化作根基,与汉文化、藏文化、白族文化等和谐、合生的文化。
关于文化,英国泰勒(EdwardBurenttTyfo〕认为: “从广义的人种学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因此,本文将从纳西文化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纳西民族的宗教、壁画、音乐、建筑等方面来论证纳西文化的和合性。[1]
和合文化东巴文化编辑
说起纳西文化,人们就会想到东巴文化。东巴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但它几乎涉及一切社会生活。东巴教是与多种宗教合生的文化。随着佛、道的传入,东巴教里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因素。
纳西族信仰东巴教的同时,支持汉传佛教传入本地区。木氏土司明代在丽江建了一些汉传佛教寺庙群,还在丽江周围的剑川捐建了云鹤、光明两个寺院。福国寺曾经被徐霞客誉为“丽江之首刹”,此寺原来是佛教禅林,旧名为解脱林,后来明熹宗赐名福国寺庙,直到1639年,徐霞客游丽江住福国寺时,据《徐霞客游记》载,他说“寺僧之主持者为滇人”,寺内住的是和尚,不是喇嘛。
到清朝康熙年间,因寺内没有和尚住,才改为喇嘛寺的。木增土司捐资修建了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的悉坛寺、华严阁、一纳轩、尊胜塔院,木氏土司上书皇帝求赐佛经,明熹宗赐佛经678件以及寺名“祝国悉檀寺”。
清代,汉传佛教又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内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族人。
纳西族信仰东巴教的同时,也允许道教传入,因此,造就了纳西地区东巴教与道教和谐而生、共同繁荣的局面。明代中叶,全真派道士曾游至丽江,随后还有其他道教派别的教士也进入丽江。除自来的道士以外,木氏土司还主动请杨园、张觉义、潘朝海等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
明代木氏土司在丽江修建了吴烈山神庙、束河九顶龙王庙、七河大玉初神庙、九河神庙、江东迷剌瓦神庙、束河大觉宫、玄光寺、县城玄天阁、中海雷音(寒潭)寺、白沙真武祠、太极庵等道观。
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发展。乾隆《丽江府志略》记载,清代丽江“道士朝真,村人络绎进香者凡九人”在明代道教庙宇的基础上,清代丽江各地又增加了不少道观、文昌宫。道教信徒还组织了洞经会,该会将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编为神牌。[6]
多种宗教汇集丽江,木氏土司兼信诸种宗教。相传,清代光绪年间,木氏家人生病,请来塔城东巴东五、巫师桑帕、和尚、喇嘛、道士等驱鬼治病。民间也出现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文化现象。丽江过去,每逢甲子年要举办“甲子会”,此会期间诸宗教并行活动。
如1924年的丽江甲子会上,有设在玉皇阁的洞经、皇经、道师三班的经堂,有皈依堂的喇嘛教法事活动,有借用狮子山南头和尚庙举行东巴教仪式活动。这种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文化现象不仅体现在重大庆典活动上,而且也体现在庙堂、宫观的共建共用上。
如今丽江古城北门坡上建有佛教的地藏菩萨庙和道教的城隍庙,这一进两院的建筑结构,前院为城隍庙,后院为菩萨庙。丽江白沙乡的琉璃殿也是一进两院结构,当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进入此地后,此庙也出现过前院住和尚,后院住喇嘛的情况。[7]
和合文化丽江壁画编辑
丽江壁画是合生文化,表现在题材上有多种宗教、同种宗教中的各教派并存,技法上以多民族的绘画揉为一体的手法,风格上兼有道教画风和藏族画风。丽江壁画是明代木氏土司倡导宗教,修建庙宇留下的历史资料。关于丽江壁画,云南工作队到丽江进行过调查,并作《丽江壁画调查报告》(载《文物》1963年第12期),此调查报告道:(一)皈依堂,福龛后面壁画五幅,皆为显宗佛画(二)大觉宫,为密宗画。
(三)福国寺,南北护法堂内各若干幅密宗画像,纯为藏画风格。
(四)琉璃殿,原来有壁画十二大幅,现存十六小幅,考察推断,绘画朴实雄健,无藏画影响。(五)大宝积宫,共有壁画十二幅,多为密宗画像,有藏文题记,掺杂道教画像。壁画糅合显宗、密宗以及道教题材,用笔设色融合汉藏两族风格。
(六)大定阁,壁画共十八幅,混合显密宗佛画,也有道教画像。方国瑜教授关于丽江壁画道:“宗教的并存现象,直接反映在壁画的题材选择上,是他处所罕见的。丽江壁画这种糅合现象,并不是单纯存在于题材的选择上,而且存在于艺术表现上。
在同一个庙宇之内,两堵不同宗教题材的壁画,并无不同的艺术风格,相反倒是有着一种统一的手法。丽江壁画除了继承汉族绘画重视笔墨变化等方面的传统之外,还吸收了藏族绘画绵密细腻的装饰作风”丽江壁画的作者,根据《万德宫石碑》、《木氏勋祠自记》以及其他民间传说等材料综合推断,这一绵延二百余年的创作工作,是有汉、藏、白、纳西等族的画家参加的。
李伟卿说,丽江壁画综合了汉、藏两个民族的绘画特征,但是藏族绘画和汉族绘画风格不是简单的混合。
以大宝积宫为例,宝积宫共有壁画12堵,其题材属于喇嘛教(红教)的有四堵,属于道教的有两堵,属于佛教的有六堵,题材尽管不同,但却有着统一的风格,孔雀明王法会图上那些天王、罗汉、诸天、八部除了用笔略弱以外,在形象上和永乐宫壁画很相近。[1]
和合文化纳西族音乐编辑
丽江纳西族音乐主要指东巴音乐、白沙细乐、洞经音乐等,这里以白沙细乐、洞经音乐为例,它们均是合生文化的代表。
纳西族音乐经典之一——“白沙细乐”
“白沙细乐”是纳西族音乐与汉、蒙古族音乐合生的音乐。白沙细乐纳西语称“北石细哩”,“北石”是地名,即今丽江县城北十公里的白沙。“细哩”意为细乐,也有译为小调或音乐的。白沙细乐在解放前用于丧事中,是一种风俗性的音乐。
张兴荣认为其来源有三,一说是元世祖忽必烈,为褒奖纳西族土司麦良协其攻陷大理之功,而将所带音乐并半个乐队馈赠木氏祖先,传承至今。二说,“白沙细乐”为纳西族自己的音乐。此观点较早见于赵藩1914年撰:《云南丛书》集部之六十三“一笑先生诗文抄”中的《巨甸居人》一诗之注释(清代李玉湛)载:就究此曲创自民间。
木氏盛时,永宁夷(普米族/古称西番)率众来袭,木氏设伏白沙以待之,歼夷殆尽。民间造此曲以吊之,故云“白沙细黎”,迄今丧事处犹用以助哀,声急,悲酸。
三说,“白沙细乐”为“多元音乐文化的孑遗”(即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结晶)。其文化背景可贯穿纳西族地区东巴文化、吐蕃(藏民族)文化、明清汉传文化等各种不同文化历史发展之始终。总之,白沙细乐的产生与最终成型是上述文化背景中,东巴音乐、民间音乐、道教音乐和部分明清戏曲曲牌音乐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8]
“白沙细乐”与昆曲、伊斯兰音乐、蒙古音乐有关,是纳西民族本土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白沙细乐”各章的演奏和演唱风格,均受到纳西族民歌慢颤音法的深刻影响,而这种“下回式慢颤音”正是纳西族音乐灵魂之所在。
“白沙细乐”具有内地音乐风格的乐曲,“白沙细乐”中“三思渠”的旋律与昆曲中的《千钟禄》、《玉簪记》有着某些明显相同的构成因素和风格特色。它又是具有伊斯兰音乐风格的乐曲,“白沙细乐”中第二乐章“一封书”的种子乐句,与伊斯兰音乐“阿赞”两者在旋律上近似。
“白沙细乐”音乐中的某些部分,其风格、调式和音乐进行,又与蒙古族的音乐非常接近。例如“一封书”“美丽的白云”中的两个片段曲调高亢昂扬,慷慨朴实,旋律高下越级的跳跃较多,起伏变化较大,音乐风格也似有几分蒙古族音乐中的漠北草原风味。[9][1]
纳西族音乐经典之二——丽江洞经音乐
丽江洞经音乐是纳西族、汉族等音乐的合生音乐。丽江洞经音乐因主要用于谈演道教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杜庆云撰文,丽江洞经音乐从音乐传承的源流脉络来看,其经腔采用的是晚唐五代的道教学者杜兴庭创制的正乙天师道的“广成南韵”。
由于杜兴庭是江西龙虎山上清宫,江苏茅山“上清宗坛”天师道上清系统的经腔、符录、礁坛科仪的传人,他创制的“广成南韵”有江南音乐古朴典雅的特色。洞经音乐自明清传入丽江后,由于当地乐会严格的口传心授方式和遵从旧制,丽江洞经乐队是一支唯一不用唤呐的丝竹乐队,因而它的演奏风格除体规出道乐仙逸飘缈的意境,也依希显现出江南丝竹文人雅集的艺术品位。
“曲牌”是做会活动各项礼仪程序的伴奏音乐,目前丽江洞经会流传保存的曲牌有《浪淘沙》十四首。
丽江的洞经音乐自中原传入后,与道教的宗教仪式的结构和内容相对应的道教音乐就其内容和形式来看不但十分丰富,而且逐步完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的斋醮科仪成为道教用以修身、祈福、禳灾、赎罪以及超度亡灵的一种独特的宗教仪式,而洞经音乐则成为这些仪式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体现出道家“清静无为、天人合一、虚无自然”的哲学思想。
丽江的洞经音乐从理论观念上逐渐摆脱了仅以“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观念,认为音乐不仅可以感天地、通神灵,而且应该反映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王朝的兴衰、歌颂大自然的风光。
丽江洞经音乐的演奏有独特的乐器,如“曲项琵琶”,据说是北宋末年的三十一代天师张时珍的后裔浙江张道士带来丽江,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著名的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还有“笔管”,目前在我国的福建莆田、仙由等地区流传,台湾地区也可以见到,是古老的莆仙戏中最重要的伴奏乐器和器乐曲牌的领奏乐器。[1]
和合文化传统建筑编辑
丽江纳西族传统建筑是合生文化,指丽江建筑是纳西族特色与中原风格兼收并蓄的建筑。丽江古城选址北靠象山、金虹山,西靠狮子山,东西两面开朗辽阔。城内,从象山山麓流出的玉泉水从古城的西北流至玉龙桥下,并由此分成西河、中河、东河三条支流,再分成无数股支流穿流于古城内各街巷,由此形成了纳西族村寨特有的布置特点,即村村寨寨有流水,家家户户有水流。
纳西族多是泮水而居。住房多建在溪流旁,有些村寨则筑沟引水,通过村寨,使与街道平列,余流则用于灌溉农田。
古城街道不拘网格的工整而自由布局,道路随着水渠的曲直而延伸,房屋就着地势的高低而组合。布局上围绕一个中心布置房屋。无论是丽江古城还是坝区村寨,民居的布置均是围绕一个中心布局。
每个村寨都有一个面积不大、平坦方整的广场,多称为“四方街”。这是商业服务、集市贸易的地方。主要街道从这里放射,分出无数小街小巷,然后民居也从这些街道两旁向外延伸,形状很不规则。民居建筑,既有北方四合院的韵味,又有江南水乡的风情。
在外部造型与结构上,古城民居揉合了中原建筑和藏族、白族建筑的技艺,形成了向上收分土石墙、迭落式屋顶、小青瓦、木构架等建筑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布局自然,水随巷走的古城,在1.
6平方公里内,有适用又和谐的80多座石桥木桥。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
”总之,丽江古城虽然模仿中原风格,但又不忘将它植根于地方和民族传统,未受中原建城礼制的束缚,城市依山傍水,不求方正,不拘一格地随地势建房布街,整个古城结构自由活泼而充满灵气,有中原建筑神韵,但又不照搬古代中原城镇的模式,在总体结构上融进纳西人传统的自然审美观和生活的情调意趣,使其成为一个自然流畅,人与山水亲和的边地古城,它是兼有山乡之容,也有水城之貌的“活着的古城”。
另外,古城在功能上还有代表地方土司文化木府为中心的西南板块和以代表了汉文化流官府为中心的东北板块,但两者有机协调,也有多元文化和合之感。[1]
和合文化和合民族编辑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角,历史上交通极不便,与中原来往不多,汉文化不普及,但只要有机会,纳西族都要学习汉文化。木氏几代都极力结交中原文化名人,虚心向他们请教。明朝正德年间蓟羽士来丽江,木公与之结为知交。嘉靖初年,周月阳来到丽江,永昌举人张含同木公泛舟玉湖。
木公与杨慎虽然始终未能谋面,却是一辈子的知音。为了帮助木氏的年轻人学习,除了延请当地教师外,木氏土司还想方设法请汉文化名师指点子弟。木增曾邀请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访问丽江,并请其指导他的儿子,声称“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 [10]。
木增在《云薖淡墨》中写到: “犹幸先大夫庆云光覆之下,得延鳞群孝廉望先生于塾。先生宏博君子也,课甚严,凡六艺之书及外家之语,靡不耳提面命。
”为了便于学习,在木氏土府的左面,盖起了藏书颇为丰富的“万卷楼”,“楼中凡宋明各善本数万卷,群书侵版亦能备其大要。”(《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古迹》)。
明朝木氏土司木公、木高、木青、木增等的诗造诣颇高,如木公诗作有《雪山始音》、《庚子稿》、《万松吟》、《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后来著名文士杨升庵从这些诗作中精选出114首,题为《雪山诗选》。
木增是个通《庄子》、善诗文的土司,今存诗约五百首、赋文20余篇。木氏所写诗词有的先后被收入明朝《列朝诗选》、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明史·云南土司传》说, “云南诸土官,知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
“考自唐宋以迄元明,金沙江、雅砻江之民族以么些为优秀,而么些诸部以丽江独盛,盖其文化较优,亦即与汉文化较深也。”清朝雍正初年改土归流后,纳西族学习汉文化更加广泛。当时学者蔡嵩称:“余视学至叶榆,丽人争来就试,阅其文清恬醇谨,与滇西诸郡邑不相上下” [11]。
到乾隆年间,丽江“读书入泮学者多,彬彬尔雅与齐民无别矣” [12]到清末,纳西族先后出过翰林2人、进士7人、举人60多人,有诗文传世的有50多人。
长期以来汉学教育和浓郁的汉学风气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社会儒雅文明的风气,形成了好读书、尊师重教的好风气。纳西族一直保持了这个传统,即使家境贫寒,也要想方设法供子女上学,以读书求学为荣。
纳西文化处在中原、吐蕃、南诏三大文化板块边缘地带,没有被任何一种文化所同化,却成为世界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纳西族是一个具有开放胸襟、包容胸怀的民族,是一个善于进行文化和合的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既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又弘扬本族文化,使文化在发展的变异性与传统的恒常稳定性两方面和合起来,真正做到文化上的与时俱进。
历史上,许多土司拥兵数万,割据一方,势力稍大就想称王,而丽江木氏土司拥有一方重兵,却顺应明代大统一的要求,不仅维护了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而且维护了边疆统一;许多土司蛰居一隅,为保持其半割据的政治地位,蓄意关闭自己门户,减少对外交流,而木氏土司却打破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限制,接受多种宗教和多种文化,使自己的民族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与纳西民族具有和合文化的品格是分不开的。
全球化的今天,纳西民族有机会同更多的民族和文化进行接触交流,纳西文化不会西化,也不会僵化,因为纳西人民明白任何文化和身份都离不开时代,构建民族身份的良方是把本土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和合,不断充实,超越文化和地域的界限;对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保护就是继续保持文化的和合性。
我们坚信纳西民族将继续发扬和合文化的品格,以开放的心态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抓住机遇,一方面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努力吸收外来文化,找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和合点,以适应现代社会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使纳西文化永保璀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