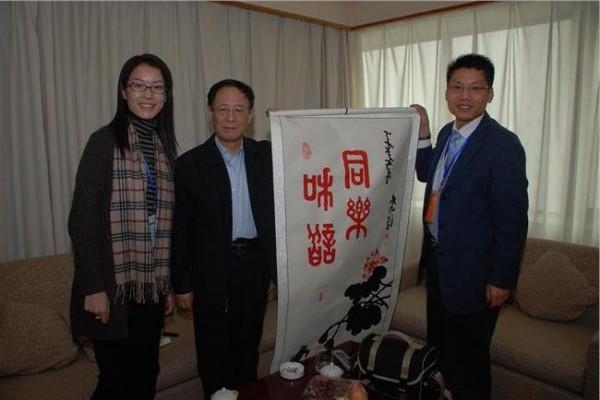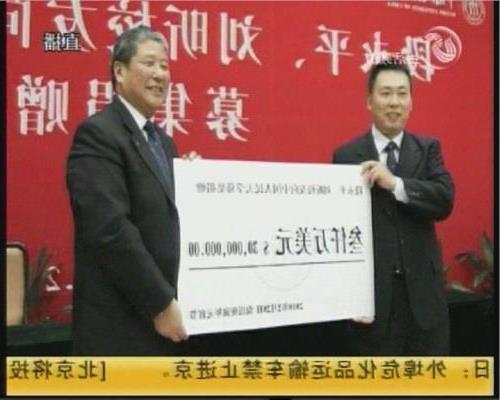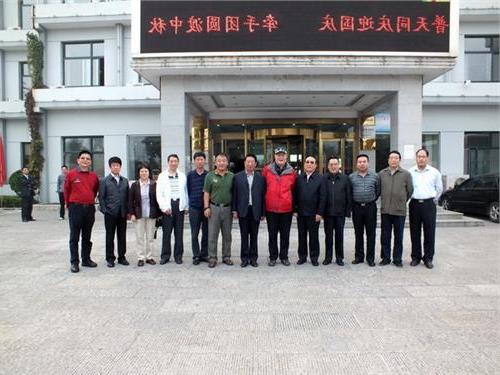刘清平哲学 刘清平:人为践履VS 认知理性:中西哲学比较
二、中国哲学的人为践履精神与天人合一倾向
宫文指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不显著地区分主观与客观,我与非我。……中国人普遍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也“首推天人关系问题”;其中所说的天“并不是与‘精神’相对的自然而是与‘人’相对的自然”,人也“不是与物质、存在相对的精神、思维”。
正是由于“天人关系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既没有出现唯物唯心的对立,也没有出现认识论的理论体系。
不过,宫文又认为:“人类从自然界中异化出来以后,自身要生存要延续。它首先要了解外部世界是什么?怎么样?也要认识人类自己是什么?怎么样?还要处理好自身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怎样对待它?这些就是产生天人关系问题的根源。
”这种看法却流露出把天人关系问题的产生归结为认知理性精神的倾向。如上所述,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正是通过要求首先认识外部世界是什么、怎么样,才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还原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
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倾向的产生根源显然不在于此。事实上,它在本质上首先来源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如何“处理好自身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怎样对待它”这一点;或者说,首先来源于中国哲学特有的关注人为践履活动的哲理精神——人为践履精神。
在中国哲学正式形成的先秦时期,意指着人有目的地作用于周围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各种行为践履活动的“为”范畴,就已经成为“百家争鸣”的焦点,以至于“有为”还是“无为”、“为仁”还是“为利”的问题(而不是宫文所说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问题”),构成了区分儒、道、墨等主要哲学思潮的分水岭。
孔子明确主张有为,尤其重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墨子同样主张有为,但更强调“务求兴天下之利”、“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肯定“兼相爱,交相利”;老、庄则主张无为,对从事有目的的人为践履活动持否定态度,尤其反对为仁、为利,强调个体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中的逍遥自由。
此后,中国哲学经历了长足发展,其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明显拓宽,但在先秦时期就已确立的这种十分鲜明、却为本世纪许多学者所忽略的人为践履精神,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根本上制约着它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并使其无论在理论架构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明显不同于以认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倾向正是以这种人为践履精神为前提的。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曾这样释“为”:“为与伪古通用。凡非天性而人所造作者,皆伪也。”这种诠释已清楚显示出“为”范畴在天人关系问题中的根本意义。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倾向并不意味着它根本否认“天人相分”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如果天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区别,天人合一也就毫无意义了。
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无论是承认天人相分,还是强调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始终都是以人为践履精神为主导,去解决天人之间在人为践履活动(而不是认知理性活动)中既如何相互区别、又如何内在统一的问题。
从天人相分这一面看,老子早已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庄子》中也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在宥》)承认天人相通的孟子认为:“……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肯定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强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为天职。”(《荀子·天论》)在这里,无论“天”是指自然之天还是指主宰运命之天,中国古代哲学家们都是从“无为而无不为”的视角界定它在生生不息的创造生化过程中的本质特征的。
与此相应,他们也从来不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总是强调从人为践履精神的视角规定人的本质存在。
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更倾向于把人定义为能够从事仁义践履活动的动物,如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董仲舒说“唯人独能为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主张“天人相胜”的刘禹锡也认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
所以,即便中国哲学的“天人相分”倾向,也已经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倾向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根本不是从“知”的角度把天、人分别看做是认知活动的客体或主体,而是首先从“为”的角度来区分二者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在强调天人合一的时候,同样不是依据认知理性精神、仅仅要求人达到对天的真理性认知。不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但他紧接着就指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从孟子的整体思想看,他显然更重视在道德践履中修身养性、将仁义礼智之四端“扩而充之”以“事天”的意义。荀子也主张:“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荀子·王制》)《易传》更为鲜明地提倡有为精神,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与天地合其德”。这些观念为后世儒家从人为践履精神出发弘扬“天人合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主张:“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春秋繁露·楚庄王》)。宋明理学明确要求人们在道德践履中遵循仁义礼智等规范,以达到与“天理”的内在统一。程颐说:“既为人,须尽得人理。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践形者惟圣人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说:“圣人与理为一,……惟有穷礼修身为究竟法尔。”(《朱子语类》卷八)
当然,道家哲学倾向于从“无为”角度肯定天人合一。不过,正像西方现代哲学的非理性精神只是西方哲学认知理性精神的否定性表现、而并非后者的空无一样,道家哲学的这种“无为”精神同样也只是中国哲学人为践履精神的否定性表现、而并非后者的空无。
因此,老庄根本不主张通过对天地自然的理性认知达到天人合一,相反却要求人们“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庄子·刻意》)。在他们看来,人只有从根本上放弃“有为”的意图,像道那样“无为而无不为”,才有可能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内在统一,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二十五章、六十四章);“余立于宇宙之中,……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
由此不难看出,中西哲学在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方面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宫文所说的是否“显著”地区分主观与客观、我与非我这种量的差异上,也不在于是强调“分”还是强调“合”上,而主要在于是以人为践履精神还是以认知理性精神为主导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以人为践履精神为主导,就会很自然地着重于考察天道流行与人为践履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人从事人为践履活动的意义,也都很容易导致以“天人合一”作为人生存在的最高理想,像老子和《易传》分别从“无为”和“自强不息”的角度所主张的那样。
就此而言,中国哲学特有的人为践履精神同样对其天人合一倾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是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区别,而是人为践履精神与认知理性精神的区别,才是中西哲学之间最具有本源性的理论差异。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问:为什么中西哲学会分别形成人为践履精神或认知理性精神?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中西哲学自身的理论观念中,而是在它们产生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做出几点简单的解释。
人为践履与理性意识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两个基本要素,本来是统一地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的;但在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传统后,它们在两个民族的哲学思维中却逐渐分化开来。导致这种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古希腊人在开放性的工商贸易活动中,建立了以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制度,并在其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具有认知世界的好奇心的学术阶层,从中发展出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性态度,由此产生了一种以认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精神文化结构;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却在社会结构中较多地保留了氏族血亲关系的原始遗俗,在宗法共同体内相互依赖的个体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与家族关系总是紧密缠绕在一起,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地从事科学活动的学术阶层。
结果,古代中国人虽然已在天文、地理、力学、数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知识,却主要着重于它们在农工生产、政事治理、军事战争等人为活动中的实际应用,并不重视以认知理性的态度把它们提升到科学普遍原理的层面;而古希腊人虽然从古埃及和巴比伦文化那里汲取了许多实用技术知识,却在古代文明中独一无二地通过理论研究把它们抽象为一般性的科学原理,从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文化(著名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就是一个具体表现)。
同时,在古希腊神话中,除了与人类各方面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众神外,还有一位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地位显赫、作为科学庇护者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另一位也具有理性倾向的阿波罗神;而中国古代神话虽然拥有分工更为细致的司责各种技艺发明的众神[⑥],却恰恰缺少一位具有理性倾向的智慧之神;甚至后来出现的“文曲星”,也并非一个在相对独立的学术活动中坚持认知理性态度的神话形象。
此外,如果说荷马和赫西俄德主要是以诗人的独立身份创作出成为古希腊文化“元典”的史诗和神谱,而古希腊的最初一批哲学家同时也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思想家的话,那么,中国文化传统的“元典”——《尚书》、《诗经》、《易经》等,却主要出自那些依赖于统治阶层的史巫之官、采诗之官之手,其关注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社会的政事治理、道德践履等领域,并由此涉及到“天命”与“人为”的关系问题,而先秦时期的许多哲学家同时也首先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正是在这两种很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氛围的深层影响下,中西哲学才会一开始就分别体现出人为践履与认知理性两种不同的哲理精神,并进一步按照很为不同的思维模式形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