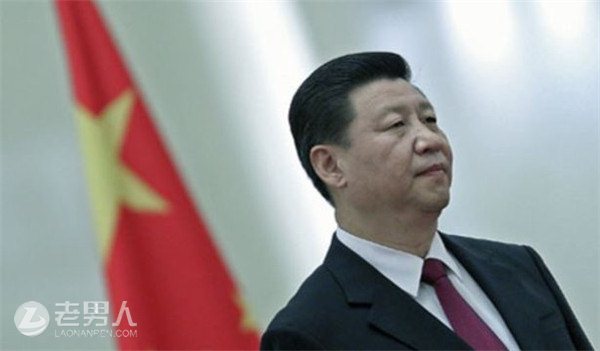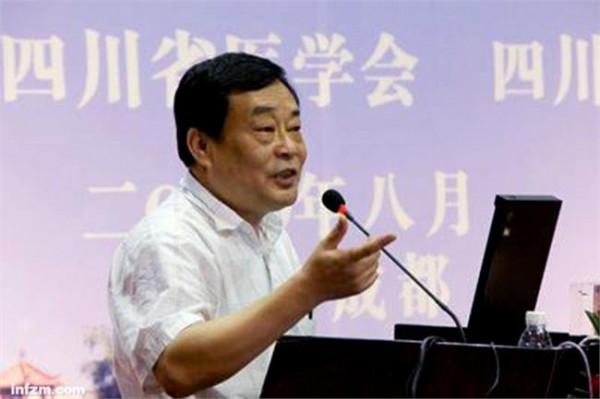【石应康李为民矛盾】追忆石应康1:接管华西医院前后
2013年1月21日,中国医疗机构“大鳄”华西医院更替高层:院长石应康和党委书记郑尚维卸任,原常务副院长李为民接任院长,原常务副书记敬静接管医院党委,其他副院级管理者维持不变。
任免会议在华西医院新教学楼多功能厅召开,这是20年来华西医院最高级别的人事调整。宣布结果后,话筒交给两位离任者作告别演讲。石应康,一位创造中国医院院长任期罕见记录的传奇人物,在这个常被灌满离愁别绪的时刻,居然没有眼泪,也没有过多的客套感谢,反而阔谈华西医院未来道路的要领,“一要团结,二要有梦想,三要创新”,胜似一位踌躇满志的新晋“领头羊”向中层管理者阐释施政纲领。

石应康细心呵护华西医院的情感很容易理解,任何人离开挥洒20年汗水的舞台都会陡生难以剪断的牵挂。但是,受制于新老交替规律,再炽热的激情也有被迫降温的时刻。演讲完毕,一片热烈的掌声把年过花甲的石应康送到台下的座位。自台上走到台下的几步路途中,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已到挥别主政华西医院的时候。

风风雨雨二十年,一幕幕往事如同鲜活时事般在眼前跳跃。
1993年的中国,连空气里都充满“改革创新”思想:邓小平与上海各界人士同迎新春,高度肯定上海的改革开放成果;党和国家组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海峡两岸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出台我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江泽民主席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正式会晤。

更具标志性的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清晰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
就在这个开云见日的年度,位居我国西南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也正在酝酿一项牵动数千人眼球的权力更迭改革:到底由谁来领衔附属第一医院(华西医院前身)的发展创新?

一个晴朗的深秋之日,时任华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钟光,只身找到附属第一医院胸心外科主任石应康,邀请他去历史文化名地武侯祠谈一谈。华西医院到武侯祠,全程2.5公里,驱车几分钟即到。下车后,两人在武侯祠内满布青苔的石板路上踱步,前者心知肚明,后者一团雾水。
后来被国内媒体反复提及的一段佳话由此诞生。
结束简短的寒暄,陈钟光切入主题,询问石应康附属第一医院当前存在哪些问题。以为只是领导摸查医院情况,石应康心直口快地阐述自己平时耳闻目睹的弊端。话音刚落,陈钟光马上抛出第二个问题,大意是如果要改变现状应该怎么去做。石应康又是一番侃侃而谈。
听完石应康的回答,陈钟光话锋急转,“假如组织上安排你担任医院领导,你有什么想法?”直到此时,石应康才恍然大悟。不过,他没有万分激动并顺水推舟地向领导致谢,反倒提出条件——“要做就做院长,副院长我是不来的”。
如此胆大如斗的理由在于,自己本计划兢兢业业地做好一名医生和科室主任,若转做医院管理就必将影响到医疗业务提升,所以便有条件;另外,假如自己担任医院领导,肯定会寻求改革,而实施变革必然要有足够的力量,若只是做领导班子配角,有限的力量很难发动群众,与其这样,还不如留在科室搞业务。
陈钟光当时的内心活动已难考证,石应康猜测他可能在想,“从没遇到这样的人,组织上有意提拔你,居然还给组织讲条件”。继续踱步的石应康倒是一副“无所谓”的心态,“反正我也没渴求当院长”。
“真把这个担子交给你呢?”陈钟光打破短暂的沉默,冒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此时,石应康继续“不知趣”地回应,“我还真有别的条件,把医院管理好,党政团结很重要,最好由郑尚维担任党委书记。”言毕,他又补充两套方案,如果组织上觉得郑尚维不合适,那么院长和书记由他独自担纲;或者,书记人选暂时空缺,副书记主持工作,将来敲定最终人选时,他要参与意见。
由“三个问题”和“两个条件”构成的谈话就此结束,两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很长时间杳无音信。
事实上,当天对着陈钟光一顿畅谈医院管理的石应康,在此之前与一路跌跌撞撞前行的“中国医院管理”并无过多交集。
1951年,石应康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父亲石美森是著名儿科专家、上海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医生、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创始人之一兼院长,母亲凌萝达是中国产科领域的翘楚,伯父石美鑫则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著名胸心外科医生,曾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
就在他出生前几年,作为舶来品的“医院管理”刚刚登陆中国。
医院管理这门学科的确切起点一直迷雾重重,全球公认的最早标志出现在1918年,当时美国外科协会受管理学家泰勒(Taylor)的“科学管理”思想影响,史无前例地拓荒开展医院标准化运动。17年后,即1935年,麦克依陈出版《医院的组织和管理》,医院管理学体系由此萌芽。同年,美国医学会首次面向在职医院管理者开办讲习会,并在大学开设医院管理学专业教程,拉启全球医院管理教育的序幕。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医院,面对初登中国的欧美医院管理思想多为效仿,几无创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医院转而采用苏联医院管理模式。这个时期也被很多史学家称作中国医院管理的“早期雏形”阶段,以模仿为主,没有完整的理论指导,更未形成自己的医院管理系统。很多人认为,向谁学并不重要,关键是保证医院遵循医疗规律向患者提供高效的医疗服务,这才是医院管理的终极目的。
春天终于到来。1977年,受父母耳濡目染而攻读医学的石应康拿到四川医学院的毕业证,1982年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并供职华西医院。两事之间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迎来盛世,医院管理同样枯木逢春:1980年,中华医学会召开全国首届医院管理学术会议;1981年,我国首份探讨医院管理的刊物《医院管理》创刊;一些学术活动陆续恢复……伤痕累累的中国医院管理重新起航。
但是,残垣断壁的废池,在短时间内肯定难以幻化成高楼林立的新城。整个1980年代,我国医院的质量管理、门急诊管理、病房管理、护理管理、学科建设等相比以前均有长足进步,可距离西方国家的水平仍相距甚远,远未形成管理理论体系,而且饱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特点。
在这种环境下行医的石应康,留给同事的深刻印象是“一个拼命奋斗的医生典型”:兢兢业业,不打小算盘,与病人相处融洽,乐意为同事提供服务。这正好辉映他的内心,自打跨进医学院校,就一直熊熊燃烧“当个好医生”的梦想。他还给“好医生”作出注脚:病人喜爱;同事和谐;技术精湛。付出总有回报,1988年,年值37岁且只做两年主治医师的他破格晋升副高职称;1989年12月,被公派留美深造。
1990年,此时石应康已身在美国。对于他而言,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并不陌生,毕竟母亲、弟兄及几位至亲都在那边生活和工作。时间飞逝,一年零一个月的访问学者期结束,石应康又到开启新一段人生历程的节点。那时,亲戚们已经帮他申请绿卡,并找好美国一家大学的工作岗位,但他最终婉拒了亲戚们的劝诫,执意回国。送别席间,唯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高级学者的小姨夫表示,“我能理解他,支持他”。
留学经历让石应康的业务如虎添翼:归国后不久,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2年,再度破格晋升教授并担任胸心血管外科主任;1993年,擢升博士生导师,成为全校最年轻的博导,并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就这样,石应康揣着“当个好医生”的梦想边收获边前进,继续不断提高自己在心脏瓣膜外科、大血管外科、冠状动脉外科等方面的造诣。
走着走着,他渐渐发现医院的制度、氛围、文化都在阻碍梦想。
一个典型的例子,工作富有激情的他主动申请每周多排几台手术,而且不要奖金。医院领导遂了他的心愿,但没想到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师却极不乐意,抱怨“为何要做这么多事”。石应康逐渐明白,“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的加班,一次两次还可以,若每个礼拜都如此,哪怕平时相处再融洽的同事也会婉拒配合。”
“既然规则挡路,就要去改变规则”,石应康暗想。
日子一天天静静地流淌,直到武侯祠谈话。
那一天,带着目的邀约武侯祠谈话的陈钟光,早已知悉石应康的业务卓尔不群,而且还通过其他渠道获悉他富有个性的行事准则:一是尊重理想,否则会向美国的优厚待遇妥协;二是内心热衷服务和奉献,极其渴望在服务中彰显人生价值;三是性格直爽且与人为善。
果不其然,武侯祠谈话时,石应康像开闸之坝,畅谈医院管理想法,且生猛地自荐执掌华西帅印。他事后回忆,其实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有无机会无所谓,若有就去打破成规,让更多人拥有做好医生的环境。
出乎意料的是,一次快人快语把自己卷入中国医院管理洪流。
1993年12月13日,即“武侯祠谈话”过去两个多月,华西医科大学突然宣布人事调整通知。刚刚迈进“百年医院俱乐部”的华西医院迎来两位新“舵手”:年仅42岁的院长石应康和谈吐优雅的党委书记郑尚维。任命通知上还列有三位左膀右臂的副院长:梁德荣、欧阳钦、裴福兴。党委副书记由石应康兼任。
也许是职工已习惯领导层的新陈代谢,抑或潜意识里就觉得“换汤也难换药”,总之,那次院领导调整在员工中并未激起多大波澜,更别提把“绝处逢生”、“学科名列全国前茅”等诸多厚望寄托给他们。
握着华西医院的“帅印”,石应康知道,摆在面前的现实如同四面楚歌。毕竟,短短两个月前,在回答陈钟光的第一道问题时,他还有条不紊地阐述过华西医院的困局。接下来要做的,是按照回答第二道问题的思路去改变现实。事情真的就有备就无患吗?未必如此。
石应康的医院管理生涯刚刚起航,前方就是一批难题。
是的,是一批。招架吧,没有缜密斟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