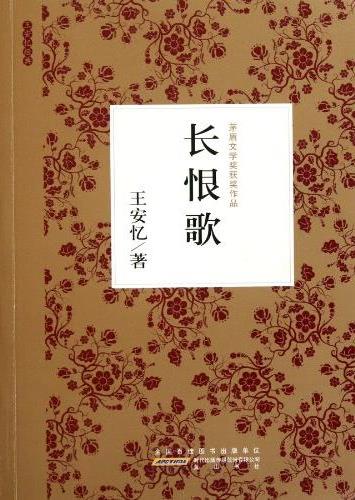王安忆长恨歌赏析
近年来,人们对这本书的探讨大多围绕王安忆在书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他们强调小说所表现的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如徐凌俊在《王安忆<长恨歌>三论》中说:“比较一下《长恨歌》中的几个软弱的男性就知道,王安忆在作品中还是强调了她的女性优于男性的这种女性意识。
男人如果有优越感,也是凭借着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与金钱,而女性,一无所凭,只凭借她们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就足以超越男性。”“小说的主角王琦瑶是个女性,王琦瑶的手帕姊妹当然是女性,连在王琦瑶那里厮磨时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腊、长脚、她女儿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
小说作者把所有的男性都放逐到历史社会、历史时间里去了。”所以他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小说的范本。
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一部《长恨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恰恰不是体现在女性的主体地位上,而是体现在女性强烈的依附心理上。整部《长恨歌》隐含了三种依附: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城市对乡村的依附。这三种依附又是环环相扣、因果相承,小说中每个人都被扣在其中一环上。而无论哪一种依附,有一点是相同的:处于这一依附链条上的人都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1、 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
《长恨歌》中的男性大多是被边缘化的。如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蜡、长脚。作者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身份,未花多少笔墨写他们的出身经历,仅仅抓住了他们生命中与王琦瑶有交集的那一段来写。因此他们似乎都有些来历不明、去路不清。
李主任是王琦瑶最初投靠的人。他是高官,权力的化身。但对政治权势的依附也使他沦为政治附庸。“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牵一发动千钧。外人只知道李主任重要,却不知道就是这重要,把他变成了个活靶子,人人瞄准。”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大势已去,李主任坠机身亡。他是时代的殉葬品。
王琦瑶与康明逊的感情之所以没有善终,是因为懦弱的康明逊最终向家族势力屈服。康明逊是资本家少爷,但他的家族是老派的,主次分明、尊卑有序,他是康家正传,未来的路是被家族设定好的。他最终依附了传统,成为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一个牺牲品。
男性去依附权势利欲,女性又来依附男性,可见注定都是一场空——
2、 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这第二种依附是全书的主线。《长恨歌》里的主人公王琦瑶流浪在男人之间,她先依附摄影家程先生成为沪上淑媛,荣膺三小姐;继而依附李主任,脱离逼仄弄堂过上优裕生活;王琦瑶与康明逊在一起,有一种抓住青春尾巴的意思,她要在青春尚未完结之时找一个托付;依附萨沙是为了把孩子生下来;依附怀旧青年老克蜡则完全是出于对老的恐惧,想找人为自己送终。
然而,王琦瑶到头来仍是无所依附。王琦瑶对于李主任来说,是名利场上退一步的相守——“……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是人生的风景。”对康明逊来说,则是他于传统势力束缚中一次无力的挣扎。对老克蜡来说,她更像是他所崇尚的旧上海的影子,他再憧憬那个时代,也不能抛弃现世人生。
王琦瑶生命里的男人匆匆皆过客,将死之际她只有一个核桃木五斗橱。在一无所有的年月里,她看着这个五斗橱,心便定了。女儿婚后去美国投奔丈夫,“王琦瑶心里犹豫要不要给她一块金条,但最终想到薇薇靠的是小林,她靠的是谁呢?于是打消了念头。”可见这橱里的金条是她的底子了,然而这底也不是她自己挣来的,是李主任的赠予。
王安忆通过这一主线,是想表现女性生无所依的人生悲剧。正如小说开篇所说:“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
”她们看似有着独立维持生计的表象、有着精细生活的不服老的心,但她们仍渴求有所依附,她们都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男性双重控制的“上海女儿”。作者借王琦瑶外婆的口说出了这一点:“……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败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
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这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两千多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
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然而这社会心理却是沧桑巨变中的一点凝滞、保守和冥顽。女性不可能在物质、精神上完全独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当时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深度。
3、城市对农村的依附
王琦瑶在上海解放、繁华梦破后回归邬桥,就是这种依附的一个象征。“邬桥的一切都是最初意味的,所有的繁华似锦,万花筒似的景象都是从这里引发伸延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子女,最终也还是落到邬桥的生计里,是万物万事的底,这就是它的大德所在。
邬桥可说是大于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物质的最原初。”小说开篇时说上海的繁华且是有实用作底的。这“实用”,便是邬桥。王安忆称“邬桥”是“母体的母体”“做的多,说的少的亲缘”“总是个歇脚和安慰” ,更直接写出“每一个外乡人,都有一个邬桥”。作者通过对邬桥的大段铺叙强调了城市对农村的依附。
作者在小说中渗透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与小说写作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