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喜宴解读】王安忆:现在人阅读少 30岁也非常幼稚
中国人认为选编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方式,这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好像分得非常严密,孩子该看的和大人该看的有分界线。幼儿看看绘本、图画,等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所谓“成人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文学本身就是青春的读物。——王安忆
2016年上半年,身在美国的作家王安忆接到了诗人北岛的电话。北岛请王安忆推荐一些给孩子读的短篇小说,他与出版机构“活字文化”合作,主编了一套“给孩子系列”图书。王安忆手头没有资料,凭记忆列出一批小说。
下半年,王安忆回国,北岛提出直接由她编选。书在2017年春节前就编好了,王安忆起初想到的那批作品,大体保留在书里,书名定为《给孩子的故事》。在王安忆看来,“故事”的含义更广博,有围炉夜话的亲切感,也是文学的最初形态。“故事”兜兜转转,发展出民谣,又因为鲍勃·迪伦获得诺奖,故事的价值被再次确认。就这这种想法,王安忆也给书里拾进了几篇叙事散文。因为担任编者,她抽走了自己的小说《打一电影名字》。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也是作家,家里书籍很多。王安忆从小就广泛阅读,不拘于儿童文学。她曾在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时代》担任过编辑,时常去学校调查、采写,组织活动。1979年,她的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在《少年文艺》杂志。写过几篇“儿童小说”后,她开始写第一篇“成人小说”《雨,沙沙沙》,并将这篇作品视为自己的处女作。
王安忆很早就反思起儿童文学的概念,并不认为文学可以分出儿童和成人两类。在前言中,她谈及理想中的读者:下限是认识汉字,能理解书面表达;上限却弹性很大,十到十五岁,也许稍大,将成年未成年、大致可称“少年”的年龄段,都可阅读。“这个成长阶段相当暧昧,不能全当成大人,但要当做孩子看,他们自己首先要反抗,觉得受轻视,不平等。”她继续写道。
确定篇目不容易,因为肯定漏掉许多好作品。如迟子建、苏童、刘庆邦的作品,王安忆几乎觉得篇篇都可以选进书里,但每位作者只选一篇是原则。她比较了苏童的作品,最终选进来《小偷》,小说记述一桩残酷的往事,但孩子间的友谊又留存了些许单纯。迟子建的作品,她起初选了《一坛猪油》,因为太长,又换成描绘生机勃勃的渔民生活和女性悲剧的《逝川》。
从1920年诞生的汪曾祺到生于1978年的张惠雯,25则故事大体以作者的出生年份排序,通读下来,仿佛简略的当代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编选过程中,王安忆终于了解到,自己“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留下的故事,包含了成长的欣慰与酸楚,亲朋逝去的惆怅,世界不可逆转的变幻,男孩对年长女性的倾慕,甚至父母辈的婚外恋情。无疑,在传统观念中,后面两种未必适合孩子阅读。
孩子该读什么,王安忆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虽然毫不因袭传统,但她还是请责编和作者们沟通,去掉故事中的某些粗话,因为“非常不雅,给孩子看不好,容易学坏了”。
2017年5月21日,王安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谈起应该呈现给孩子们的故事。
“现在人阅读少,30岁也非常幼稚”
南方周末:你在少年时代读什么样的作品?
王安忆:其实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别人肯定不会有我这么好的阅读条件:我家里面有书,可以读很多。我很早就开始阅读,范围也挺广,主要是童话、传说、神话。那时候,我母亲在上海作家协会,我很小时,可能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到那边的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我总是借一大堆回来,很快还回去再借。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儿童文学的这些书,我个人兴趣倒不是很大。
在1960年代,我们是这么分的:学龄前或一二年级的孩子看《小朋友》,以绘画为主,也有文字,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四年级到初一读《儿童时代》,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文字多,但有相当大一部分插图;年龄再上去一点,我们还有上海的《少年文艺》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阅读,当时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阶梯。
南方周末:哪些作品影响了你的成长?
王安忆:这倒说不清楚了,小时候看的不一定记在心里面,但是阅读会慢慢积累起来产生影响,很难理性地分析。很难说我受谁的影响,我们就是杂乱看书的一代人。我1978年回到上海,到《儿童时代》工作,看了一些儿童小说,但没有认真分析过它的状态。
我们可能继承了苏联当时的“校园写作”体系,把少年儿童、少先队员看成祖国的未来。我编辑和阅读儿童文学,最早时还写过,但是很快不写了,因为感觉有一点把文学幼稚化。我很早就提出,文学不应该这么分类。
南方周末:与你的少年时光相比,现在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安忆:现在的人阅读少,当年我们不管爱好不爱好文学,读书量都比现在大。图片、电视、电影还有动漫……现在直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阅读量非常低。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你先得识字,之后还要有一定想象力,能把文字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声音、画面。读图一定是很直接的,相对来说简单和表面得多。
但年幼的孩子读绘本,是比较科学的。他们识字量少,看图画非常合适,尤其绘本有专门的风格,非常适合儿童阅读。我个人很喜欢绘本,觉得好的绘本像安徒生童话一样,小孩要读,大人也要读。它有些东西是孩子根本读不懂的。像《海的女儿》,写的不是残酷的故事,而是非常高尚的,那么纯洁、无我的爱情。
西方有些绘本非常深刻。我曾经看过一本叫《阁楼上的光》,好像是“新经典”出版的,真可以称为经典,大人孩子都可以读。它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只是生活当中小小的现象,配上图和文字。这些现象非常幽默、温馨或严厉,总之很有趣。
南方周末:为编选这些故事,你是否特意观察过当下孩子的趣味?
王安忆:我没有刻意去关心这些,只是觉得现在给孩子看的东西太幼稚了。好像一个人年龄很大,还是这种趣味,三十来岁的人也非常幼稚。这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具体现象非常多。孩子读书少,动漫都那么简单,好像一个人发育非常晚,始终那么天真。从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等都趋向于低龄化,非常简单,整个标准在不断降低。影视作品我现在看得比较少,它们可能更加强调直觉和所谓的视觉冲击力。
南方周末:你在前言中写道,“得让他们把过来人放在眼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王安忆: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很差,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智商。阅历还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的阅历和认识肯定比他们丰富。以前过于强调孩子要阅读“低”的,其实不见得。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看课外书,班主任过来说不应该看这样的书,意思大概是在你这个年龄看《红岩》已经到头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名叫《虾球传》(注:黄谷柳的长篇小说,以194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一带为背景,描写少年“虾球”在底层社会的流浪历程)。我四年级就看《红楼梦》了,《红岩》不能满足我。《铁道游击队》这样的经典我很多都没看过,个人喜好不一样。
有些概念,把事情规定得越来越窄。我们现在好像分得非常严密,孩子该看的和大人该看的有分界线。幼儿看看绘本、图画,等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所谓“成人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文学本身就是青春的读物。
“不给他看小说, 他就不知道死?”
南方周末:最初联系你时,北岛怎样形容他的想法?
王安忆:我以前看过他们出的系列书,给孩子的诗歌、散文等,所以大体知道他们的想法。有一篇是我向编辑争取的,就是黄蓓佳的《布里小镇》。他们觉得这篇小说好像写和孩子无关的事情,但换个题目,比如“爸爸、妈妈的爱情”,就有了关系。我们不断沟通,他们认为这篇写大人之间的三角恋爱,不应该给孩子看,但我觉得小说里面的人物都那么天真可爱。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把这篇小说保留了下来,我感到很满足。
南方周末:你选择了汪曾祺的《黄油烙饼》等写死亡的作品,是希望孩子对死亡有所认识?
王安忆:这又关系到我们对孩子的认识:难道不给他看小说,他就不知道死吗?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些孩子很就早经历爷爷、奶奶去世,回避没有太大意义。我倒没有考虑死亡是不是不该让孩子阅读。
南方周末:书里的故事还涉及很多重大主题,比如亲情、友谊、成长。这是你的个人偏好,还是文学就植根于这些最重要的词汇?
王安忆:严肃的文学当然要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光阴……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慢慢学习,尤其是我们对孩子的定义,就像我在序里写的,我大概把孩子、读者的年龄上限放在15岁。15岁的人应该读正常的文学作品了,不要再读那些为他们特制的。
南方周末:一些作品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比如东西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以及王璞的《捉迷藏》。但孩子未必了解得那么清楚,你预期这些故事将产生什么效果?
王安忆:《你不知道她有多美》里的大地震完全是隐喻性的,景象很灿烂,是一个男孩子对女性初生的崇拜。大地震给了他一个环境,身上插满玻璃片,玻璃片亮闪闪的,不能拔,一拔就出血。它有隐喻,意象又非常美,非常璀璨。
《捉迷藏》写得很好,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丰富,可能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出来,了解不了解背景无所谓。每个孩子都会捉迷藏,她在外面躲一晚上,回到家以后,显然发生了一件比一晚没回家还要重要的事情,这就行了。你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可能发生很多比他的事更加严重的事情。他现在可以明白一点,不断地再详细地明白。读书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情丰富,让孩子更聪明,让孩子了解: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还要多。
南方周末:这个选本反映了哪些你的特质或价值观?
王安忆:它还是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一些我对小说,尤其对儿童应该读的小说的看法。这些小说写得很特别,文学性很强,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孩子看的,没有我们惯常看到的儿童文学那种“娃娃腔”。中国人认为选编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方式,这很有意思。让我编选,肯定要体现我的选择,每一篇都经过我的阅读和考虑。我们经常碰到编者只排名字,排他觉得有名的作家,这样编不够好。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左)也是作家,家里书很多。王安忆从小就广泛阅读,不拘于儿童文学。(视觉中国/图)
“我不太赞成暴力美学”
南方周末:让孩子读令人难过的故事,是要打“预防针”,告诉他们人生会发生这些吗?
王安忆:不是人生,我们读小说,是要将感情变得丰富一点,得到一些充实。难过是感情的一种表达,如果一个人连难过都不会,还有什么感情可以享受?
南方周末:但大家通常认为该让孩子多看点世界的温存,少让他们接触残酷的事情。
王安忆:我对残酷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看的,比如说,暴力的东西。我选的小说,没有一篇是暴力的。暴力是外部的东西,内里感觉不舒服,感觉到难过,正好说明你的感情还没有麻木、还敏感。像电影分级一样,有些东西就是不该看的,连大人都最好不要看。
我个人抵触暴力,还有比较庸俗、鄙俗的东西。从美和丑来分辨,特别暴力的东西首先不适合美学,我不太赞成暴力美学。美学应该和道德在一起,又和我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在一起,但“真善美”这个词被大家用烂了。
南方周末:你希望这些故事能“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指什么?
王安忆:其实是非不需要我来解释。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去做的,还有一些事情的对错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苏童的《小偷》,里面的是非就很微妙,但又和感情联系在一起,有些事情不是理性告诉你不对的,而是感性告诉的。应该让孩子面临一个比较丰富的环境,再抉择。
南方周末:你选择了一些少数民族或军队背景的小说,孩子未必经常读到,是有意为之?
王安忆:我倒没有从人的身份上去选择,我觉得它们都很好。阿来那篇《秤砣》特别有意思,其实是讲我们给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规定是有变化的,不要觉得世界的规定只有一个。粗看觉得有趣,慢慢会不断发现里面有东西。
张承志的《红花蕾》也写少数民族生活。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能够分清楚物质贵贱和货币的关系。而文中那个女孩的生活和货币完全没有关系,她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她的世界里有另外一种评判标准。
南方周末:鲁敏的《在地图上》与《秤砣》很像,也写到了人们对世界的规定和人的生存状态。
王安忆:是的,鲁敏那一篇我很喜欢,我找到它很偶然。我一直记得有这么一篇小说,但以为是苏童写的,还当面问过苏童,苏童说他没写过。我想不起是谁写的,当时鲁敏不是很有名。这次编选,我看了一些以前的年选,才看到这篇是鲁敏的。虽然比较长,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放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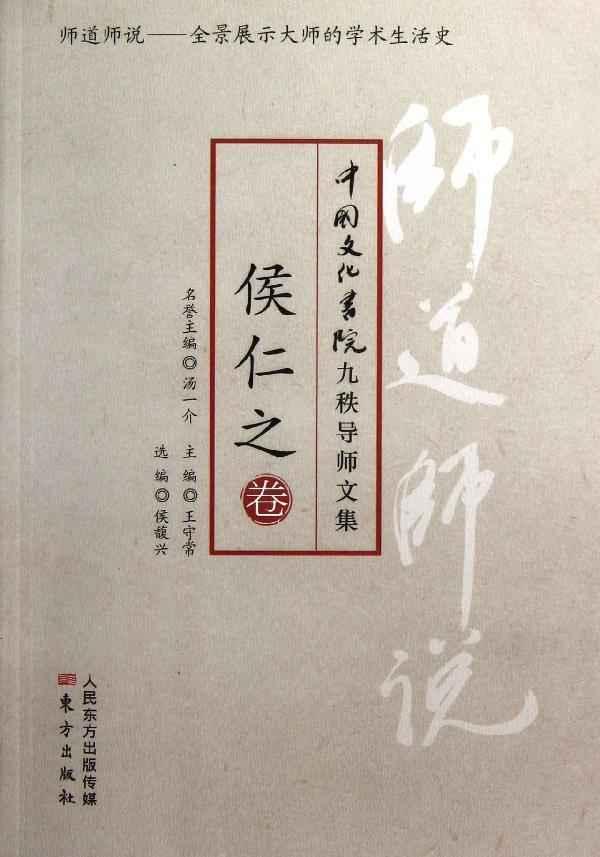
![>刘纯燕配音 [独家]刘纯燕忆邓波配音细节:让人一听声音就想亲她](https://pic.bilezu.com/upload/a/bf/abf9afe86dbf2fae087185f384368a6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