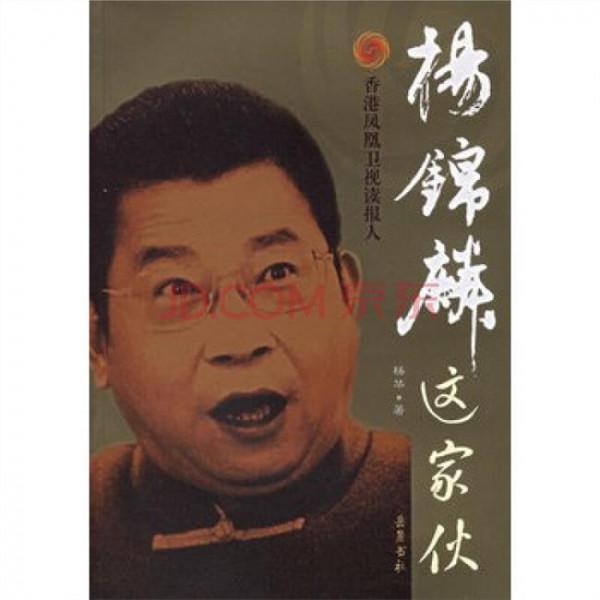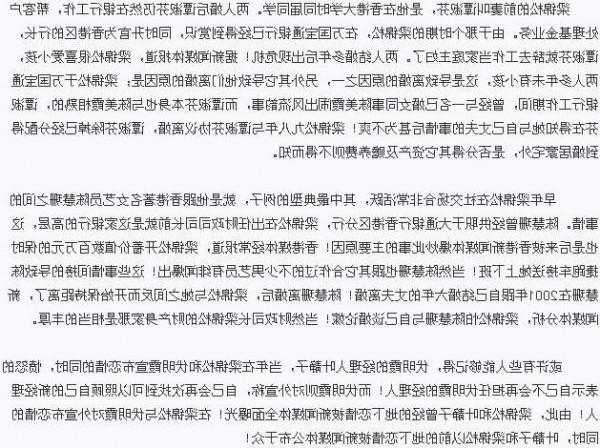关锦鹏在香港电影界 关锦鹏:既近且远 既远且近
节选自《青年电影手册》第五辑:《关锦鹏:既近且远,既远且近》
对话者 / 关锦鹏 程青松
摄影 / 缪健 凌代军
程青松:其实在更早的《人在纽约》中, 张曼玉的女同性恋角色都已经有这样的,只不过到了《男生女相》的片尾,你袒露了同志的身份,那个阶段,你拍了不少纪录片。

关锦鹏:有《斯琴高娃的二三事》、《男生女相》等。我的大众传播专业没有念很久,因为是与无线电视台的训练班同时念的,精力可能都是在无线电视台这边。
程青松:看得出来,你在拍片的时候,可以动用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纪录片,包括《红玫瑰白玫瑰》里也是以字幕的形式呈现的,这很新颖。为什么会这样?

关锦鹏:我觉得我小时候,撇开邵氏的武打电影,不能不说与性取向有关。我记得我看张彻的武打电影的时候,我完全被打动了,是因为一个男人可以为另一个男人去死,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我觉得那时已经有一个过程来验证我自己的同志身份,哪怕那个时候是懵懂的。

但我个人觉得电影是跟我在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男生女相》最终只是代表了我的个人观点,《浪淘沙》的导演可能从来没有那个意思。但作为观影者我有权利这样诠释你展示给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当然性取向或者说我个人的sensibility(感性),哪怕我后来一直听到最好的电影是一种互动的说法,并不单指某一方面的交流,是双向的 , 但我觉得哪怕不懂得很理论化地去说电影应该怎么互动,至少我切身感受到了。

程青松:《女人心》可能就稳稳当当说一个故事,但是《地下情》,我觉得不只说一个故事,到《阮玲玉》、《胭脂扣》更是如此了。
关锦鹏:从《地下情》到《胭脂扣》,很快我就有点不甘心去叙述一个故事,我希望一场戏可以有很多的层次,这个是跟前面或者后面有关系的。
程青松:你的电影很现代,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不是说把一件事情告诉大家就完了, 一人一故事一道理,它是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商业片反而要简单一点,所以你的电影里你自己认为是香港成分较多,其实大家一看,尤其是《有时跳舞》,特别像欧洲电影,但你不是按照那样的思路去拍的,这个绝对不是商业电影。我觉得可能别人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关锦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北京买了一本讲华语电影十个导演的书,那时候我还没拍《长恨歌》,他说上面清清楚楚地把我的作品,从《女人心》到《蓝宇》都介绍了,但是中间唯一没有《有时跳舞》。
程青松:我觉得你拍的整个过程,把自己内心的东西都全部解决了。1998 年拍《愈快乐愈堕落》的时候,也都是在表现这个内容,这个电影也很有意思,邱淑贞在电影中的经历特别像同志电影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需要透过别的东西来发现,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投射的过程。
关锦鹏:我觉得《愈快乐愈堕落》里面曾志伟的角色,包括邱淑贞的角色,都透射着不同程度的我。柯宇纶用香水,我觉得他更多是被陈锦鸿那个女人吸引,他还是有点不知道往哪边靠,这种阶段,我是有过,就是在挣扎。曾志伟的角色某种程度已经是放开了,我觉得《男生女相》带给我的是我电影前后段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对我自己而言的,对观众,或是我的朋友来讲,不见得那么重要。
我觉得哪怕《人在纽约》、《地下情》都是朦胧的,哪怕《胭脂扣》,都是一开始两个男人贴得那么紧,梅艳芳是异装成男人的,我都有这个意识。
我觉得《男生女相》之后有一种坦然,那种坦然是你对每个角色,甚至是对你自己的东西拉开一个距离去看。让我想到在拍《男生女相》时,我曾经访问侯孝贤,因为谈到小津安二郎,侯孝贤导演给了我八个字,我觉得很受用,某个程度上来说也是侯导做导演的标杆,那八个字就是“既近且远,既远且近”,一个好的导演就是满怀激情地把心里的故事说出来。
但我觉得,你蛮有激情地把你自己的东西说出去的时候,同时也要有距离地看待它。
程青松:张曼玉和阮玲玉进去之后要抽离出来。
关锦鹏:都是这样。某个程度我对电影本身的看法,后面不管是《愈快乐愈堕落》、《蓝宇》,还是《长恨歌》,都是这样。对《长恨歌》,香港有这样一个评论,就是说关锦鹏要告诉人家:将来他有一天要死守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