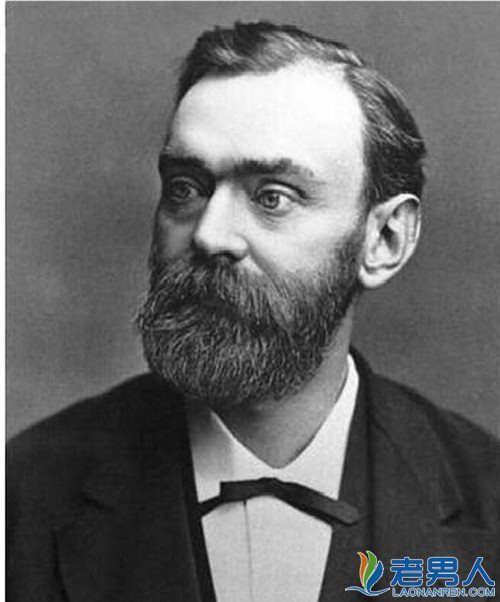桀骜不驯相近的词语 桀骜不驯:历史上的奇葩知识分子
明代有过一个奇异的人物:陈谔。这个人是很有趣的。关于他的文字记载,至今读来,感觉也要比各类新闻中的八卦有趣多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明史.列传第五十》:“陈谔,字克忠,番愚人。永乐中,以乡举入太学,授刑科给事中。

遇事刚果,弹劾无所避。每奏事,大声如钟。帝令饿之数日,奏对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见,呼为‘大声秀才’。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还职。已,复忤旨,罚修象房。贫不能雇役,躬自操作。适驾至,问为谁。谔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怜之,命复官。”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被体制化的司马迁,从来就一无是处。写出《史记》的,不是那个被体制化的司马迁,而是那个因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司马迁。
在俄罗斯,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于司马迁的人物。杰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就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иёв)。生于1853年的他,二十出头就担任当时世界上所公认的最好的大学之一圣彼得堡大学的高级讲师。

1881年3月,他出面为那些参与谋杀沙皇的人辩护,并公开向亚历山大三世呼吁宽大处理。结果,自然是遭遇沙皇的惩罚:被禁止公开讲课,被迫放弃学院生涯。
从此,过着流浪生活,也没有经济能力成家立业。然而,他的成就,正是始于1881年3月之后。《生命的精神基础》(1882-1884)、《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1887)、《俄罗斯和普世宗教》(1889)、《自然中的美》(1889)、《爱的意义》(1892-1894)、《上帝的观念:为斯宾诺莎的哲学辩护》(1897)、《理论哲学的基础》(1897-1899)、《善的证明》(1897-1899)和《三次谈话》(1900)。

在俄罗斯自由主义传统中,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一个占有着重要位置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至今惠及世人,尤其对于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国人有着启示意义。如反对伦理主观主义,而主张 “最低限度的道德强制制度化”。
“最低限度的道德强制制度化”,是道德存在的基础。没有“最低限度的道德强制制度化”,就没有道德可言,道德的存在,也就丧失其意义。也就是说:以德治国,不如依法治国;德治不如法治;德治是扯淡,法治才是务实。
索洛维约夫证明了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相容性,仅仅这一成就便足以使其与马克思.韦伯并列。而今,谁还记得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们的那些皇皇巨著?
叶公超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上,也有过一个奇异的人物:叶公超。不到22岁,他就拿到了剑桥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当时出国留学英美的华人中,这是罕见的。
他是钱钟书的老师,钱钟书却在后来的《围城》一书中暗讽他性情慵懒。读懂那段故旧的亲友,即便恼怒,却也无可反驳:毕竟梁实秋翻译了莎士比亚,而叶公超却未能翻译过一部英文著作,仅仅临渊羡鱼般的赞赏过作为小说翻译家的林琴南和作为《诗经》译者的庞德。然而,翻译毕竟是二流的文艺事业。一流的文艺天才,自然只能从事一流的文艺事业。
叶公超对于鲁迅的评价:“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性,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词语里。”“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从中足以见得,叶公超对于鲁迅的理解,极其深刻!这样一种理解,纯粹是一流的文艺天才对于另一个一流的文艺天才的一种惺惺相惜,真正的政客,是不会有的,有也不可能公开发表出来!
叶公超也是后来因物理学成就而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杨振宁的英文老师,但是杨振宁在回忆他这个叶老师的时候,语意中显然有着误人子弟的嗔怪。在他的另一些学生的回忆中,这位叶教授,给学生上课的兴致可不怎么高,他教书的时候,都懒得备课,到了课堂上,更是比领导还领导,领导大多是要发表发表演讲的,可是他呢,懒得讲,经常就是叫学生自己上去读英文原版的《傲慢与偏见》,甚至懒得点名,让学生按照座位顺序依次上台。
引领自习?这种法子在今天肯定要被举报、告发N回,其个人水平,也会被质疑。
如季羡林就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
’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然而,叶公超的这一教学方式,显然是受到了Robert Frost的影响。Robert Frost有着奇怪的个人主张:“只讲究念书不念书,不讲究上课不上课”;这也就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一种伪教育;真正的教育,是要给予学生自学能力并引发学生自学的兴致。
文艺这东西只能靠学生自己去学自己去悟。这是非常前卫的一种观念,也只有Robert Frost和叶公超这样的大牌人物,才有资格去实践实践,否则的话,不是给学校开除,就是被世人误解为教育上的懒惰和误人子弟。
英美现代诗人中最著名的艾米利.迪金森和T.S.艾略特,她们在华人中最早的知音,就是叶公超。当叶公超在爱默思大学读书的时候,这位美国著名诗人正是该校“驻校诗人”,也是对他极其器重并寄予厚望的老师。非常可惜的是,叶公超并未如Robert Frost所愿,成为媲美泰戈尔的亚洲著名诗人,而是偏离正轨,走上了政途。
就Robert Frost对他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当诗人而去从政呢?这肯定是Robert Frost所不能理解并要为此抱憾的!
叶公超有着一流的文艺才华,最大的见证者,就是Robert Frost,其次就是T.S.艾略特。1925年秋,叶公超来到剑桥大学进一步深造并结识了在英国诗坛负有盛名的T.S.艾略特。N年以后,当叶公超的学生在欧美遇到这两位英语诗歌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还主动提起叶公超。
叶公超的学生王辛笛在爱丁堡大学时曾领略过T.S.艾略特的风采:“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当时我不免有些看不惯)。一看到他,我立刻就想起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名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
叶公超本可在文学上一展才华并取得骄人成就,却阴错阳差步入政坛。
晚年叶公超应召回台,却没想到整个台湾竟从此成为一座监狱:禁止离台、“有务(身边有特务)而无政(政事不准问)”、“小便有人随同保护”,长达二十年的监视、软禁、愚弄。他怎么也想不通,当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大使,怎么就沦落至此等境地?
在他死后多年,这一谜底才算是揭开。黄天才《沈昌焕密电 叶公超去职》(台北《传记文学》53卷26期,1998年12月):当年激怒蒋公,并使蒋公急电召回叶公超予以免职的,是叶公超在美国对蒋公的不敬批评,似与叶公超不赞同否决外蒙一事无关,至少无直接关联。
叶公超晚年的时候曾遗憾的说:“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倒有些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直到临死前的前天晚上,他还对前来拜访的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这显然是一种至死方悟的人生遗憾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