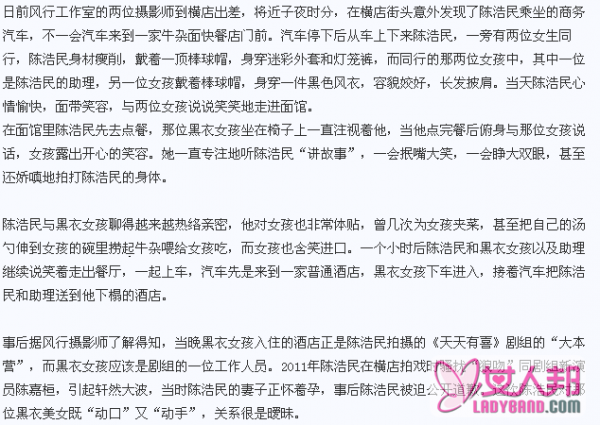【悭吝人拼音】以色列式《悭吝人》的宿命
近年来,北京人艺每年都会引进一两部以色列的戏,且口碑都不错。以色列戏剧,俨然已经成为首都戏剧界的一个期待。但今年以色列哈比玛国家剧院带来的《悭吝人》,多少有些让人失望。
莫里哀的《悭吝人》,就主题来说,只要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就不会过时,金钱欲望对人的异化和对家庭伦理、爱情的破坏,仍能显著地启发当代观众,因此这部17世纪的喜剧在21世纪上演,创作者不必花费太多精力重新挖掘主题的现代意义,只要在舞台上充分营造出喜剧氛围就能获得成功,若有所创新则能收获惊喜。

在以色列哈比玛国家剧院的演出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
人物造型上:利用了阿巴贡扮演者原本的谢顶特征,其他人物将其两侧仅剩的头发揪成尖形,进一步丑化了这个吝啬鬼的形象;厨师兼马夫的帽子和围裙均被巧妙两用,既符合剧本的规定情境,又加强了阿巴贡的吝啬特征……

舞台调度上:开场,阿巴贡将一摞钱藏在地毯下,后卷起地毯时险些没找到虚惊一场;阿巴贡怀疑男仆偷窃搜身,逼其一件件脱衣服,仅剩内裤还要搜,男仆捂住下身说“这是我自己的”;克莱昂特将钻戒骗到玛丽亚娜手中,阿巴贡心疼得晕厥;末场,昂赛姆先后三次主动掏钱,都被阿巴贡快速塞进钱匣……

但在更多的场面中,表演都较为写实、刻板而沉闷,喜剧效果几乎只来自文本,而在父子发现相互借贷真相、媒婆与阿巴贡过招、瓦莱尔和阿巴贡打岔等闹剧性场面中,平实的表演甚至为文本减了分,观众自然也笑声寥寥。

我没有看过对莫里哀创作影响深远的意大利即兴喜剧和法国民间闹剧,但我猜,当年莫里哀亲自扮演阿巴贡的演出,台上一定充满着插科打诨的夸张表演,台下也一定笑声一片。作为完全靠演出谋生的剧团的演员和剧作者,莫里哀必须想方设法吸引观众,不让他们睡着——第四幕结尾阿巴贡与观众互动的场面设计也就不难理解。
而以色列戏剧,从近年来引进北京的剧目来看,无论是卡梅尔剧院的《安魂曲》、《手提箱包装工》,还是盖谢尔剧院(由俄罗斯移民组成)的《耶路撒冷之鸽》、《乡村》,多是现实主义表演风格的悲剧,即使掺有轻松表演,也都蕴含沉重感伤的主题。
如果说,由于没有全面考察,以色列戏剧基于民族经历而形成独特气质的结论尚显草率,那么以色列学者肖什·阿维戈尔在1996年出版的《以色列戏剧》一书中确实说过,“时至今日, 以色列的戏剧从未被看作是‘单纯的娱乐’或者‘一次单纯的审美之旅’。”
阿维戈尔同时指出,1917年建于莫斯科的哈比玛国家剧院是一家以意识形态为根基的剧院,从它建成之日起就担负着宣扬犹太人民族运动、犹太人国家发展和文化宣扬的责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演不出莫里哀式的闹腾,或许并非偶然——阿巴贡与观众的互动,明明可以让观众玩得更热闹,演出却止于剧本的规定行动。
当然,硬币还有另一面。阿巴贡知道儿子对玛丽亚娜的真情后,原著中只是威胁要棍打“不孝子”,演出中竟真的动了手,却反被儿子推倒在地,儿子本欲离去,却回身扶起阿巴贡,此后父子间仍旧剑拔弩张——对于亲情这唯一的温情处理,在全剧中是如此跳脱,由此强化了观众对父子关系这条全剧主线的意识和思考。
《歌德谈话录》里有言:“《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的。”但据说卢梭不能接受剧中父子间的反目要挟,认为父亲固然不像父亲,儿子却不可以不像儿子;进而到了19世纪初,德国翻译家把剧中父子关系变成亲戚关系,削弱了讽刺的尖锐度。
此次以色列的艺术家,以特有的敏锐和才能,表面上一定程度满足了卢梭的伦理要求,本质上却彰显了歌德发现的深刻悲剧力量。
更大的妙笔在演出结尾,阿巴贡抱着自己的钱匣独自坐在舞台一隅,被一束聚光灯直射着,其他人提着箱子排队离他而去,几张纸币从空中飘落……演出一改原著的喜剧结尾,渲染出主人公孤独落寞的悲剧色彩。这个结尾,有着以色列卡梅尔剧院《手提箱包装工》的视觉形象,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演绎莫里哀《无病呻吟》结尾的悲剧内涵。
我相信,若整体的喜剧效果得到充分体现,点睛的悲剧色彩将使演出产生更加震撼的艺术效果而臻于完美;但如今,前者的基础没打好,后者即使再漂亮,艺术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这,或许就是以色列人演出《悭吝人》的宿命。
关键词回复关注北青艺评,回复下方红字可以查看2月精选内容
电视剧
国剧的虚胖浮肿 日韩的清新可人
少帅
“洗白大导”洗白“少帅 ” 把他变成历史人质的二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