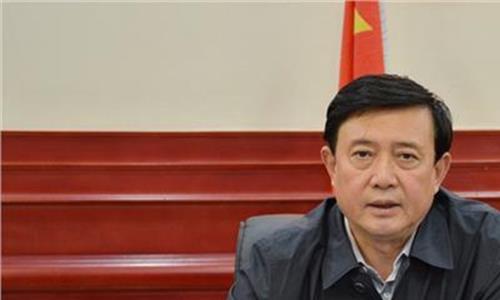赵燕侠简介 赵燕侠口述: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
正当我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在艺术上不断有所突破的时候,中国的历史走到了难忘的一九六六年。光明和黑暗在中国进行着一场殊死的大搏斗,神州大地被搅得天昏地暗,我们国家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浩劫。我一个京剧演员也为江青所不容,必欲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对江青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我跟江青并不熟悉,一九六三年的年底,有一天她突然把我找了去,就在中南海里边的丰泽园私人请我吃饭。江青一见了我的面就假惺惺地说:“你是个人材,我发现你太晚了,真是‘相见恨晚’啊!

”吃饭的时候便跟我攀扯起过去的事来,她说:“我知道,你小时候受过苦,我小时候也受过苦,咱们是一个阶级、一条藤上的苦瓜嘛。因此,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接着江青便给我讲起了排演“样板戏”的问题。江青对我是笑脸相待,并谈了一些生活琐事,甚至她还告诉我:用的卫生纸,为了讲卫生,用的时候先拿熨斗烫一烫,可谓“关心”。

自此,江青经常用她的吉姆车派人来接我,让我陪着她看电影、看戏。
江青这个人,她说喜欢你时,看着看着电影就剥块糖放在你嘴里;她要不喜欢你时,动不动就翻脸,把你大骂一顿。我慢慢地感到,江青跟邓颖超、康克清这些老大姐不一样,她们对人是那么和蔼可亲、真挚关怀。而江青,对人总是那么矫情、是非、蛮横霸道,而且爱指手划脚,给你乱发指示,瞎布置任务。

我们有时按照组织系统,接受了市委布置的任务,她偏给你另来一套,还定要按照她的意见办,使人无所适从。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既认不清她的本来面貌,也识不破她的阴谋诡计,但觉得同她很难相处,就尽量躲得她远一些。
后来,她再派人来接我时,我能不去就不去,有时没办法去了,看戏的中间我就以去厕所为名“溜号”。当江青发现我不在她身旁,又让人去找我,我回来后,她恶狠狠地说:“我身边有老虎?”
“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江青有一次见了我,下命令似地说:“赵燕侠,你要揭发北京市委和你们团的问题,可以把大字报贴到他们大门上嘛!”我也不了解内情,哪能随便乱放炮,便没有按照她的指示去做,江青对我耿耿于怀。
一九六四年底,江青要北京京剧团排演《江姐》,要我扮演戏里的女主角江姐。第二年的三月份,她又要我们团去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并指出:“去了之后要戴上手铐、脚镣,坐坐牢房,体会一下当年烈士们的真实感情。”到了重庆渣滓洞,我们真的成了“铁窗面壁”的阶下“囚”了。
脚上是八斤重的脚镣,手上是八斤重的手铐。当年烈士江竹筠是渣滓洞里被敌人囚禁的重点人物,我也便成了“体验生活”的重点对象,把我单独放在一间牢房里,铁栅栏门一锁,吃饭时也不让我出来,从牢门空里递进两个窝头,里面还掺着沙子。
动不动就“提审”,折腾完了就拉出去“枪毙”,真是活活地折腾人。这还不说,最使人难受的是组织人参观,他们把我们锁在牢房里,组织当地一些不明真象的人来参观。群众把我们当成了真的“罪犯”,有的人站在我的牢门前议论说:“这一定是个要犯’,要不怎么她一人单独关押着。”我们简直被当成了动物园里供人观赏的动物。
还让我们搞了一次所谓“越狱”,那天夜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下着雨,山路泥泞,一路上也不知栽了多少跟头,后边还真有枪声。同志们水里滚,泥里爬,一会儿急行军,一会儿卧倒隐蔽,折腾了多半宿,把人累个半死。这叫什么“体验生活”,简直是居心折磨摧残演员。事后,我对这种“体验生活”有些不同的看法,不想传到了江青耳朵里,竟成为我“对抗、攻击江青”、反对京剧革命的一大“罪状”。
不久,江青从上海打来电报,叫《沙家浜》剧组的编剧、导演于四月十日前赶到上海,听取她的什么指示,也要我于四月十六日务必赶到上海,排戏练唱。我有高血压和肾脏病,那段时间病得厉害,本想回北京把病好好治一下,但为了演好《沙家浜》这个戏,我还是去了上海,有时身体实在支持不了,我就坐在一旁看别人排练,不想江青反倒说我“泡病号”。
在上海第一次彩排《沙家浜》那天,我病得厉害,只好由别人来演阿庆嫂。那天我也去了,没跟江青坐在一起,坐在了第一排,看了不一会就去后台了。江青派人到处找我,问:“赵燕侠哪里去了?”意思是让我去陪江青看戏。在后台,有的同志也从关心我出发,问我说:“你怎么不陪江青同志看戏呀?”我这个人,向来不会溜须拍马,尤其对那些霸道人物更是看不惯,叫我整天跟江青的屁股转,这样的事情我干不来。
我从小就有一种十分牢固的“凭本事挣钱,绝不靠邪的歪的”思想。我说:“干嘛呀,一个人看戏老得别人陪着。”其实,当时我对江青是: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我离你远远的。这次没陪江青看戏,她对我更是怀恨在心。
江青惯于对人使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派手法,对我也是这样。为了给人以假象,表示她对演员的“关心”,散戏的时候她假惺惺地对我说:“你感冒了,想必是带的衣服少了,我那里有件毛衣,等会叫人给你送来,是旧的,可别嫌脏。
”事后,她便通过当时上海市委的张春桥给我送来一件毛衣。我知道这个人很“是非”,我没穿,一直放在那里。有人劝我说:“那怕等江青同志来看戏时你穿一次,让她看着心里高兴。”我说:“我身体胖,怕把毛衣给穿坏了。”就这样我一次也没穿,后来不知为什么,江青又派人把毛衣拿走了。
我从上海回来后,病得更厉害了,便去中医研究院看了中医,医生强调要我好好休息,防止病情继续发展,给开了假条。这些事江青都知道,可有一天她见了我说:“你身体不好吧,看了吗?”我说:“看了,没看好。”不想她当面就跟我翻了脸,气冲冲地说:“什么没看好?咱们国家医学这么发达,我就不相信看不好你的病!”
后来,江青跟我们团里的同志讲:“赵燕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让我的大夫给她看,仔细检查检查。”江青定要在我的病上抓辫子,偷偷调我的病历看,她见是中医开的病假证明,没好气地说:“中医开的证明不算数,让她看西医!”有人把话传给了我,我很不服气地说:“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装病。再说中央也没有这个规定,说中医开证明不算数。”
这一来,着实惹恼了江青,下狠劲把我往死里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万人大会上点了我的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时间,“黑帮”、“现行反革命”、“戏霸”等棍子劈头盖脸向我打来,一些侮蔑之词满天乱飞。就连沈阳的大街上,都贴着“打倒戏剧界的大毒蛇赵燕侠”这样耸人听闻的大标语。我小小的赵燕侠竟成了江青兴师动众,重点“讨伐”的对象。
我们家更是被大字报包围了,门上贴了封条,一家四口被扫地出门,住在人家九平方米的一个危险的东房里。小会批,大会斗,关“牛棚”,强迫劳动,搞变相的游街,让我背着床板在前门大街上跑,一个劲地往死里折磨。但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梦想着有一天还要登台演戏。
后来,我被弄到干校,足足当了四年的“壮工”。在这期间,我成了“只适于劳动,不适于演戏”的专政对象,既不准我吊嗓子,更不准我练功,这对于我这个有二十多年艺龄的演员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强迫我离开舞台将近十年。要知道,这是我在艺术上能够得到锻炼和发展“正是时候的十年”,多么值得惋惜!一个演员,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剥夺了登台演出的权利。
古人不是讲过“苦雨终风也解晴”吗? 天总是会晴的。在摧残折磨中,我始终抱定了这样的坚强信念:我相信党,历史最终将证明我赵燕侠不是人民的敌人。我朦胧地意识到,江青这号人绝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她迟早是会完蛋的。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使我日思夜想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象浩荡的东风,吹散了满天乌云,我饱尝着一个演员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那种难言的欢畅,又重登舞台了。
记得,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一天,在首都体育馆纪念总理逝世的大会上,我为首都观众用京剧清唱了赵朴初同志写的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一首诗。虽说是一段清唱,但我却有些紧张。事先,我反复学习、理会了原诗的意思,进行了认真的琢磨和推敲,并请我们的名琴师李慕良同志帮助我设计了唱腔。
演唱的时候,一方面引起了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一方面觉得自己终于又能为广大观众放声歌唱了,不禁落下了眼泪。此时,我的心情是难以描绘的。
不久,我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闯王旗》,又陆续恢复演出里了《白蛇传》、《红梅阁》、《玉堂春》、《碧波仙子》、《花Ⅲ错》、《辛安驿》,《拾玉镯》等一些传统剧目。
自我重登舞台以来,经常收到全国各地一些观众的来信,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希望。今年我已是五十二岁的人了,从年龄上来讲,一个演员的青春期已悄然长逝,但我懂得,艺术的青春永远属于战斗着的人们。我就是不服老,这几年来,我每天着厚底,有时也扎大靠,坚持了练功。
我常常是上午练功,下午排戏,有时晚上还要演出,一天下来,对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确实够戗,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去年九月五日,登了广告我主演《玉堂春》。
但就在这一天我的血压升高到低压l20,高压180。这又是一出唱、念十分吃重的戏,是“回戏”,还是继续演出呢?想来想去,这场戏不能“回”,观众都在忙着大干四化,好不容易才抽出点时间来看戏呀。可不能让观众乘兴买票来,败兴退票去,无论如何这场戏要坚持演。尽管到了晚间我头昏得更厉害了,但我还是演出了,虽然嗓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可我觉得没有辜负观众,心里觉得舒畅。
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旧有的一些程式和套子,在某些方面已不能符合今天时代的要求。刚粉碎“四人帮”时,观众对传统剧的恢复演出十分欢迎,那是因为观众阔别传统戏十几年之久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观众本身也在起着变化。
不但要求题材、内容好,而且要求文学性强;不仅要求演员有技,还要有艺,并且还要有独特的风格。因此,摆在我们广大京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既要尊重传统,注意师承,但又绝不能蹈常袭故,陈陈相因。
这就必须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使京剧与时代合拍。我自己会的传统剧目在百出以上,加上解放后新编的那就更多了。但我目前经常上演的只有《白蛇传》、《红梅阁》、《碧波仙子》和《玉堂春》( 这出戏我只演“会审”、“监会”、“团圆”三折,不是作为“花案”来演,而是作为一出“冤案”戏来演),而《辛安驿》、《花田错》、《拾玉镯》等一些戏只是偶尔演一演。
为什么不多恢复一些呢? 我想,宁可少演,决不滥演。京剧怎样创新,如何改革,我愿与同行的一些同志们认真探索和研究,为京剧的不断发展和提高,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十年动乱,京剧艺术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提到重要日程上来。我作为一个老演员,今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青年演员。把自己身上这点玩艺尽快传授给她们,这是事业的需要,也是我应尽的职责。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决不松劲。(赵燕侠一九八O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