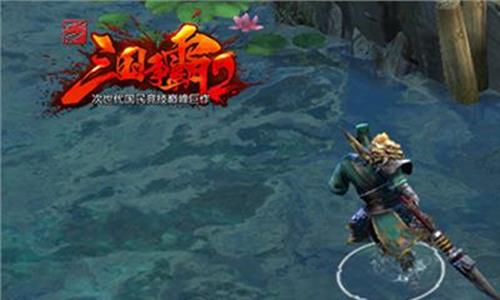钗头凤翻译 打工版《钗头凤》:春梦中 那株含笑乍开的朱砂梅
1998年,我十九岁,走出校门不久,在江门市高砂加工区亿都电子厂做仓库搬运工。能认识地,虽属偶然,但至少也有十年修造的缘分吧(佛家曰:十年修来同船渡,百年修来共枕眠)。
刚进厂不久,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厂里刚出粮,我拿了龙卡去建行取款。黑压压的人群,把取款台围得水泄不通。台内的营业员不断叫排好队、排好队,不排队不准取款。我自恃人高马大,把手伸得长长的,很快就把龙卡递了进去。没料到,又被营业员递了出来:“你来得最迟,到后边去。”我窝着一肚子火,索性跟着人群乱挤一通,嘴里还嗬嗬直叫。人群顿时东倒西歪,营业员火了,停止营业。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觑,擦擦汗,自觉排好队。

江门市中心东湖公园
江门高沙港潮莲大桥,当年亿都厂就在附近
我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排到后面去, 嘴里却骂骂咧咧的。骂够了,汗水干了,就耐着性子等待。突然,我眼前一闪亮:啊,我面前站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一袭青黑色的连衣裙,雪白的高跟鞋,披肩的长发如一泻瀑布。大约是经历了沧桑风雨之故吧,皮肤略显黝黑,眼角已有一丝细细的鱼尾纹。

但那张鹅蛋脸上,新月似的娥眉,墨葡萄似的眼睛,高挑圆滑的鼻梁,小巧玲珑的嘴巴,轻轻一启,便显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玉牙。啊,感谢她的父母,把她的一切一切都精心排列组合得恰到好处。
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人为的修饰之处,简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素看厌了那种不伦不类、妖里妖气的嗜脸,这是何等的清新俊逸啊。这模样,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想不起来。

真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因此,我实在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看着看着,心里就卜卜跳,姑娘也觉察到了有人在看她,头发一甩,脸偏向了一边。等她回头时,我便鼓起十二分的勇气搭讪道:“刚才,刚才你受挤了吧?”“没有呀,我根本就没有参与。

再说,挤来挤去有什么用呢?” 脆生生的普通话银银铃般的响过。她手握龙卡,始终与拥挤的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你不好意思挤过去,又恰恰显示了她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她笑盈盈地站着,活像一株含笑乍开的朱砂梅。
该她取款了,我又下意识地盯住她。只见她在银行回执的签名栏里,一笔刷成了“沈惊鸿”三个字,飘飘欲飞,活像-只飞鸿在翩翩起舞。“沈惊鸿,沈惊鸿”,多么动听的名字!我不禁细语呢哺着。哦,我想起来了,“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亭台。
伤心桥下清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这不是陆游的《沈园》诗吗?诗,是人生最好的伴侣。如诗的名字,可读可咏啊!“姑娘可是出自文学世家?”“哪里,我父母钟爱这首诗罢了。”“那他们也钟爱《钗头凤》,也有着陆游唐婉般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不简单,不简单!
”“哎,不要触景生情了,你才不简单哩。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破译我名字的人!谢谢你,明天见。”这时,她已取好了款,为我能破译她的芳名而深情地看了我几眼,眸子里似乎还闪烁着泪花。她莞尔一笑,飘飘悠悠地走了。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脱口而出:“凌波不过横塘路,便目送,芳尘去……”
明天见,明天哪儿见?我怎么没追上去问问她呢?我又默默吟诵着《沈园》诗,还在纸上写了又写。这首诗是当年年届八十高龄的陆游重游沈园,想起年轻时与表妹唐婉之间的恋情,心绪难平、挥毫写下的。那天,我也莫名其妙失魂落魄一般,吃饭时忘了筷子,冲凉时忘了浴巾。
夜里,好不容易入睡,一入睡就是满眼乍开的朱砂梅。一树梅花一树诗,每朵梅花里都镶嵌者“沈惊鸿”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这倒应了陆游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说实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的这种无可名状的感觉。以前都从未有过,包括十年寒窗,包括这家“入其厂门,靓女如云”的电子厂。正如《诗经》所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呵。
邂逅。昙花一现的春梦,空扰我心。星期一上班,我还是把心收不回来,我能到哪里见到她呢?午休时,我又发疯似的往建行跑,希望能见到她,希望能捎给我一丝意外的惊喜。可最终还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刹时我又觉得自己难免有点卑微,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很怕与女孩子正面接触,跟女孩说话就口吃,就脸红。我一直崇尚歌德说过的一段话:“二十几岁的爱情是幻想,三十几岁的爱情是轻佻,人到四十岁才明白---原来真正的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我还不到二十岁就……我卑微了,轻佻了,不可思议了!
亿都厂的仓库在五楼,其余楼层是车间。下午,我恍恍惚惚拉了一车物料下四楼。刚开车间门,就与一个女孩撞了个满怀。我正想数落她几句,那女孩却甜甜一笑。“啊,你不就是……”她不回答,轻吟道“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
”真是她!一张迷人的笑脸,声情并茂的吟诗声。只是那清一色的蓝工衣,只是我没想到她就在这里。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的心快要蹦了出来,转过身去,竟忘了拉车。默默地看着她从工衣柜里拿出碗来在热水器前接水喝,默默地记住她工衣柜的编号是“458”。她见我这副模样,脸一红,随后又笑:“快,上班呀!”我这才捂着火辣辣的脸拉车离去。
向来不修边幅的我变得整洁起来:衣服要日日换,镜子要时时照。以前把头发留得老长,现在每个星期都要去发屋修整修整。送往四楼的货多而繁乱,以前总是百般推诿给他人,现在却要抢着送。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知道她的工位就在四楼车间的右手边,那里还有我一个老乡妹;我只知道每每路过她那里,总要想方设法多看她几眼;我只知道那里有一张一往情深的笑脸,有一双纤纤玉手在电子元件上飞舞;我只知道有时四目相撞,就会撞击出心灵的火花。
那是诗,艾青说,诗是心灵撞击的火花。
不久, 我就在老乡妹那里打听到她是喝洞庭湖水长大的,难怪有那般的灵气和秀气。她是组长,办起事来干净利落。名字如诗,说起话来也有诗情画意的。听她讲话,就像在听百灵鸟唱歌。我说老乡妹,你亦有同感啊。她说本来就是嘛。
她还打一手好五笔字哩。可惜无人提拔,干了几年还是蓝领。她的性格虽开朗,但也很孤独。一下班就趴在书堆里不出门,据说是迷上了一个叫做什么斯的女神。这几年来,她都未回过家,也不见她收到过什么信函。再要好的人打听她的家世她都笑而不语。
还有,她不喜欢跟异性讲话,连电梯也不乘,上上下下都走路。她说那是是非之地,最好避而远之(这一点,厂里确有先例。多么矜持的姑娘!你为什么处处都有种戒备心理呢)。“喂,你打听她这些干嘛,是不是想……她可大过你呢。”“去去去,连缪斯都不知道,还多嘴多舌的。大,大又怎样,燕妮不是比马克思还大四岁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迭。老乡妹抓住了话柄,嘻嘻一笑,噫,不打自招了。
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举手投足,都实实在在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无论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我都能感悟到她那种特有的轻盈的脚步声。不用看她,保准知道她就在我的前方后方,左面、右面。只要有心见到她,保准知道她在什么时间会出现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还会与哪些姐妹们在一起。
但是,我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不敢向她表白点什么,甚至连话也不敢对她说。她是我心目中圣洁无瑕的女神,我不敢对她有所亵读。况且,我是个很保守很传统很现实的人。
我不敢祈望什么,因为我是个搬运工。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外资厂里,我是个在世人心目中只配与一辆破人力叉车为伴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人都可以用来肆意发泄吆三喝四的搬运工啊!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歌德的那段爱情名言,亦在我思想里根深蒂固。
可是,我毕竟是热血沸腾的年龄,情欲于中,不得不发之于外。我为她写了好多诗,但一个只能做搬运工的头脑里能储藏得了多少诗料呢?只有将写成的诗又丢进废纸篓里。于是我就来个借花献佛,借别人的东西,发泄自己的感情,把它写在一张小小白卡上,利用星期天无人时塞进她的工衣柜里。我以为此法甚妙,神不知鬼不觉的,有距离,有退路,少尴尬,少麻烦。
第一次, 我录成了则一高山流水会知音的故事。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里弹琴,樵夫钟子期竞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操。高山流水会知音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
我是第一个能破译她名字的人,不敢言及爱情,但能否成为知音呢?何为知音?我想知音是不受性别、年龄、地位等条件限制的。但父母、恋人、亲戚、同事不一定就是知音。知音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音是人生最高境界的最完美的朋友。茫茫人海.知音难览呵!要不,伯牙怎么会摔琴绝弦,终身不操呢?
高山流水会知音
我未署名,我看见那一树梅花姚姹紫嫣红。
她没有丝毫的反感之意。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又向她推出了当代那些名家们写的富有朦胧味,飘渺感,能表现出一种孤独无助、寂寞难耐、欲爱不能的诗作。渐渐地,我看见那一树娇妍的朱砂梅在沉思。
也许,她还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她在猜测是谁如此无礼,三番两次地来扰乱她的心和生活秩序。于是,我学写了一首诗给她:“我不是蓝天唱晴的鸽哨/你不必徒劳去寻找/我不是衍生的佛光/你不必回昨顾眺/热烈的夏天不属于我/富庶的金秋不属于我/倘若有一天,你又步入/乍寒乍暖的风雨小道/透过溟蒙的雨雾/会传来我嘶哑的呼叫。”
呵,朱砂梅变得坐怀不乱,如沐春风了。
能让她开心,我也很高兴。路过她那里,我禁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可惜,我高兴得太早了。那天,我路过她那里,意外地发现她将我写的诗传递给她的小姐妹们看。她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顿时逃奔而去。我疑心我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疑心我有芒刺在身,所有的人都在背后指责我、鄙夷我。
我为什么要向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子表露那些呢?我为什么要自不量力、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呢?“多情自古空余恨”,现在,我该自食其果了。我不敢下四楼了,我想那一树梅花变成了无数锐利的刀枪,直刺我卑散的灵魂,枯稿的颜容。
过了几天,我心灵深处又在含冤叫屈了。我并没有向她祈望什么呀。这只是我心灵空间的一种奇托,情感世界里两个超负荷的载体错了位而撞击出了一些文字。为什么要出现错位呢?我却不明白。我只认为这与自己崇拜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法没有背道面驰。我只认为这是舒婷的一首诗中说的:“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凤一个个吹灭。”
我想向她作出点解释,来洗涤我的错。但是,见到她,我又不敢说话,不知说什么好。她亦是把我望望,欲言又止,拂袖而去。后来,她就有些有意避开我,我的心就蔫了。
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她没有来上班了,顿时焦躁不安起来,像丢了件什么宝费东西似的。中午吃饭,我意外地发现我的工衣柜里有一封信:
峥嵘君:
你好!谢谢你的一片深情,谢谢你为我写成的好诗(还谢呢)。认识你,是我一生的幸福。你給我多少欢欣和鼓舞,我永远忘不了,直到天荒地老(这是真的吗)。“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一切,我都能读懂。你说得对,高山流水会知音,我们是知音,一开始就是。要不,你怎会轻而易举就破译了我的名字?
其实,那天的事,你误会了。我感受到你写的诗美极了,“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我就拿出来与她们一道分享,别无他意。她们向你投来的是青睐的目光啊!你太自卑,太多虑了(原来如此)!
可是,我要走了,不得不走了。生活,使我要“宠辱不惊,观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我走了,倘若有缘,我的故事就等明天相告。海明威说过,“明天,太阳照样开起。”不过,明天的男孩,可要勇敢些哟!倘若无缘了,一切就随风而来,一切就随风而去吧。请珍重、珍重。
握手!
惊鸿
1998年11月6日
就这样,生活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心底不知隐藏了多少孤独、无奈的惊鸿姑娘,“挥一挥衣袖,不带一片云彩”地走了。走的时候,没有长亭短亭,没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天,天下着雨,我收起信,一口气跑到江边,仁立在风雨中,心中的歌声起:“芳草萋萋,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她走了,没有带给我任何消息。她走了,我成天萎靡不振,度日如年,味同嚼蜡。一天晚上,我在昏昏噩噩之中做了个梦:
惊鸿姑娘跟着一个高贵的少年飞走了。我跨越西江,飞渡湘江,追寻到了洞庭湖边。洞庭湖上矗立着一座高楼,很有点像曹操的铜雀楼。惊鸿姑娘进去了。
唉唉,那位少年好英俊潇洒。那座铜雀楼好深好高。那楼台上守护着骠悍的打手,他们的样了好吓人,他们的腰间挂着投枪匕首……
我惊呼一声坐起,汗涔涔而泪潸潸了,直叫:“惊鸿,惊鸿,你在哪里?”
第二天,我发特快信到《知音)杂志社,在“吉祥鸟”里刊登了这样的文字:“惊鸿姑娘,不要忘了,也不要拒绝,那些值得珍爱的美好的记忆。有人在原地等着你。”
我相信她定会看到这段文字的,因为她曾对我说过她酷爱(知音》,每期必读 ,面且是细细的读。
果然,她来信了。我见到她信封上飘洒的字体就欣喜若狂。可惜的是,她在发信人的地址姓名上注明的是“内详”。
信拆开了:
第一张,是白纸;
第二张还是白纸;
第三张,又是白纸;
不过,第三张白纸的末尾端端正正地写了两个较大的字:“晚了!”
这两个字和一个感叹号好像被水渍过,有些模糊,有些发毛。下边有一破折号和三个字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