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和尚说不得】布袋和尚为什么叫"说不得":暗讽明初文字狱
凡是读过金庸《倚天屠龙记》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段情节:当蛛儿被吸血成性的青翼蝠王韦一笑抢走后,张无忌狂奔于大漠黄沙之上,试图追上韦一笑从而救回蛛儿。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布袋和尚尾随其后,将张无忌套入了乾坤一气袋中,并背上了光明顶。

这个布袋和尚的名字很有趣,叫做“说不得”,禅味十足,很符合布袋和尚之名。佛曰:“不可说”,一落言筌,便失第一义,所以佛祖拈花,伽叶微笑,说则不得,言语日近而道心日远,至于禅宗对答多以机锋行事也是出于同一考虑。除此之外,“说不得”一词还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社会文化禁忌,这一点上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倒是相差不远。

《倚天屠龙记》的时代背景是元末明初,最终朱元璋窃取了明教的领导权,建立了明朝。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也是僧人出身,在“说不得”一词的理解上却殊乏禅味,他所喜好的是作为禁忌的“说不得”。

按照赵翼《廿二史劄记》中“明初文字之祸”条目所载: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其中有以“睿性生知”之句而被杀,原因是“生知”一词在发音上涉嫌影射“僧”字,而朱元璋本人在早年时曾做过僧人;另一位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其中用了“圣德作则”一语而被诛,原因是“则”字的发音上接近“贼”,涉嫌影射朱元璋参加红巾军的经历。

“僧”字说不得,“贼”字说不得,连和它们发音相近的字也说不得。蒋镇和孟清因为仅仅说了其中的一个字就被砍头,与后面徐一夔的例子相比显然有点冤屈了。
赵翼引《闲中今古录》所载,杭州教授徐一夔所作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见以后龙颜大怒,将徐一夔处斩,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
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十二字中“僧”和“贼”的忌讳全都触犯,徐一夔倒也算得上是罪无可恕了。笔记与野史记载中难免有一些虚构不实之处,然而过去君主高高在上,由于臣子们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而行使手中的生杀大权,原本不足为奇,更何况其中或许尚有政治因素和其它隐藏的诸多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统治者乐此不疲地玩弄的这种血雨腥风版的“说不得”的政治游戏,其目的显然不单是发泄一时的个人情绪,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在社会、政治、文化场域内建立一套禁忌符码来巩固君主的绝对权威,平衡、制约各种政治势力,禁锢人心,钳制舆论,确保其家天下的局面。
此种“说不得”游戏中体现的阐释学尤其引人注目。阐释权掌握在帝王手中,主观随意性较大,原本歌功颂德的臣子,却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惹祸上身,如此这般,天下士人难免提心吊胆,人人自危。那是不是一旦破解了这套禁忌符码(比如不说“生”字,不说“则”字,便可享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言论乐趣呢?事实上未必如此。
朝廷上还有各式的帮凶,整日里忙着影响和引导帝王的阐释,试图从言语中读出点什么东西,发现几个大逆不道的词汇,从而达到相应的政治目的。
赵翼在“明初文字之祸”条的最后提到,由于朱元璋当时崇尚文治,导致不少开国武将不满,告以“文人善讥讪”之名,并以张九四(张士诚的小名)为例,说他对文人厚待有加,而文人在给他撰名时却取了“士诚”这样的名字。
朱元璋开始觉得“士诚”这个名字也不错,于是那帮武将们便积极发挥阐释的主动性,说《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的句子,最后导致朱元璋在阅览奏章时,“动生疑忌,遂起明初文字之祸”。赵翼归纳的“明初文字之祸”其起因未必正确,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关于语言的禁忌符码永远也无法得到彻底的破解,因为随便一个词都会经由某种人为创建的关联而形成对禁忌的冒犯。
回到《倚天屠龙记》,当张无忌问布袋和尚的名字时,布袋和尚道:“说不得。”可怜的张无忌未能领会,继续问道:“为什么说不得?”布袋和尚回答:“说不得就是说不得,还有甚么道理好讲!”此种封建专制体制下“说不得”的阐释游戏,颇似布袋和尚的随身法宝乾坤一气袋,袋口大张,随时就会套在别人的头上,而且还不许口袋中的人有任何追问。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禁忌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那几个词语本身,有效地制造一种了无处不在的威胁,再加上阐释构建关联的随意性以及朱元璋“治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对明初士人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强烈挤压,造成“天下股慄”的局面。
明初士人若想明哲保身,自当谨记布袋和尚对张无忌的告诫:“你已落入我乾坤一气袋中,我要取你小命,你逃得了么?你只要不动不作声,总有你的好处。”据《坚瓠集》记载,朱元璋有一次进入一座寺庙游玩,发现里面悄无一人,只看见壁间画有一个布袋和尚,墨迹犹新,旁边题有一偈:“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世上没有几个人像张无忌那样神功盖世,能将乾坤一气袋胀破,那些喘不过气来的明初士人们所祈求的,也仅仅是将袋口放宽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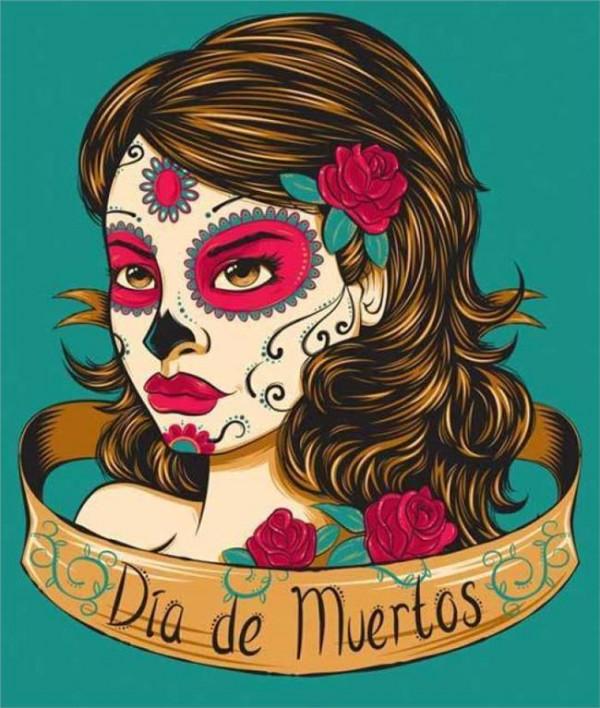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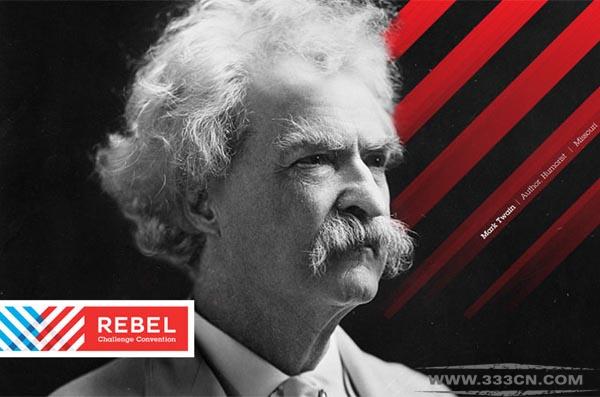

![>山口百惠-《山口百惠超级精选》香港版[ape]](https://pic.bilezu.com/upload/c/97/c974e210a0eebc5011c965f5f3d59a6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