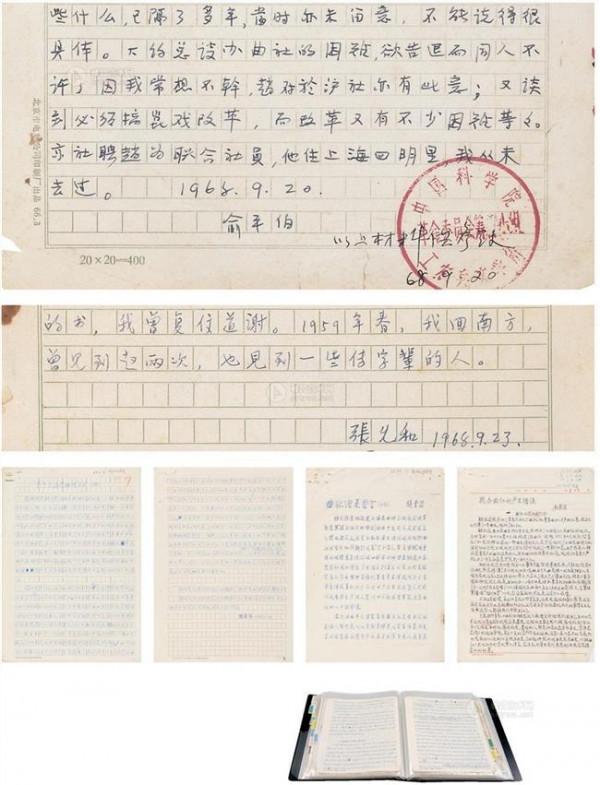桃花扇昆曲 《桃花扇》:什么是彻底的悲观主义?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说:“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他认为《桃花扇》和《红楼梦》都窥视到了人生痛苦的本质,并寻求解脱之道,属于彻底的悲剧。《红楼梦》侧重写人生,《桃花扇》兼具政治与历史,前者的解脱出于自我顿悟,后者则是由旁人指引,不过它们在哲学意义上同属于彻底的悲观主义。

悲观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生存意欲”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人就是意欲的奴隶,受到意欲的驱使,不断地去摸索和劳作。意欲满足则无聊,不满足就痛苦,在无聊与痛苦之间,只存在转瞬即逝的快乐,人生的本质就是“生存意欲”在求满足而已。

在“生存意欲”之后,还有“男女爱欲”,它的威力比“生存意欲”还甚。前者求生存,后者求繁衍、求延续生存,因此“男女爱欲”无尽,而“生存之欲”有限。
要想摆脱痛苦,只能否定意欲,可是否定意欲就意味着否定了人生,因此,要直面人生,就得承认它在本质上是痛苦的。文明的进步丝毫不能缓解意欲的压迫,但有一种东西能够使人暂时摆脱意欲的束缚,进入到纯粹知识中——这种东西就是艺术。

艺术能给人带来美感,使人忘记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得以纯粹地观照外物。其中第一种美感叫作“优美”,这种美感能使我们的内心回复到宁静的状态;另一种美感叫作“壮美”,它能够使“生存意欲”破裂,消隐了起来。过去我们总是服侍于“生存意欲”,求生欲使我们舍弃自我,甘心为奴,不能认识人生的本质。而“壮美”却打破了这种幻想,使厌世情感超过了求生欲,让人摆脱意欲的统治,能够自由地观照人生。

悲剧就是一种产生“壮美”感的艺术品,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感发人的恐惧与悲悯之情,感染人的情绪,使人的生活之欲消退,进入到纯粹认识中去,让精神受到洗涤。
基于此,叔本华把悲剧分成了三种:
对于前两种悲剧而言,分别出自偶然性和必然性,遇见极恶之人的交构从而酿成悲剧,这是比较偶然的现象;而受命运的愚弄,产生悲剧,这又是必然现象。唯有第三种悲剧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而且是自然而然。第三种悲剧意在说明不幸不是例外之事,而是人生所固有的基调。当你生存在一个悲惨的世界中时,个体的悲剧总是免不了的。
《桃花扇》融合了三种悲剧,并且在总体上属于第三种悲剧——侯方域想要置身于国事之外,寻个清净安乐之处,结果总是不免要坠入时代的大悲剧里。
《桃花扇》正文有四十出,讲述的是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史,故事始于崇祯十六年,终于弘光元年,实际跨度仅三年而已。开头的《试一出》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由一名九十七岁的礼赞出场介绍故事内容,他自称:
“离合之情”就是男主角侯方域与女主角李香君的聚散离合,是个人之小悲剧;“兴亡之感”是弘光政权的兴起与覆灭,是亡国之大悲剧。在大悲剧的背景下,小悲剧不断上演,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种悲剧”——生存在亡国、亡天下的年代,悲剧总是无法逃脱的,它的发生,实乃自然而然,不可避免。
不过侯方域和李香君并非一开始就瞥见人生的这个真谛,他们一直在抗争、挽留、幻想,直到最后一出,经张道士点化,方一念顿悟,寻得解脱之道,这便是《桃花扇》的伦理学之价值。
跟《红楼梦》一样,《桃花扇》出场人物众多,叙事线条复杂。如果说《红楼梦》以五十四回为分水岭,那么《桃花扇》也大致以二十出为分界。前面讲述的是侯方域与李香君从相聚到分离的始末,并叙述了弘光政权的兴起。后二十出头则讲了弘光政权的灭亡,侯方域与李香君再度重逢,却终悟一切皆如梦幻泡影,最终遁入空门。
侯方域最初并不关心国事,认为在衰落之世,还是能够寻得个安居之地。他一出场就说:
那时正是崇祯十六年二月,亡国前夕,侯方域却还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归故乡洛阳,结束流亡生活。他的好友吴应箕说:
国家危在旦夕,江南的士君子们仿佛若无其事,还在消遣春愁,可悲可叹。之后他们一起去听柳敬亭说书,柳敬亭给他们讲了一个《论语》的故事,说孔子整顿鲁国朝政,乐官们纷纷逃窜,各自投奔了不同的国家,只有四个人选择退隐江湖,最后他说:
这其实是在暗示摆脱痛苦人生的解脱之道,人生犹如迷津,四处都是桃花阵,哪里都是痛苦,想通过满足欲望来“别处寻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欲望总是接连出现,怎么可能平复得尽呢?唯一的办法还是找到桃花源头,才能寻得解脱。因此,柳敬亭最后告诫侯方域说:
后来,确实是柳敬亭引导侯方域入道,在南明灭亡后,他也最终退隐江湖,变成了一名渔翁。不过,当时的侯方域还在迷津之中,他在江南“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阮大铖想趁机拉拢他,便请杨文骢做媒,为侯方域娶了青楼李贞丽的女儿李香君。新婚之夜,侯方域赠与李香君一柄宫扇,做为订盟之物。
谁知李香君知道嫁妆出自阮大铖之后,坚决不肯收,这使得侯方域开始知道名节的重要性,他说:“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从这时起,侯方域与李香君逐渐卷入弘光政权兴亡的悲剧之中。个人的遭际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大悲剧的左右。
婚后,侯方域过得十分美满,当他再次找柳敬亭听书时,柳敬亭却告诫说:
果然,侯方域本是好心修书力阻左良玉引兵南下,却反被阮大铖污蔑为通敌造反,只能仓皇逃出南京,与李香君从此分别。之后便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发生了“甲申国变”,悲剧的大基调已经形成。当时,侯方域面对三镇内讧,知道天下大势已去,不仅哀叹:“不料局势如此,叫俺怎生收敛。
”他也察觉出大悲剧即将来临了。之后,他又跟随高杰驻防黄河,本以为能够“遂了三年归志”,结果却是清兵南下,中原沦陷,只得孤舟南逃。
彼时的李香君因拒绝改嫁、守楼不下,导致血溅宫扇,她也只得哀叹:“桃花薄命,扇底飘零。”之后又被抓入宫中,不得自由。侯方域回来时已是人去楼控,独有山人蓝瑛在里面作画,于是侯方域在画上题诗:
仿佛醒悟了柳敬亭的指点,想要寻个桃源以避开乱世之大悲剧。之后,侯方域与吴应箕等皆被阮大铖投入监牢,他们与柳敬亭再次相遇,大家步月狱中,悟了天下崩坏的现实,想要一起“避乱秦人,同话渔船。”距离悟道解脱已不远了。
弘光元年五月,清兵大举南下,南京城即将沦陷,百姓都争相逃亡。李香君自宫中逃往栖霞山,侯方域等也在老礼赞的带领下,同去栖霞山避乱。
栖霞山上住着个出家的张道士,他一出场就道破了人生虚幻而痛苦的真谛,说:
原来人生就像一个傀儡在哄闹,它时而发笑、时而恸哭,却没有毫无意义,倒不如出家前往“玉壶琼岛”,超脱出痛苦之外,获得解脱为好。
悲剧思想是共通的,莎士比亚也有类似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他在《麦克白》里写道:
如果我们能看破人生的虚幻,那么就离解脱不远了。
在最后一出,当侯方域历经离合兴亡之后,他一登场就说:“久厌尘中多苦趣,才知世外有仙缘。”这说明他已经挣脱了“生存意欲”的束缚,厌世感已经超出了求生欲,得以观照人生。之所以未能完全顿悟,是因为香君尚在,“男女爱欲”还未断绝。
当侯方域在水陆大会上与李香君重逢时,他对人生幸福又充满了幻想,想要“夫妻还乡”,重新回到“生存意欲”的欺骗中,在悲惨的世界里谋幸福。不料,张道士却撕裂桃花扇,喝道:
对此,侯方域认为“男女爱欲”无法超脱,反驳说:
不料,张道士大怒道:
连家国君父都没了,天下也已经沦亡了,这么一点男女之情又如何守得住呢?张道士明言,要求得解脱,首先得直面人生的痛苦,而不是在男女之欲的掩饰下继续逃避。如果侯方域与李香君还乡了,那么他们只是继续苟活而已,或者剃发易服,或者含辛茹苦,就像那些逃往各国的乐工一样,在迷津中“别处寻主”,终究没有直面人生的痛苦,而是想规避它、逃脱它,到最后只是又迎来一次新的悲剧而已。在悲惨的世界中,个体的幸福是无法达到的。
最终,《桃花扇》打破了“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大团体惯例,而是写侯方域与李香君双双顿悟,选择了出家。这样,《桃花扇》就跟《红楼梦》一样,把悲剧写得非常彻底,将痛苦感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种悲剧的目的不是要教人躲避痛苦,而是要求人正视痛苦,并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办法,对此它们开出的药方就是“修行”,就是出世,用这个办法来拯救人生。
至于这个药方是否有效,那便是另一个人生哲学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