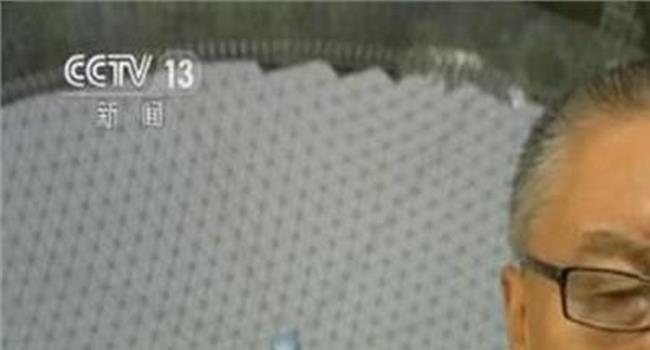南仁东简介
南仁东先生从始至终都是一位浪漫的冒险家。这种浪漫冒险从他在清华大学时利用大串联的机会,毫无负担地游遍广州到新疆天山的大半个中国就开始了。在吉林长白山里的下放劳动车间,他成了开山放炮、水道、电镀和锻造的行家里手,临了还当上了厂里的技术科长。他头发留得很长,爱画漫画,但总被驻厂军代表盯着,就改画毛主席像。

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从前喜欢穿一件很贵的黑色皮夹克搭配墨镜,还拥有一套纯白色的三件套西装——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一位被认可的科学家。但他早已坐过这个领域最受尊敬的位置: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IAU DivisionX)主席。

直到他去世前一年的夏天,71岁的老头穿着汗衫短裤,向人炫耀:「瞧我这一身名牌。」他曾在多个国家工作,几乎走遍地球上的每个角落,这让他很骄傲。他后来上了年纪,腿脚不好,但如果你去扶他,他会毫不犹豫地让你滚到一边。
他难以想象自己会成为某项重大科学工程的实施者,他是个讨厌负责任的家伙。对他来说,大望远镜更像一个巨大、好玩的玩具,地球上的事早难以满足他,他只是很单纯的,想要看得更加宽广、更加深远。但做事总是很难,20多年前,几个重大的全球望远镜计划都不带中国人参与,百般努力,无一而成。
所以当10多年前,十几个灰头土脸的中国科学家经历了几个月的探索、走了几百个小时的山路,终于从「大窝凼」的洞口钻出来,看见头顶的那片璀璨星空和吃惊地望着他们、电都没有通的12户村民时,「没有人仰望星空?」南先生一定会疑惑这句话,我们不是一直在做这件事吗?
「这里好圆。」他说道。
这位极爱面子的老人一定更愿意因为天才构想和艺术成就出名,而不愿被描述成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劳动模范。但后面这点,他也的的确确做到了。他直接在中国科学学院会议上管院长路甬祥要名分、要钱,谁的面子都不给。国际评审专家对他的评价是:「南,英语说得不行,但在伸手要什么的时候就说得特别清楚。」
他曾经说过:「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特别多的理想,大部分时候是不得不做。但人总得有个面子,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11亿,当时令人咋舌的大科学工程的价格,现在不过是一部电影的票房。一个不喜欢负责任的人,负起了责任。他拿到钱之前,吹牛,开玩笑,拿了钱之后,原来的洒脱就不见了。
他骂人,冲人叫喊,拍桌子吹胡子瞪眼,对领导更是肆无忌惮,「一副我确实不喜欢你我就骂你两句怎么了」的气势。他是FAST项目的明星,周围村民都认识他,他戴着印有自己名字的蓝色头盔,年轻的科学家谈起他两眼发亮,院子里养的狗只跟在他一个人的后面。这意味着他比谁去工地的次数都多。他跟工地上的工人倒是打成一片,河北来的水泥工人说:「老爷子好着呢,给我们买被子。」
他实在不是统领全军的好人选,他太过完美主义,什么事都想做到最顶尖;他同时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经常为别人夸大困难,担忧低估他人的能力。他本做的不过是追寻宇宙的深邃,但之前这些事过于琐碎烦忧。幸运的是,去年,世界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在他的努力下建成,中国人可以稍稍领先全球的,发现更多的脉冲星,观察到早期宇宙的蛛丝马迹,或是第一次接收到外星文明的电波。可以不必去看国外天文台的眼色了。
2016年9月25日年竣工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不太公平的是,相较于漫长的宇宙观测,人的一生太过短暂,很多像南先生一样的天文工作者,甚至没有亲自使用过经年建造好的仪器,人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但想必南先生并不遗憾,尽管临了也没评上院士,现在可能也没几个人记得那十几个从洞里钻出来的中国科学家,但他的一生已经活得足够宽广,就像探寻宇宙的宽广需要先有内心的宽广一样,他做到了这一点。他曾经不断思考,外星人是什么样?我能否见识到更有趣的宇宙画面?
「我们和猴子的DNA就差不到1%,而我们之间却是千差万别。我们甚至和苹果的DNA也没差多少。我们不知道海豚如何理解哲学,如何感受生活的幸福;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海豚知不知道我们如何理解……看来,在海豚和人类之间,即使我们不是唯一无知的一方,至少我们肯定是无知的一方。」
南先生度过了极好的一生,唯一有些遗憾的是他未曾拥有自己的宇宙飞船,否则他一定会在今年偷偷一个人驾驶它飞向太空,扭头看着身后望着他、尊敬地称他为首席的、目瞪口呆的家伙们,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