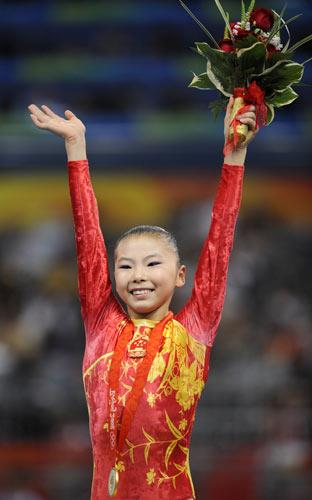庄周梦蝶歌曲 干春松:孔子梦周公和庄周梦蝶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奠定后世中国思想基本形态的诸子百家,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互相争辩而各自发展,从而构成中国思想发展的高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等,异彩纷呈。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

因此,不同的主张之间,往往构成对话关系,儒家和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是如此。尤其是儒家与道家之间因为人生态度上的差异和互补,尤其令人回味。今天,我希望通过两个梦的解析,来讨论儒道之间在人生态度上的差异,探讨古人对人生目标的理解。
所谓“两个梦”只是一个简略的说法,其中,一个是《论语》中的“孔子梦周公”,其实说的是孔子对于很久没有梦到周公的一个叹息。另一个梦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庄周梦蝶”,《庄子》书中有很多关于梦的描述和讨论,但均不如庄周梦蝶般深刻、富有哲理,因而也最能体现庄子哲学的复杂性。
通过这两个梦,主要是通过历代思想家对这两个梦的经典解释的梳理来展开。我们知道,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历代文人对它的解读,而不断能产生新的解释空间。在这些解读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历史和经典之间互相成就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因为新的解释的汇入,经典本身也不断地丰满。
当然,选择以梦作为切入点,我们需要作一个说明,即古人与现代人对梦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别,古人比较重视梦,在很多时候,他们把梦看作是对现实即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一个“提示”,而现代人更多是把梦看作是一种心理活动。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很多对梦的记载,这种记录通常会跟现实的境况产生关联。通过这些铺垫,我们首先来解读孔子的“梦”。
孔子梦周公
《礼记·檀弓》中记载了一个孔子做梦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名,是说孔子觉得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内容是这样的: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
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个故事在《孔子家语》中也有记载,内容几乎一致。这个故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孔子对自己的弟子子贡所叙述的一个梦。孔子说夏商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摆放灵柩的方式,并说自己既然梦到了殷商时期摆放灵柩的情景,他将之理解为自己即将要死的“预兆”。
其次,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感叹。孔子将自己视为泰山和梁木、哲人,但是“明王不兴”,他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难以有实现的机会了。所以,孔子对于自己生命的终结充满着遗憾。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一生的缩影,即有德而无位。对此,《论语》中则是通过“梦周公”来呈现的。
《论语·述而》记载道:“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我太衰老了!很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我们都知道孔子最为推崇周代的礼乐秩序,而周代的礼乐制度的完善则赖周公。周公,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按王国维先生的概括,周公通过宗法封建制度的建立从而构成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的建构,某种程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伦理基础。
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的批评和“吾从周”的信念,都显示了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秩序崩坏的忧虑和重构社会秩序的雄心。《论语·八佾》中: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丰富而完备,孔子遵从周礼。他还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孔子不再梦到周公的慨叹呢?
汉代的郑玄对于这句话的解读是这样的。他说:“孔子昔时,庶几于周公之道,不能究见之。末年以来,圣道既备,不复梦见之。”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孔子早年并不能真正了解周公之道,所以经常梦见以期待有所发现。而到晚年,孔子已经具备圣道之全体大用,所以就不用经常遇到。这种解释放在汉代的历史环境中,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在汉代,孔子被视为是为汉制法的,因此,他已经是一个秩序的建立者,因此,便可以不复梦见了。
同样是汉代的《白虎通》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大致可以佐证这样的看法。《白虎通》里问圣人是否自己知道自己是圣人,其回答是说孔子自己知道自己是圣人,其例子就是《论语》中“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即文王已死,孔子就以“文”自任。
宋代的解释有所不同,程颐说:孔子盛年的时候,一心想推行周公之道,所以在睡梦中,可能会见过周公。而到孔子老年的时候,认为周公之道难以在有生之年实现了。程颐说:“存道者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也。
”而朱熹则对程颐的解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这个解释,可讨论的地方很多。一般而言,孔子常说不知老之将至,因此,并未因为自己年老而放弃自己的志向。只是壮岁之时周游列国,希望有明王来实现他的理想,而晚年则将这样的理想寄托在删削诗书和教育学生上,因此,并不能说“无复是心”。
孔子晚年喜欢读《周易》,我们在讲儒家的时候,特别强调积极进取,且多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表达,这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态度,因此,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事情可能做不成,但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这就是儒家积极进取的一面。
对此,清代宋翔凤《论语说义》对孔子梦周公的解读,我觉得很符合孔子的一贯立场。他说:
昔者,孔子耳顺不逾,天纵将圣。年有壮老之异,志无衰盛之分。惟感周道之既衰,则思周公而无梦。“甚矣吾衰也久矣”,吾者,谓吾今日也;久者,谓自幽厉伤之,至今日而已久也。孔子谓周道之衰,当吾之世而益甚。如鲁之郊禘非礼,其精神已不能与周公相接。制礼作乐之意,吾将坐视其泯没。精神不交,则不复梦见也。周公其衰,之杞之宋,又不足征,此《春秋》之作所不能已与!
这段解释很典型地体现了公羊家解释经典的特点,也就是说,强调了孔子虽然不能直接制定社会秩序,但他是通过编定《春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褒贬来宣告他自己作为一个“制法者”而存在的。而且,宋翔凤也吸收了程朱解释《论语》的一些说法。不过,他并不认为衰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周公所制定的礼乐秩序的式微,因此,孔子不能坐视儒家理想的泯灭。
由此可见,对孔子之梦,在后世的解释中,多是从孔子作为道的担当者的角度,体现到儒家侧重社会责任感的价值倾向。这种使命感又表现为救天下的豪情壮志:一方面,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能弘道的精神;另一方面,天下无道,不能逃避,需要人来振危起弱。这种态度一直被后人所继承。
比如孟子。有一次他跟淳于髡关于“嫂溺,援之以手”进行了辩论。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古人说“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嫂子溺水,救不救?孟子说当然是要救,遇到特殊情况要灵活变通。有人进一步问,现在天下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你救不救?孟子回答说,要救,但不同的人挽救社会的途径不同。学者,主要是写文章来救天下。其实,后世的儒家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传播思想来救济天下。
这种思想在宋代还表现在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壮语,以及王安石的“共治天下”的思想。
所以,在孔子的梦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强调的对待人生应该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刚健有为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当然,儒家的思想中有些倾向也包含着“退让”和“妥协”。比如,《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就是说,大道如果不能推行于天下,孔子要乘坐着竹筏子到海里。钱穆先生曾将此解释为表现了孔子和平豁达的气象。
孟子也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给了人们一条退路,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发达了,要造福天下。如果没有机会,那么就做好自己,独善其身。不过,理解儒家这种倾向需要了解其前提。它的前提就是自己先要努力,首先要求道,求道不行再选择抗争或退隐。
就如孟子所说的那个“达”,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才能实现怀抱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在道家看来,儒家的行道之志是没有必要的,对于保全生命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以自己的想法来改变社会也会导致对别人的选择的干扰。所以我认为儒家所强调的刚健有为,更像是一个外表温顺、内心坚强的君子。而道家考虑更多的是,人怎么样去生活,而且是愉快、逍遥自在的生活。
庄周梦蝶
庄子一般而言,被看作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不过历代对于庄子和儒家的关系有别的看法,甚至一些人认为庄子可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这些问题很复杂。
庄子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比如就理想境界而言,儒家期待自己成圣成贤,庄子则向往坐忘和解脱。把圣人只看作是人生境界中的一个未臻完善的环节。而更高的则是“神人”“至人”。至人肯定是无所牵挂的,所以“至人无梦”。
由此,庄子的梦也没有孔子梦周公那么沉重。如果说儒家是一个温润而坚强的君子,那么道家一直在寻求如何才能快乐的生活。《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梦的故事,其主题是探究人的梦境与觉醒、生与死、快乐与痛苦。
《庄子·外篇·至乐》中有一段枕骷髅而托梦的故事。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庄子到楚国,遇到一个骷髅,向骷髅询问是因为贪生怕死、道德亏欠还是国破家亡而遭灭身之祸。问完后拿骷髅作枕头而睡去。夜里骷髅托梦给庄子,说庄子白天所问都是因为人生有所牵累。庄子借骷髅之口道出人生在世的拘累和劳苦,因此,死亡之后才能摆脱劳烦而获得快乐。
不过,在这个故事中,很显然还停留在一种“生不如死”的比较浅层次的超脱境界中。的确,结合《道德经》和其他的道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致认为:过于执着于对世俗的秩序的关注、社会责任的承当,是导致人们失去快乐生活的原因。
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层次来理解庄子,起码还不能理解《齐物论》中的哲学思考的深度。在《齐物论》中庄子讨论了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视野”问题,也就是认识方法问题,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齐不齐、以不齐为齐、物各付物。
所谓齐不齐,则是要消弭世界上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贫富差异啊等等。而以不齐为齐,则是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但是能发现不同事物可以有不同的乐趣。
这就好比《逍遥游》中的大鹏和小鸟,虽能力不同,但各自有各自的乐趣。而物各付物,前两个层次的升级,即不能把差异绝对化,每一种物种都充分实现其自己。在这样的思考中,庄子对“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就更为深入了。
“庄周梦蝶”的故事是《庄子·齐物论》的结尾,其内容是说: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说: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然飞舞在花丛草地上,轻松惬意,全然忘记自己本是庄周。突然醒来惊惶不定,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物化”。
这个梦阐释出了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即所谓“有分”,但这个分别又是值得思考的,即何者才是真实的状态。梦境和觉醒或许只是不同的梦罢了,或者说梦和醒的这种分别只是一个更大的梦中的不同状态而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处境呢,庄子提出了“物化”。关于“分”与“物化”古今学者有不少的注解与论述。
西晋玄学家郭象认为,自然万物的原初本性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存在,万物之“性”是事物自然而然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万物存在之根本。这就是“性分”。他的“性分”论是在《庄子注》中提出来的。按汤一介先生的解释,“性分”概念大致有两层涵义:一是对事物本质的明现,二是对“物物自分,事事自别”的事物间差别状态的肯定。
“逍遥游”所指的境界就是万物能无为自得,无为自得就是明白自己的“性分”所在,因自得而无为。“自得”就是要明白万物都有自己原初的本性,只要能够按照自身的本性发展,对于万物本身而言就是达到最极致的体现。就这点来说,其实没有做任何在自己原初本性之外的事情,所以是无为。
而比较复杂的则是“物化”。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
“庄周梦为蝴蝶而自己觉得很快意的关键,实际是在‘不知周也’一语之上。若庄周梦为蝴蝶而仍然知道自己本来是庄后,则必生计较计议之心,便很难‘自喻适志’。因为‘不知周’,所以当下的蝴蝶,即是他的一切,别无可资计较计议的前境后境,自亦无所用其计较计议之心,这便会使他‘自喻适志与’。这是佛家的真境现前,前后际断的意境。”
在徐复观看来,庄周梦蝶在他梦见蝴蝶而不知自己是庄周的时候,感到最快乐,反之,梦里梦见依然是自己,并不是最快乐时。所以说,人在做梦的时候,才不会有计较计议之心,计较计议是大多数烦恼的来源。他还说:“惟有物化后的孤立的知觉,把自己与对象,都从时间与空间中切断了,自己与对象,自然会冥合而成为主客合一。
”这里的“物化”指的就是人与别的事物的分别的消除,忘记了自身,这个时候人的主观和客观就会冥合在一起,超过主客内外,合二为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物化”与“有分”连在一起的前提是,首先要认识到庄子梦蝶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一样并不是绝对的,应该有超越性。《知北游》篇中说:“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这个“化”就是化与不化的结合,而不是所有的“化”,不是像庄子所说的都化成梦,说蝶化,蝴蝶还是蝴蝶,庄子还是庄子,不要被蝴蝶的特性和庄子的特性束缚,这个才是“化”的涵义。
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在其《庄子今注今译》中将“物化”解释为:“意指物我界限消除,万物融化为一。”又在《老庄通论》中阐述道:“《齐物论》的最后,以蝶化象征主体与客体的会通交感,达到相互泯合的境界。这境界实为最高艺术精神之投射。”在《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和《十家论庄》中对庄周梦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庄周的蝶化,比喻着人性的天真烂漫,也象征着人在没有陈规制约和戒律重压时的适意自由。在庄子看来,宇宙就像一个大花园,蝴蝶可以无拘无束,欢欣于这个大花园的花丛中间;人生也应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宇宙自然之中逍遥漫游。”
这种解释跟庄子追求自由的主张是相一致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郑开教授对“物化”的理解很深刻,他在《试论〈庄子〉的“化”》中说道:
“‘庄周梦蝶’的核心在于‘物化’,那么怎么理解‘物化’概念呢?钟泰提示的两点十分重要:第一,他引述了《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解释《齐物论》的‘物化’,这显示了正确的阐释方向;第二,‘物化’是《齐物论》起首命题‘吾丧我’的转深,也就是说,‘丧我’‘无我’是理解‘物化’概念的重要基础。《达生篇》所说的‘指与物化’相当于‘梦化为蝶’。”
还指出了《庄子》“物化”概念与理论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庄子》所说的‘物化’思想显然力图克服心、手、物之间对立、隔阂与疏离。总之,‘物化’既非‘化’亦不是‘不化’,它意味着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西方美学中的‘契合’概念更深邃而且更有力。”
将“物化”与“吾丧我”的结合体现了对庄子思想的整体把握,人对于外在世界的反应,如果是随物转移,那么也就是无所谓“分”,如何在确立分别的前提下,克服内心的执持,则是既保持自我的独立,又不被自我所束缚的化与不化的结合。
读完这两个梦,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刚健和宽容、道家的智慧和轻灵,既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但又可以统一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中国传统的智慧真是在这样的富有层次性的思考中,为我们提供多样性的人生坐标。儒家强调责任感,强调积极进取,而道家追求内在的超越性。但这样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在魏晋玄学家的态度中,儒道之间可以互补和融合,即一个身居庙堂的人可以心系山林。
在我看来,离世而独立固然会给人一种欣喜,然而面对浑浊的世界,我们当然不可能一走了之,对此,儒家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阔气象。而从庄周梦蝶的寓言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智慧的激荡,也能领悟到人生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我们要处之泰然,超然物外,却也不能失去内心的支撑和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