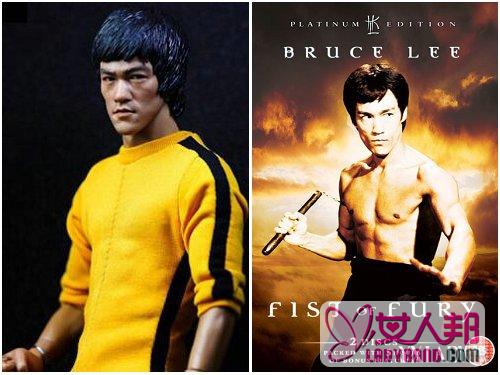【一念无明免费】《一念无明》电影观后感
导语:年度口碑佳作《一念无明》一举斩获新晋导演(黄进)、最佳女配角(金燕玲)和最佳男配角(曾志伟)三座重磅奖杯,成绩斐然。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电影《一念无明》的观后感,欢迎大家爱爱阅读参考!
这个社会对待病人真如我们想象般宽容吗?摔折腿,拄着拐杖,路人退避三舍,怕再把你绊出什么事故。突发感冒未准备口罩,地铁上咳嗽两声,身边人默默转过脸,在Whatsapp里噼里啪啦打着字:「隔篱有人感冒都唔戴口罩」。身体虚弱头晕眼花不足与外人道,旁人看你并无大碍也不在意,个中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这样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疾病,就更让人惊惧,对其表现出的嫌恶程度,也就更肆无忌惮。影片的开头,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大海去精神病院接「病愈出院」的躁郁症儿子阿东(余文乐饰演)出院,而早前,妻子在被儿子照料的过程中突发意外身亡。虽医生称此事与儿子病症无关,但父亲的担忧写在脸上。他挤出笑容,故作轻松地与没什么表情、说话气若游丝的儿子打招呼,眼神里却全是防备。
父子许久没见,在那之前,父亲和在美国的小儿子都不知所踪,而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拥有稳定女友的长子阿东辞掉工作,独自陪伴病重且情绪不稳定的母亲(金燕玲饰演)。母亲用咒骂发泄怨恨,阿东在拼命隐忍和爆发中挣扎,终于把自己逼成了躁郁病人。于是他入院、治疗、出院、被父亲接回到逼仄杂乱的板间房,试图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再次获得这个社会的接纳。
病态的人:「那个人样子好怪……他好像一条狗哎。」
如果你将自己代入阿东的视角,会发现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如同电影英文片名一样,是一个「mad world」:
好友的婚礼上,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没人在意主角在说什么,阿东忍无可忍下的「仗义执言」,似乎更令好友尴尬;用人单位听到「躁郁症」后避之不及的状态,并不因他的坦诚和专业能力而改变;笑嘻嘻总是拜托自己和父亲的邻居,在他发病后,第一个落井下石;而狭小逼仄的空间,父亲枕头下发现的自卫用具,前女友宽容背后的强烈恨意,甚至令他找不到一个抒发情绪的角落……于是他冲去超市,大口大口吃着可以「改善情绪」的黑巧克力,换来的却是路人的指指点点……
于是他强拉起来的,脑袋里的那根弦,再次「啪」一声断掉,让他从兴奋且动力十足的「躁」期,滑去犹如万丈深渊般的「郁」期。
有关阿东的片段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茫然的他突然疾走乃至大步奔跑在深夜的街道,电影画面平行向后移动的样子。阿东像一个被抽离掉的人,在对他而言意义不明的世界里移动,空洞不知所踪。他看人的眼神,总夹杂悲伤与怀疑,令人不由担心,他下一秒会否作出什么极端行为?而比起那些选择主动去拒绝和伤害,没心没肺的看客,他的隐忍和善良,却又显得格外可贵。
好在总有温情场景弥补:下一秒,他和父亲说起年幼时去城门水塘的约定,二人无伤大雅地争执了几句,暂时和解,相互依靠着,走回他们的家。
病态的家庭:「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家当然不是万能的。而阿东的病因,显而易见来自他的母亲。苦等丈夫与小儿子却无限失望的母亲,没有其余的宣泄出口,只能把所有情感垃圾都倾倒在阿东身上。她是阿东世界里的第一个「疯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需求无度,不懂感恩。她何尝不可怜,然而她也亲手毁掉了为他竭尽全力的阿东的人生。
在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片《伴生》中,其中一位为照顾年迈父母、中年仍未出嫁的女士,对着镜头流泪:「我好想有时间,可以安静看一套戏、读一本书,做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做不到!」为人子女,都想做到孝顺,然孝顺的界限在何处,孝顺分内事,究竟该亲力亲为,还是乐得交予他人,自己轻松?
影片中,束手无策的大海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大儿子,儿子一句话说得轻巧:「你把阿东送回精神病院,自己选间条件不错的老人院,钱不是问题」。绝望的大海,淡淡问出了这样一句:「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曾经他是逃避者:他努力工作,想给妻子更好的生活;他百般辛苦,却害怕妻子的失望和不满;他逃避家庭,酿成苦果,决定承担,却发现难度远超他想象。他和阿东在对峙中说出心声,而曾志伟在这一段落泪剖白的影帝级表现,实在无法不令人动容。
承担是给自己的枷锁,逃避是无视责任、把痛苦留给亲人……二者之间,有没有万全之策?如何在调适好自己心情的同时,也对家人多一份理解和包容?道理说来总是简单,做起来,却步步艰辛。
活在这个疯狂世界:「我没事了」
尚未被疯狂世界改变的邻家纯真小男孩,成了阿东的解药。在所有人都觉得他「荒谬」、「不正常」时,只有小男孩和他正常交流,与他相伴,听他讲话。他坐在天台上,对着急赶来的父亲说,「我没事了」。
他当然不是「没事」。他生活的世界依然逼仄、杂乱、充斥着形形色色自私而缺乏同情心的人类,他依然善良而软弱、恐惧而坚持,他的父亲依然无从理解他的内心,还要背着巨大的包袱寻求解决之道。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活下去便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影片一个颇为温馨的「Happy Ending」。
导演黄进说,这是一个很想带给香港人的故事:想呈现出如何直面问题、觉醒并寻求改变的状态。事实上,在压力巨大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中的「阿东」——不久前,香港心理卫生会的一项调查还显示,香港人的抑郁指数创新高,有百分之五点五受访市民估计患有抑郁症,需要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另有百分之九点一的受访者属「应关注」的组群。
「阿东」非但不是边缘人,甚至还可能早已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而未被发现。
编剧则强调「伤害往往来自不了解,无知造成日常的邪恶」。她认为「电影最强大之处,就是让观众感受角色的情感,学懂同理心,从而令世界更美丽」。
这个故事整体来说,压抑又「不开心」,但曾志伟、余文乐、金燕玲一众大牌演员却毫不犹豫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出演,更称之为「十年一遇的好剧本」(曾志伟语)。在快速发展、冷酷麻木的社会运转成一部失控机器的同时,能有这样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专业水平也绝不逊色的新导演作品出炉,实为观众的幸运。
電影院燈光亮起,散場期間,聽到周邊觀眾不時飲泣,大概都被故事中的情形感動了,但我仍然無動於衷,甚至是煩躁,故事是理所當然地殘酷,一眾邊緣人在社會夾縫中無處容身,更沒有出路。這絕非是一部讓人愉快的電影,看不到劇中人有任何希望,也得到不到任何救贖的機會,每一張面孔上由如荀子所說的「性本惡」得到實証,要麼,這是創作者對世界懷抱深深恨意,想透過電影作為媒介將一切不滿發洩;或是,還未如願能走入角色的內心感受,只固執糾纏於真實狀況而無法自拔。
而我傾向相信是後者。
《一念無明》如同黃進和陳楚珩這對編導過往的短片作品,將角色放置一個極端的環境之間,《三月六日》裡的三個社運年輕人被捕後在警局與警察對抗,而短片集《Good Take》裡的同名短片,甘草演員難忍太太離世,正當想自行了斷時,發現鄰居正被賊人入屋行劫。
同樣,《一念無明》裡也有很多衝突,跟隨著男主角阿東(余文樂飾)的經歷,父親,前女友,而至周邊鄰居,朋友,我們看到阿東在各種人際關係的失落扭結,這種衝突在家庭關係中特別明顯,父親長期缺席,弟弟早已離棄老家,只有阿東面對病患的母親,最終悲劇發生,如期說這是一部關於精神病患者的電影,更似乎是關於一個原生家庭最終解體的過程。
但看似壓抑和克制的態度,其實隱藏不了電影中極度煽情浮躁一面,作為他們首部長片作品而言,所涉獵的內容之廣,反映出創作者野心不少,除了家庭,加上教會,友鄰,以至醫療制度,在不足一百分鐘的長度下,阿東身邊的每一段關係也只不過換來更強烈衝突,就以前女友與教會一段為例,整個段落,由前女友在阿東面前出現的神態,到向眾人告解自己的不幸,在講台上數落出前男友各種不是,情緒逐步升級,創作者意圖想表達的是對教徒麻木的不滿?前女友的軟弱?還是只不過單統借一個平台對他人復仇?戲中每一個人物的動機也是一瞬間地爆發,對於一部相當著意描述低下層,社會邊緣人士狀段況的電影,當這些人早已被社會附加上向種標籤和定形時,他們對阿東所作出的行為,也只不過成為加強阿東作為受害者的遭遇。
除了片面的情緒,我們究竟了解到當中多少難處和真相?而事實上,電影中對阿東的躁鬱症描繪也相當粗淺,從有限的篇幅所理解,他的病患也並非嚴重到與他人交惡,但編導二人為了保持著戲劇張力,放大了很多不必要的成見,社會固然有很多不公,但矛盾的形成,是不是就如我們眼前所見那樣?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角力,對於一部走寫實路線而言的電影,放棄了真正深入探索的可能性,究竟有沒有如宣傳所上所說那樣,有過對真實個案更深入的了解,對此有所懷疑。
又或者,《一念無明》在有意無意間也展示了現今香港一個真實狀況,這個一點也不和諧的城市,每一張面孔也會讓人憎厭,不安,排他性重,連一刻休息的時間也沒有,這不單是躁鬱症病者所面臨,而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城市的人,要麼每一個人只能圍爐取暖,要麼是排除他者來確保自身安全,但只為了形造戲劇張力,而視而不見現實生活中看不見,隱藏背後的魔抓,這不正是現今我們面對社會問題時,往往出現的真正問題,令事情走向無法收補的局面?
我並非要全盤抹煞黃進和陳楚珩的用心,特別在現時香港電影生態下,交出一部獨立製作電影,確實難得,而他們唯獨欠缺了的會否是,對主角,包括他以外的其他人,保持著相同的「同理心」?也變相令觀看《一念無明》的觀眾繼續用有色眼鏡去看精神病人,甚至是周邊同樣需要被關懷的人物? 但最令我不安的,是創作者無意識地跌入了一般精神病的論述,香港作家李智良所言,當我們言說精神病是,會將問題與社會割離,認為這是個人可能是成長,可能是先天因由而起,「當我們說一個人有精神病,其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正面對一個很複雜的處境,首先要食很多藥,然後那個人所有的感覺、所有的經驗都會被人翻譯做同那個病有關,無論做什麼都會被人認為是因為精神病。
」(引至明報2月19日 「不要將精神病問題割離社會——訪李智良」) 這種標籤在戲中根深柢固,更不要說戲中的性別定型問題,戲中所有女性都是壞人,也感該說。
香港電影近年也出現了多部被觀眾稱為「良心之作」,但《一念無明》的缺失,也正正說明了在製作社會議題的電影,需要對該問題有何等深入研究。在此,借用影評人譚以諾對堅盧治新作《我,不低頭》所作的評價,這應該是我們面對任何一部標榜寫實和良心電影時,應有的準備。「對社會制度需要何等的了解,而並非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對社會上的人需要何等的愛和耐心,對世界又需要何等的希望和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