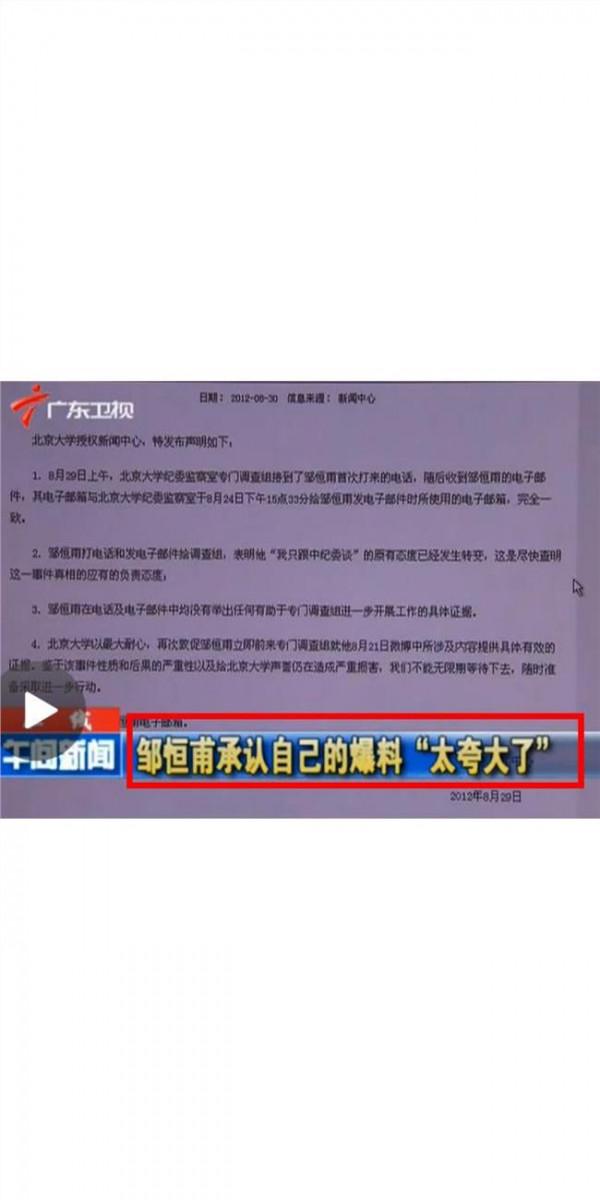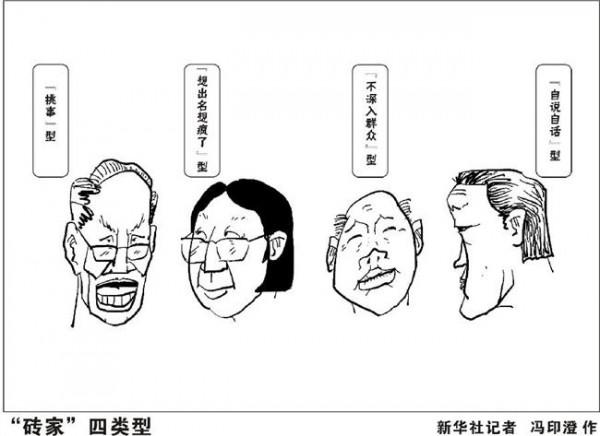我眼中的邹恒甫 张狂邹恒甫
如果说邹恒甫有过错,或许就是因为他作为经济学家,将自己的实验场过分地理想化,就像一个生物学家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做实验。但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中国社会更加的人情化。这对于邹恒甫来说,是个挫折,但也为净化复杂的实验场给予了一个改变的推动力。

★采写/《小康》记者 蒋卫武
在与张维迎起争执之前,邹恒甫的社会知名度并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低调的一个,媒体大多吃过他的闭门羹。但也在彼时,他在学术界已声名鹊起,经济学圈子里,虽然他年纪不过46岁,但已经有“谈笑间,点评江山”的意味,这些得益于他早年留学哈佛,成为新中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由此可以对国内许多知名经济学者直呼“学弟”。

或许因为他以15岁的弱冠之年进入武汉大学,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20岁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求学,奔波于各个学院仰拜世界一流的名师;因此他不屑于社会的人情世故。在人们眼里,这是个 “为人张狂”的书呆子。

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热衷于从数理推导来消解强权的基础;他性格张扬,嘻笑怒骂,爱用“好玩”来下结论。但他并不总是全身带刺,对于老百姓,他自称是“中国穷苦百姓的走狗”,对于母校武汉大学,他说自己是“癞皮狗”。

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在经济会议上,邹恒甫的标签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媒体在报道他时,总会强调: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我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包括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对于他传奇的学术身份,邹恒甫说得非常淡然。他也直言自己并不是从小就成绩骄人:“我的中学不是华容一中,而是五中,一个阶段的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自尊心才是做事业最重要的动力”。
尽管他对自己的求学过程讲得平淡,但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却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是教育部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刘道玉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30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武汉大学是教育部选定的学校之一。
当时包括好几所大学都向他发出了录取书。但因为留学概念新起,邹并未来得及考GRE、TOEFL,威斯康星大学录取他时只是作为硕士留学生,但美国哈佛、斯坦福大学却因为邹恒甫的优异表现而破格愿意其读取博士。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一再打电话请求刘道玉先生去教育部通融。“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吴纪先说“不能埋没人才”,其时甚至以“辞去系主任”作“要挟”。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并于1947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吴先生深知高起点对于一个人才的重要性。
刘道玉由此几经周折,辗转通过熟人,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来为邹恒甫的留学据理力争,使得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得以“成行”。
“他人很聪明,同时又很用功,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去听文、史、哲的课。涉猎广泛”,刘道玉先生回忆邹恒甫在武大上课时的情景说。
在哈佛大学,邹恒甫没有辜负吴老师和刘道玉校长,他继续武大时游学的习惯,在各个学院间选课修习,并且能够顺利攻克语言关。
至目前为止,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6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大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为第三位”。
而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推动力,林毅夫对邹恒甫的评价是:“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研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作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林毅夫应该充分懂得自己措词的份量,对于邹恒甫的褒贬他在用自己的学术信誉作担保,但对邹恒甫的夸赞,他很大方:“邹教授是个具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的教育实干家。
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
目前邹教授所引领的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专业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本科项目。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如果说命运曾经垂青这个长得虎头虎脑,顶着一头卷发的年轻人,那他没有辜负命运对他的垂青;如果他的老师、学校对他充满期待,邹恒甫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中国的IAS”
采访邹恒甫地点是在他中非基金的办公室。“200多平米,三面玻璃,对于北京的景色,你可以随意俯瞰”,当时他心情很好,因为刚刚从深圳高等研究院开会回来,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askin先生。
“我就是想在中国创办一个IAS,”他并不像饱读诗经的人惯有的成稳,相反,孩童的天性在他46岁的时候还保留得太多,让人觉得他太理想化,有时又挺顽劣。
IAS,即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于1930年成立,创建宗旨是为各领域科学家做提供进行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IAS的名人如爱因斯坦、哥德尔(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其不完全性定理不仅改变了数学,而且改变了整个科学世界和建筑于此定理之上的哲学) 、冯·诺依曼(数学家,现代电子计算机创始人之一)等。
“自己写100篇文章,不如让100个学生各写1篇文章”,邹恒甫说做教育是自己最激情的事情,“会让我睡不着觉”。
1988年,邹恒甫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就职于世界银行,1990年,他归国省亲回到武汉大学。“当时看到同学还是用二十年前的经济学教材,他就认为这个状况一定要改”,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回忆当年邹恒甫一箱一箱地从美国带回经济学经典教材,并且希望同学能够学习英文原版。“要充分相信年轻人的适应力”,他说自己当年在哈佛就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能赶上进程。
1994年,邹恒甫创办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取名“IAS”,希望以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来激励同学,同时又在此前冠以“幼小的”IAS,来标识差距。
“当年我是一张纸,一张桌子把武大的IAS创办起来的”。而他的朋友有时会戏谑“抓去做了壮丁,剥削了劳力”。
对于这类声讨,邹恒甫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全单应承下来。“那是没错,当年我就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来给我上课,而且是免费的,就连差旅费都是他们自掏腰包”,邹恒甫称唯一给过陈志武500元,因为考虑到当年陈志武先生过来上课时是带着家眷。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于1999年将研究教学领域拓展到哲学、历史、国学等科目。其学术委员会由包括Jean-JacquesLaffont,RobertBarro,EricMaskin等近30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组成;拥有国内外知名教授及讲座教授近40人。
“当时我请前美联储主席来武大讲课,武汉市政府都觉得很哄动,以为请来这么牛的人来武汉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邹恒甫却认为学术不分贵贱:“他们给中国学子上课还能看武汉的樱花,去珞珈山跑步,都非常高兴呢”。
1998年,邹恒甫应邀任教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也就在这时,这个湖南人放言:“中国国内经济学期刊没有一个SSCI(THOMSONISI),就让我们自己制造一个SSCI吧!”
湖南人以性格刚烈为名,敢作敢为,但当时这番豪言还是震得中国学术界发愣,认为这是一个狂人的狂语。
或许当时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但邹恒甫却为此举办了自己平生第一个新闻发布会。邹恒甫说过他的“自尊心”是推动自己的原动力,或许他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公布来让大家以及自己明白这不是一个“大玩笑”。
“只有国际性的刊物才能制造出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样才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走向国际,这条路即使再艰难,也必须走下去。”邹恒甫有豪赌的勇气与胆量。
这一次,还是他的朋友们帮了他。邹恒甫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总能得到朋友的鼎力相助。当然,他的朋友、知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曾说“恒甫很热心,他对朋友非常铁”;同时,或许因为他的事情总是关乎于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与良知,所以能够激起朋友的热情回应。
为了将《经济与金融年刊(中文版)》(下称《年刊》)办成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杂志,邹恒甫游说自己在哈佛时的同学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多次投稿,另外还有巴罗、素洛、马斯金等顶尖经济学家,这使得《年刊》很快赢得国际地位。2008年5月6日,《年刊》正式被SSCI收录。所有文章将从2007年(第八卷)第1期开始收录。
“只要你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努力去做,没有不成功的”,邹恒甫称。
“只有爱与恨,没有中间路线”
“有记者1994年说要写我,但10多年过去了,还不能成稿,写我不容易,”邹恒甫得意地大笑,他喜欢自己成为一个难题,看人皱眉苦思。但他又是大方磊落的:“你如果要了解我,可以在我的办公室设个位置,每天带你的手提电脑来上班就好了。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要为人讲述一个准确的邹恒甫,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从小喜欢随身将书装在口袋,没事就翻看;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里充满矛盾。喜欢时,他会像个孩子,与你不设防地推心置腹;但对于意见相左者,他却变得好斗,像古战场的士兵非要争得一个有你无我的结果。
他喜欢高贵,特别欣赏中世纪宫廷贵族的气息,他也不乏平和,甚至希望以后有机会做农场主。当然,其中有一点非常确定,他鲜明,会明白地告诉你自己的喜好。这种坦承在时下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优点,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的是会意。
邹恒甫会顽皮地将国内一批知名的经济学家说成是 “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并且会在一些大学的演讲会上直接对他们的学术“命门”指指点点。
“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说到自己的恶作剧,邹恒甫不以为然,还高兴摊开双手举出另一个例子来。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个性要么是让人爱,要么是招人恨,没有中间路线。
说到什么人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讲了一个自己在哈佛时所经历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SergeLang,也就是在电影《美丽的心灵》里被纳什打倒在地的那个书呆子。这是一个极端仇视支持越南战争的人。为了不让越战支持者亨廷顿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SergeLang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在课堂内外,他整理了一千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并且把他的一千多页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
“我有幸得到两本,因为我选了他两门数学课”。
课堂里,SergeLang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课后,他就在MIT,波士顿大学到处讲座批判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这样一来,美国的新闻报道也跟踪而至,闹得哈佛不得安宁,而所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都知道了亨廷顿的逻辑错误。于是,亨廷顿至今未当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邹恒甫在讲这个故事时,双手翻腾,兴奋得额头冒出毛毛汗,他如此用情地讲SergeLang的故事,或许也是在说一个中国版的自己。
因为他的才华,他荣誉加身,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数理经济学联合班长、清华-BERKELEY心理经济学组长、北京大学经济学一级教授、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还有人称2004年为他的丰收年,他被评为“十大最具影响力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但因为鲜明的个性,他也遭遇不平事。与张维迎的争执,使得外界认为是“从兄弟到反目”而扼腕。但在这场争执里,不但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震动,同时,“中国高校官僚化治理”也成为媒体的一个热点话题。
说到与人的纷争,邹恒甫还是那副“我心昭然”,任人评说的姿态。但据他身边的人说:偶尔在酒醉后,邹恒甫会一改嘻笑怒骂的神情,变得凝重,高声呼出一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