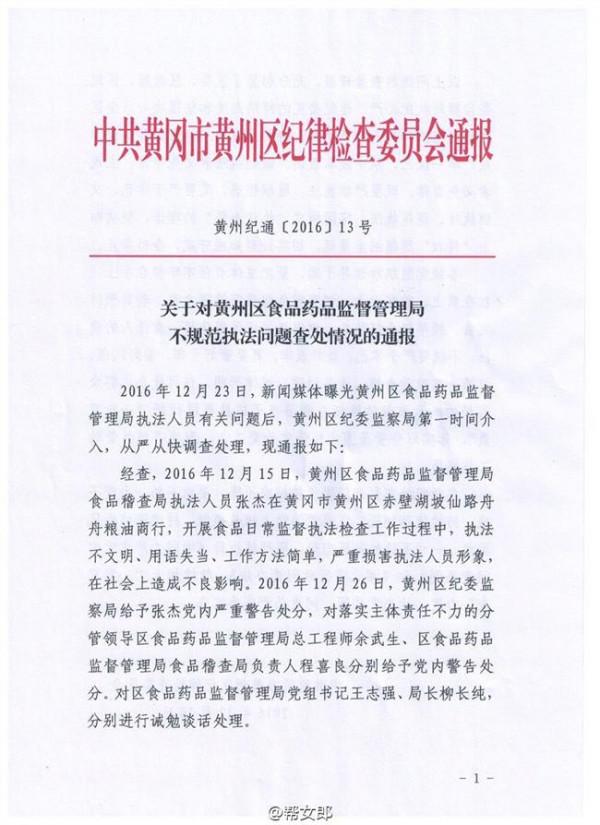【张承志黑骏马赏析】【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张承志|如画的理想
大概从六岁上幼儿园时起,我就喜欢涂抹勾画。一年后上了盔甲厂第一小学(即汇文小学),大概是因为有了课桌吧,画画的爱好,立即就成了痴迷。记得我把课本每一页的边角空白都密密画满,被老师罚用橡皮擦干净。大约在二年级那年的新年,我给班上的同桌和好友都画了一张贺年片。

盔甲厂一小的同学们那时有一项享受:课间操后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须知孙敬修和收音机播出的他那劝善如流的娓娓故事,是北京五十年代的一个象征——孙老师远远在台上讲,我们全校千余名学生,就那么一班班原地站在大操场上,一片寂静,听得如醉如痴。
应该是我上三年级(1957)那年,孙敬修老师当了我们班的图画老师。不用说,我在孙老师的课堂上如鱼得水,成绩一色五分。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孙老师说画自由画,但也可以临摹他拿来的一张。后来才知道全班都画临摹,唯有我一个独自陶醉,在心在意画了一幅《黄继光堵抢眼》。万没想到,从来慈爱绵软的孙老师突然不高兴了,带着气给了我三分!
我震惊无比。图画课的三分,于我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刻回想琢磨,或者当时我没听见孙老师改了主意让大家都画临摹?抑或是那天孙老师有心事、而我却表现得狂妄招嫌?
可能是后者。三年级的我在图画课上得意忘形,几乎是无疑的。
一定是那时我尾巴翘翘的样子,让和善柔顺的孙老师反感了……只可惜这反省,晚了半个世纪!
那个三年级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厄运之年。唯能忆起的一件事,是和班上一个混血儿打了架;而班主任,我以为她决心要把我逼入死地,盘算给我学生手册的“操行评语”写“差”。因为她执犟地逼供,要我承认“屡教不改”。而这四个字,乃是将“勒令退学”的“差”级评语的原文。
我心里唯有一个念头:要是承认了“屡教不改”,母亲会出什么事?那一天母亲劳累的影子充斥了脑海,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回答这一句。天渐渐昏暗了,学校里已空无一人。班主任还在坚持问:“你说,你这算不算屡教不改?”
就在那绝望的时刻,突然孙敬修老师从一旁路过!
孙老师认出了我:哟,这不是……他怎么啦?班主任轻描淡写:他犯错误了。
孙老师喃喃说:“是么。张承志在图画课,可是好学生呀。”
早想了事回家的班主任借坡下驴,死刑突然缓期了:哼!看在孙老师的面上,今天就算了。以后再犯……
今天我写着依然感动无比。
多少年了,我牢记着他这几句话的原因,尚不是为了追述我与孙敬修先生之间短暂的私淑之交,而是因为他的救援结束了“屡教不改”的纠缠,让操劳的母亲遭受连坐的恐怖,被化解了!
十大建筑的兴建,终结了我们贫寒丰富的胡同生活。搬家以后我发觉,朝阳区的艺术气氛远较城区高得多。合唱团,诗朗诵,很快我被选入朝阳区少年之家美术组,在一位姓董的辅导员门下,进入了准专业的美术训练。
董辅导员是位出色的画家和教育家。他用油画和彩墨画了两幅京剧肖像(扮演苏三的女演员就是他的女朋友)。油画浓烈透明、彩墨挥洒自如,如在我痴痴凝视的眼前,展示着美术境界的可望不可及。
他对我们的素描训练完全是科班水准。美术组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初中那伙大哥大姐已然是艺术家派头,他们画那种卷发的石膏头像,忙着考入美院附中之前最后的临阵磨枪。而我们小学组则永远对着石膏六棱体或三角锥,每周日画一个上午。董辅导员要求我们自己把自己积累的素描时间写在画纸上,他强调:你能找出的“面”愈多,你就能画更长的时间。
已是三年饥荒的边缘,美术组除了白纸、水彩、铅笔之外,不能提供任何画具。油彩像梦一样遥远,辅导员的方针是坚定地画素描。一次,他把吃剩的半个窝头替换了石膏。我们一边画得眼花,一边懂了为什么打基础:窝头真难画啊。
创作画的机会很少。但董辅导员不是孙老师,他让我们“爱画什么画什么”。这回我在心在意画的是一幅《收麦子》,一辆大车上坐了几个红领巾,一位老大爷扬鞭吆车,梦想中心爱的马,占了一半画面。辅导员把我的这幅创作装进镜框,挂在美术组的墙上。这一回我可没敢得意:满墙的画里数我这一幅最差。何况我已懂得,展示的作品未必优秀,有时是为了比较讨论,才挂到墙上的。
一天,看见董辅导员端详它,我们也围过去。辅导员转过脸问我:“你是不是见过赶车的坐在右边?”
我茫然。他却高兴地说:我一直觉得有些怪,今天终于发现,老大爷坐在车辕右边!一般赶车人是坐在左边的……
我也猛然看清了。就在那一天,一种关于生活真实与画面平衡的思路,植入了我的心里。
每个星期天,从三里屯步行走到下三条,喊上一个美术组的伙伴,出神路街,进入坛口,走过静谧的日坛,推开红墙小院的木门,削尖几支中华牌的铅笔——唉,日坛公园里的少年之家!难忘的美术组的每一个小时!
这是一个文人骚客如蝇似蚁一拥而上、狎书玩画的时代,这是一个假画臭字如垃圾堆塑料袋一样、污染中国的时代。
为了区别,在出版这本收集了数十年速写、草图、画作的心爱小书时,我想强调,我不冒充画家。这本小书收入的并非“文人画”,也不敢做美术的炫技。正相反,眺望着自己迟疑的线条和失准的色彩,堵噎我心里的,唯有达不到绘画境界的遗恨。
我再次掂量了自己——终此一生我只能是一介作家了,虽然我也很喜爱其他语言,包括色彩的表达。
和此书的姊妹作、摄影集《大陆与情感》一样,此书宗旨并无改变。描写我的三块大陆,蒙古草原、黄土高原、天山南北——阐释大陆上各异的文明,为生息于斯的民众辩护,记录他们与我的关系。
只不过这一本的手段,是草图、速写以及绘画。两脚踩上的土地,也更扩展到了欧洲、日本、地中海的西半、加勒比与中南美——都是这个地球的关键地域。
如上追述,甚至与许多吃着美术饭的职业画家都不同——画家不仅是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理想,而且我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学画史。所以,在自警和不吹嘘的同时,我也不掩饰自己的另一种语言憧憬,不掩饰此生要画成几幅油画的野望。
不知我能否说——
这不是什么才能的炫耀,而只是一种学习的记录。是的,也许已经到了总结的时候:从孩提的往昔,到人生的迟暮,就是这如画的理想,以及不歇的学习,使我愈来愈扎实地靠紧了——他者与世界,并逐渐完成了一个作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