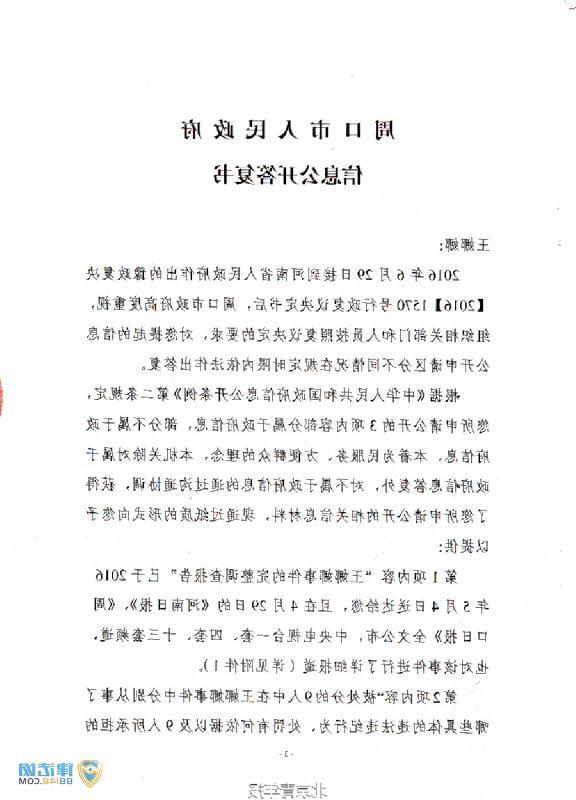“余秋雨事件”始末(滕俊时 王非记官方查清余秋雨不是石一歌成员)
1999 年 12 月,正当余秋雨历险考察从中东到南亚的古文明而引起全球华人密切关注的时候,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在北京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声称据一个“当年同事”的揭发,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写过几十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多数媒体作了报道。
2000 年 1 月,余秋雨随考察队从尼泊尔回国,途经四川,得知此事,似乎完全没有重视,只是托一个记者交了一封信给正在四川结婚的余杰。后来那个记者公布了那封信,看得出来,余秋雨在信中以很轻松的口气判断余杰是不小心误信了捕风捉影的谣传,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文革后才出生的余杰,自己在文革中遭受大难,只在林彪事件后大学全面复课时参加过教材编写,所谓“石一歌”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的一个笔名,自己曾写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胡适传》的一个开头,用的全是自己的真名,从未发现有任何与文革有关的“政治问题”。
余杰一定没有估计到余秋雨会亲自给他写一封这么充满善意的信,他接信后又在魏明伦家见了余秋雨,并很快发表对余秋雨的道歉文章,承认自己在谈论文革时也用了文革的思维方式,他还表示钦佩余秋雨的宽容大度。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一场误会已经解除。没有想到的是,大批判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先是古远清在《文艺报》上揭发余秋雨写过一篇《评斯坦体系》,后来又说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造成了致命打击。更重要的是,余杰所说的那个自称“当年同事”的孙光萱也亲自在《文学报》和《南方周末》上现身了,他不说余秋雨以前的问题,只说余秋雨现在的“态度”,但给广大读者的感觉是,“证人”出场了。与此同时,肖夏林揭发余秋雨为深圳做顾问、说好话,收受一套豪华别墅;朱大可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是“文化口红”;余开伟批判余秋雨把盗版集团说成是“文化杀手”,又揭发余秋雨在中学里就写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 由《南方周末》、《文学自由谈》、《文学报》领头,全国六十多家报刊发表批余文章多达一千余篇。据统计,发表批余文章最多的个人是湖北的古远清。他原是余秋雨的热烈吹捧者,遭余秋雨拒绝后结交孙光萱,成为批余第一人。第二名是湖南的余开伟。
在这种情况下,余杰也一改他的道歉态度,声称要“战斗到底”了。从此他批判余秋雨时不再引用含糊的所谓“当年同事”的揭发,而是只举孙光萱一个人了。
从相关的日程和资料来看,在这整个过程中,余秋雨似乎一直忙着在海内外演讲,以一个亲历考察学者的身份,报告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域的所在。他还以二战被侵略国的代表,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祭”上发表演讲。因此,对于记者问起在国内遭受围攻的情况,一直回答“是无聊小事,不必在意”。直到孙光萱的一再出场,他才警觉起来。
余秋雨曾告诉前来采访的传媒评论家徐林正,这个孙光萱是“贺敬之研究者”,早在“两个凡是”时期曾经“清查”过余秋雨议论文革和领袖的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这个颠倒黑白的“清查”才被迫停止。经过复查,真相大白,余秋雨才被破格提拔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来余秋雨又担任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负责人,曾评审过孙光萱企图以一本研究贺敬之的小册子谋取一所高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的申请,他以孙光萱为例提出了“一切没有大学文凭的人都不能在上海高校申请高级职称”的主张。这使孙光萱产生双重心理怨恨,一直等到一九八九年之后他的研究对象执掌全国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而余秋雨彻底辞职后已并证明没有再走仕途的可能,才大规模地在媒体间“算帐”。余秋雨的这个谈话,曾在《美文》杂志发表。
余秋雨判断,那个写批判文章最多的古远清所散布的一批批“材料”,一定是孙 光萱提供的。余秋雨觉得只有通过诉讼,才能在法院的追查下弄清真相,于是便以诽谤和侵害名誉权的理由把古远清告上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并要古远清赔偿16 万元人民币。古远清被告诽谤的主项即余秋雨是《评斯坦尼体系》一文的主要执笔者,该文给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造成“致命打击”云云,法院刚开始审理就知道完全是不实之词,因为该文的作者胡锡涛三次声明此文完全由自己所写,与余秋雨一字无涉,而且他在写作此文时,余秋雨在外地农场劳动;胡锡涛又以时间证明,在他写作此文之前,孙维世早就去世,因此不可能对一个死者造成什么“致命打击”。法院正考虑把余秋雨提出的16 万元赔偿费降为 10 万,作出判决,但余秋雨发现事实真相已清,孙光萱为古远清提供伪证的证据也已经获得,又考虑到古远清在报上诉说自己清贫,付不出赔偿款,就主动向法院提出,只要被告古远清在法庭上签署道歉文书,可以放弃赔偿款项。2003 年 3 月 18 日,被告古远清向原告余秋雨道歉的法律文书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道歉文书的法院文号为:(民)初字第 388 号。
被告古远清离开法院后立即在湖南卫视及湖北的报纸上,用胜利者的口气叙述被起诉的过程,后来又写了一本“庭外审判余秋雨“的书出版。余秋雨不再作任何回应,只是不指名地在《借我一生》中写了一句:“应该相信他还有作为一个人的最后羞耻感”。
与此同时,余秋雨还在北京起诉了公布“收受深圳豪华别墅”谣言的肖夏林,也是为了弄清谣言的来源。北京的法院完全出人意料地驳回了余秋雨的起诉,理由是,这个传言虽然不实,却不会损害余秋雨早已建立的形象,而且,赠送和收受豪华别墅,不一定是坏事。这个判决,受到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教授和其他诸多法学家的质疑。但是余秋雨似乎并不在意,因为通过审理他也清楚了造谣者是深圳的无业游民朱建国。
余杰在这整个过程中,心态发生了多次转折。他一开始 害怕余秋雨起诉他的造谣,因此先在一份小报上发表道歉文章;后来又怕自己点燃的批余风潮被别人抢了头功,便放弃道歉,继续批余,但闭口不说事实,只是上纲上线;再后来他发表在目前中国的传媒环境和法制环境下,诽谤、诬陷不仅很安全,而且还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于是胆子更大了。
从 2002 年开始,余杰开始以“批判过重要人物”的履历,向美国政府申请人权保护。由于美国政府和早就去美国的中国“异见分子”并不知道真相,误以为余杰揭开了一个国家领导人(余秋里?)的历史面目,而这个国家领导人又残酷地迫害了余杰,因此,居然被余杰申请成功。他以“反政府的异见分子”的身份成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特殊机构向中国政府开列的“人权保护名单”中的一员。
为了符合这个身份,余杰在美国等地对余秋雨的批判用词越来越高,现在直接称余秋雨是“文革打手”、“四人帮打手”,证人只有一人,就是孙光萱。
余杰的聪明在于:如果中国政府查问他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原因,他写的文章虽然不少,真正造成社会影响的仍然只是“批判余秋雨”,与国家安全丝毫无关,中国政府也不能对他怎么样。他的主要麻烦,是要让美国方面继续相信他,因此他还要把余秋雨的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2004 年 7 月,由余杰间接授意,北京几个三流文人策划,《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的记者张英等人拜访孙光萱,根据孙光萱的思路对余秋雨三十多年前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并公布孙光萱自称从家里拿出来的所谓“清查材料”。
这一动作,以个人随手出示的“家藏材料”冒称档案公布,构成了对“两个凡是”时期整人运动的肯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否定,因此引起了上海市各个政府机构的高度重视,开始了历时一年之久的反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作为全部批余事件起点和重点的“石一歌”事件,与事实完全不符。调查报告很长,与这个重点相关的结论是:
1, 余秋雨在 1973 年参与的,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成立的“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他写完鲁迅在广州的一段生平后就离开了;
2, 教材编写组的部分成员,在 1974 年被调到上海巨鹿路作家协会组成以研究鲁迅为任务的“石一歌小组”。查阅这个小组的 229 次会议记录,没有一次有余秋雨的名字,而孙光萱则参加了210 次;
3, 孙光萱、古远清声称,即使那个由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的“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也归属上当时的上海“写作组系统”管辖,并借此无限上纲。据查,当时上海的“写作组系统”是一个与“公检法系统”、“工业组系统”、“财贸组系统”并列的政府管理机构,所有的大学、研究所、编辑部都受它管辖。当时与教材编写组一起受它管辖的,还有周恩来同时指示成立的《英汉大词典》编辑部、《辞海》编辑部、《汉语大词典》编辑部、《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编辑部等,都有杰出成果,至今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使用,不能因为它们存在于七十年代前期的上海,就予以否定。
与批余浪潮中,一个在文革中曾担任造反兵团首领的叫金文明的人后期加入,于 2002 年突然揭露余秋雨的著作中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在《南方周末》和香港的《明报》、《信报》发表,又在大陆和台湾出书,全国有二百多家报纸报道,又一次造成海内外轰动。
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梁启楷分析,金文明所谓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可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排校差错,与余秋雨没有什么关系,金文明指出来是应该的,但完全没有必要发动这么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更何况,这些排校差错,绝大多数在余先生后来的文集中早已改正;第二部分是金文明学识欠缺所致,把自己不了解的文史研究新发现当作了错误;第三部分是历来有争议的文史疑点,余先生选择了其中的一种答案,却因为写的是散文,不可能以注释说明选择的理由;第四部分是“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对立,金文明认为古书里用过的词汇和含义一旦被人改变,就是错误;第五部分是金文明牵强附会,诬赖余先生,例如他抓住余先生写到过《康熙字典》,就诬赖余先生认为这部词典是康熙皇帝一个人自己编的,然后进行批判。”
很少有读者逐条去查阅金文明的每一个指摘,但是,当代我国文史领域的顶级权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却花费精力查核了金文明的各项批判。 2003年 10 月 19 日,章培恒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通过个案分析,对金文明借“文史差错”之名攻击、诬陷余秋雨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作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到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为了掩盖章培恒所作的这个结论,金文明戏剧性地制造了一起“余秋雨剽窃章培恒”事件。他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揭发余秋雨在早年的戏剧史著作中剽窃了章培恒《洪升年谱》中的四百个字,然后又在2004 年第 4 期《文学自由谈》上专门论述了这个“剽窃事件”,还为此出版了两本书,在封面上就印着“剽窃”二字。由于“剽窃”的指控远远超过了他以前伪造的“文史差错”,又一次全国轰动。北京肖夏林等人还借这个事件,发起把余秋雨驱逐出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运动。
当这个事件在全国范围(包括香港传媒)闹了很久之后,今年年初,资深编辑海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查到了被“揭发”的余秋雨原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惊奇地发现余秋雨在引述章培恒那四百字时是明确作了注释的。他在震惊之余把原著相关部分(大陆版425 - 426 页,台湾版 461 页)拍了照片,投寄报社揭露真相。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收到黄海星的文章和照片后打电话给金文明,问他为什么把明明有的注释说成没有,金文明轻松地回答,“我是想当然。”《南方都市报》在2005 年 5 月 4 日把这个伪造的剽窃事件揭露出来了,但是,以极大篇幅刊登金文明造谣文章的《中华读书报》、《文学自由谈》等各种报刊,却完全沉默。海星认为金文明自称“想当然”也是伪造的,因为他曾一再声称逐字逐句地查核过原著。
2005 年 8 月,章培恒教授亲自在病中写出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发表,认为金文明绝不是“想当然”,而是蓄意诬陷。
为此,海星撰文指出:“在公共出版物上诽谤一位大学者‘剽窃',这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小事。这样的案件不是靠道歉、赔款就能了结的。我们国家的法制,什么时候能够严惩越来越嚣张的诽谤者,保护越来越稀少的文化创造呢?如果真有那一天,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许有了一线希望。”
因为所有的诽谤都围绕着海内外读者非常熟悉的余秋雨,所以每一件都引起全国轰动;过了一阵,诽谤的漏洞出现了,谣言破碎,但多数媒体就不再吱声,也不辟谣,只是期待着新的诽谤的产生……
——这已成为这些年“余秋雨事件”的模式。由于这样的诽谤既能一夜成名,又能搏取稿酬,败露后还很安全,所以形成了一支固定的队伍,海外学者称为“围绕着一个名人过日子的寄生虫队伍”。
所有的诽谤不断地自生自灭,其实仍然都是从那个原始诽谤滋生出来的,那就是由孙光萱、余杰一手制造的“石一歌事件”。
对于这个一直挥之不去的原始诽谤,余秋雨采取了一个最无奈的办法,在《借我一生》中发出悬赏,大胆宣布“只要有人能指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布。”
这个悬赏,全国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至今已有一年多,没有一人来指证领赏。由此进一步证明,所谓“石一歌”是一个纯粹的诽谤事件。
在余秋雨发出悬赏之后,一些原来在诽谤中处于主角地位的媒体开始悄悄寻找下台的台阶。从二 00 四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一种所谓“余秋雨虽然没有问题,但态度不好,因此遭受攻击是自作自受”的论调。他们认为应该有的态度是:不管人家骂得对不对,应该立即认罪,求得大家谅解,然后慢慢说清真相。
余秋雨虽然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诽谤者辩论过,甚至在他的笔下和口中也从未出现过那些诽谤者的名字,但他确实没有认过“罪”。
这种“没问题也应该认罪”论调,首先由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发出,在该刊编辑部隆重推出的一篇总结“余秋雨事件”的文章中,声称“原来余秋雨的问题,只有我预想的十分之一,因此他的主要问题是态度。”对于《文学自由谈》的这种下台阶遁词,评论家赵盾指出:“它原来诬陷一个人犯了十次重婚罪,有十个不合法的老婆,后来经查证,这一个人从来只有一个老婆,就只好改口说,这个人的问题只有原来预想的十分之一。”
最典型寻找这个遁词的,是《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他参与了孙光萱最大一次诽谤事件后,一再装作“中间人”的形象进行评述,却完全掩护和美化了孙光萱、余杰、金文明等人的行径,只对实在做得太愚蠢的古远清略有微词。他在一篇评述余秋雨事件的文章中引述他最满意的一段话来规劝余秋雨:“你既然没有任何事情,就应该及早认罪获得别人尊重。”这是一种在中国非常典型的整人逻辑。但是,既然没有任何事情,那又要认什么罪呢?他引述说,“因为别人的书不好卖,你的书那么畅销;别人上不了电视,你却经常受邀于电视台… ”认的就是这个“罪” 。
从《文学自由谈》和《南方周末》如此找遁词 的情形看,延续多年的“余秋雨事件”大致已经结束。只剩下被多数读者认为精神不是很正常的古远清、余开伟两人还在继续用本名和化名写文章、出书,那也只是借“余秋雨”三字赚钱,与坊间大量印着他名字的伪本书一样,不会引起正常人注意了。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鲁滔先生撰文指出:“余秋雨事件”不应该这样结束,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对公民名誉权、人身权进行法律保护上的极度薄弱。这个事件的很多参与者,包括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在正常的法制国家都要承受刑事罪责,有的还会很严重,比如那个古远清。因此,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一部比较完整的负面教材,供后人研究中国当代司法史和传媒史时分析、解剖。



















![>邹平王传民 [邹平民间借贷]邹平高利贷王传民又谁 邹平高利贷事件始末](https://pic.bilezu.com/upload/c/92/c9277ca6c93844ebdb3e5a6fac7bde3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