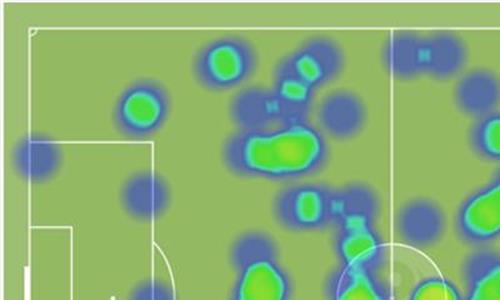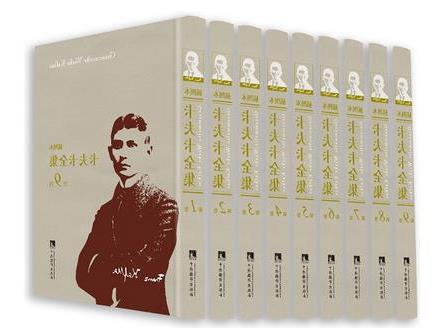【卡夫卡城堡】如何理解卡夫卡的《城堡》?
读那本书那年是1993年,我二十出了头。《城堡》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无聊的一本书,那之后我再没读过也不想读它。但这本书又是最重要的,它启发了我的创作,之后无聊、荒诞都是我表达的主题。现在我鬼哭狼嚎的跑调歌曲出了名,已经说不清到底是我做的事情荒诞还是这个世界荒唐了,人生本就如此吧。
生下来的我就是个噪音,无聊和荒诞就在童年记忆里。在船上长大的我,别人还在小学时就跟着父母跑船,沿着长江、运河、太湖、巢湖华东这些水系走,父母干重活儿,我干杂活儿。晚上总会有人上船偷东西,运什么就被偷什么,水面上死人也经常见到,随随便便就死了。
后来我不想再和这些东西打交道了,太恐怖了,而且也干不了,我是一双娘炮的手,干不了走船这个事儿。小时候的我会什么呢,会喊,嗓门特别大,没人喊得过我,在运河上面大喊,能叫到另外一边船上的狗叫烦,并且轻而易举。
我留下第一个荒诞、无聊的作品可能就是长江上,一个小孩在对着掉下船的尸体扯着嗓门大喊。
从那个环境跑掉了的我,去当兵,去上海卖打口碟,又跑到北京组摇滚乐队。
在1993年的夏天,朋友孙孟晋推荐给我《城堡》这本书,那时我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一个月左右。那个年代看电影看的都是没被剪辑过的外国片,录像带一放出来屏幕都是雪花飘飘的,我和黄渤这个同学唱的《一剪梅》里就提到了这些。
当时好多文学的译本都找不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版新的了。但是孙孟晋他们那些文艺青年家里书很多,一屋子都是书。
受的教育很少,初中都没毕业的我,但是写歌又想写得和别人不一样,需要读书获得些启发,人哪有什么天分啊,基本都是扯的,快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让孟晋推荐他认为的十本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书,到北京后,他写信把书单寄给了我。书单上第一本就是卡夫卡的《城堡》。我问他如果10本只看一本,那看什么,孟晋说看《城堡》。
读《城堡》的时候我住在东村,在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现在应该是朝阳公园。我们一群穷得要死的做艺术的年轻人聚集在那儿,给自己待的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北京东村,为的是和方力均、岳敏君、杨少斌他们住的圆明园的「西村」呼应。
《城堡》这本书看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了,大概几个月吧。书既不色情也不好懂,没有奇怪的东西,非常无聊,完全是硬着头破看下来的。在那个闭塞的年代,我连卡夫卡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
它的故事都是隐形的,没有正常的叙事和爱情。大概讲了一个人想进入城堡,好不容易进入了城堡,这个城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之后什么样子书没写完卡夫卡就死了。太无聊了。时隔很多年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那时我每天就是练琴、唱歌,有空了再读读书,有酒喝就更好了。当然喝酒是很少的,因为喝酒要花钱,都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回头看看,没法说清楚是怎么活下来,很多时候一个穷人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根本没法说清楚,除非编故事。
书里面K在寻找城堡,我看着觉得K就是我,也是身边很多人。那时候东村里的每个搞艺术的都是K.走在那里,感觉所有人都在认真地无聊,认真地荒诞。
东村除了臭就是脏,路边池塘里泛着死猪的白肚皮,苍蝇乱哄哄地到处飞。到处都是长头发、大胡子的人,有的在光腚儿,有的把自己吊在房顶,屋子里还烧着火。还有比如张洹那个就更狠了,全身涂满蜂蜜和鱼的液体,光了身子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到处都是苍蝇。我就在房子里天天练呼喊,整座院子都被我弄得震天响,在练一种秘笈,怎么样轻而易举地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
就在这种乱七八糟的环境里,我读完了《城堡》。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读这本书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一个年轻人,跑到北京鸟不拉屎的地方,跟一群长头发、大胡子的人待在一起,还爱光腚、在看一本这么无聊的书,竟然还看完了。但是之后,我就明白了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儿,当代艺术对于人生就是这样荒诞。同时也给了我启发,就是要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还有更荒诞的,1995年我和东村的人一起做了件事,《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最初的想法是把人关在一个笼子里面,锁好,锁上有个窗口让他透气别闷死。从建国门买张票,把这个人抬进去,放到地铁里转一圈,到了晚上再把他抬出来。后来觉得有人做过类似的了。就改成了后来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10个人脱光了按体重大小从下往上叠在一起,一共五层,说是要给山增高一米,还特地找国家测量局的来量一下子,搞得特别认真似的。有什么意思,其实没有意思,但它是艺术。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肯定很牛逼,因为投资太大了,2000块啊!我们10个流浪汉,每人凑了200块钱份子钱用来请摄影师、租车。
后来这个东西被说得很有思想、很有深度,我就不服,它就是无聊和荒诞的作品,就是种无聊荒唐的表达,这就是卡夫卡啊。我们在用无聊和荒诞来寻找城堡。
过了4、5年这张光屁股的破照片卖了2000块钱,回本了,这个才是最荒诞的。
后来,东村、西村的人分散去了798、宋庄,这两个地方也渐渐成了文化现象。
再后来我唱词《小莉》,更多人知道我了,好多人说这是爱情歌曲。前几年,陈升跟我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整张专辑都是爱情歌曲,我才知道世界上只有爱情歌曲才能火啊。其实我唱的东西都是那样,就是我自己想怎么来怎么来,我去年还唱了《我要发横财》呢。我是真的想发横财啊,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发财,那可能就要去抢劫了,所以还是让我发财吧。
这些年,我没想过刻意表达什么,也没想让谁去理解、读懂,那样的话要累死了。但是这么多年做下来发现,其实还都在卡夫卡的这个套子里,无聊、荒诞、疏离、恐惧。我也说不清到底是自己做的事情荒诞,还是这个世界荒唐了。人生就是这么荒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