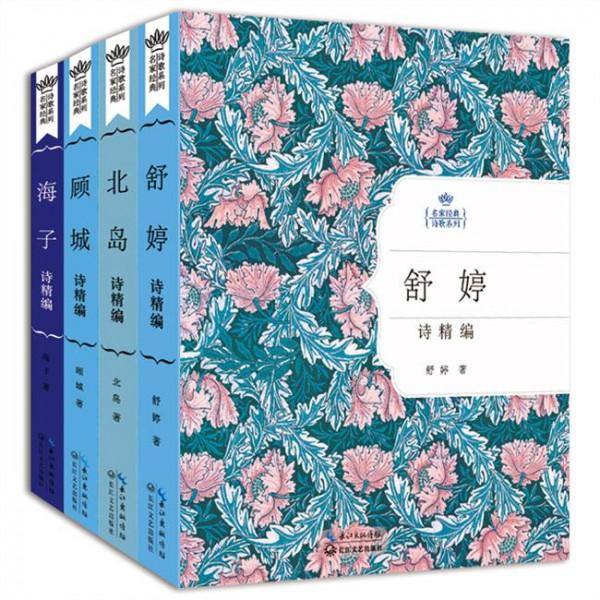【中岛敦山月记】山月记(中岛敦)
陇西[①]李徵博学聪慧,才情颖异。在天宝[②]末年,仅弱冠之年就进士及第,身登虎榜,随即被补为江南县尉。由于性情狷介,自视颇高,因而不甘心做一个卑微的小吏,没过多久就辞官还乡,返归故里,在家乡虢略隐居。

由于整日沉湎于诗词歌赋,所以断绝了与时世、士人的往还。李徵自忖:与其做个低等小吏,在长官面前卑躬屈节、低声下气,还不如做诗人百年之后名垂青史,千古流芳。但是,文名尚未远播,生活的困窘却与日俱增。李徵渐渐地焦躁不安起来,相貌也变得冷峻峭刻,脸颊深陷,只有双眸依旧炯炯有神。

那个往昔进士登科金榜提名时面容丰美的少年形象再也无从寻觅了。几年以后,由于不堪忍受的贫穷困顿,也为妻儿老小的衣食生计,不得不再次屈膝忍辱效力官场,前往东部担任一个地方官吏。
李徵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他对自己选择的诗歌之路有些绝望,一是过去的同年、同僚都已经进位升阶,高官厚禄,而他如今却不得不向这些自己过去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愚钝之辈颔首拜谒。

此事给昔日才俊卓异、傲视群雄的李徵以莫大的伤害,他益发地孤介、自尊。因而他在官场总是郁郁不乐,狷狂的个性越来越难以自控。一年以后因公外出,旅宿汝水河畔时,终因绝望而发狂。那天夜半,李徵脸色突变着从睡床爬起,一边嘴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一边喊叫着下了床,冲入幽暗之中,再也没有回来。随从的人搜遍了附近的山野,也没有找到李徵的任何踪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晓李徵的下落。
翌年,祖籍陈郡的监察御史袁傪奉诏出使岭南时,途中在商于地界歇宿。次日凌晨,天色未明时就要出发。这时,驿站的官吏解释说:“从这儿往前不远的路上,有吃人的老虎出没,行旅之人不是白天是不敢通过的。现在天色尚早,官人可以在此稍做等待,天亮以后,再走不迟。
”可是,袁傪却依仗自己的随从人多势众,并没有理会驿站官吏的劝阻,立即登程上路了。借着残月的微光,袁傪一行正要通过林间草地时,果真有一匹猛虎突然从草丛中一跃而出,眼看就要扑到袁傪时,却在瞬间回转身体,隐入了草丛之中。
接着,从草丛里传来了一个人反复念叨“好险哪!好险哪”的话音。袁傪听着这声音特别耳熟,在惊惧之中猛然想起什么似得,便叫到:“哎呀!那岂不是在下好友李徵的声音吗?”袁傪和李徵同年登进士第,友人甚少的李徵,袁惨算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了。那或许是因为生性温和的袁傪和性格狷介的李徵从未发生过冲突的缘故吧。
草丛中,良久没有回应,却不时传来隐忍的、微弱的哭泣声。好一阵才低声应答:“在下确实是陇西李徵。”
袁傪忘记了恐惧,翻身下马,走近草丛。用眷恋的口吻说道:“久违了!”“我们在此重逢,年兄为何不愿现身啊?”袁傪问。
李徵的声音回答说:“现如今在下为异类之身,如何可以腆着厚颜在年兄面前显露卑贱的形体呢?况且,如若在下自行现身,必定会使年兄你心生恐怖厌恶之情。可是,在下的确没想到会在此见到故人,此刻是依恋之情胜于自惭形秽(羞惭)之念。倘若年兄不嫌弃在下如今丑陋的外貌,就请稍稍耽搁一点时间,和你以前的老朋友李徵叙叙旧吧。”
此事倘若在以后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那时,袁傪竟坦然地接受了这超自然的怪异事实,没有丝毫见怪。他命部下停止前行,自己站在草丛旁,与那看不见的声音对谈起来。他们二人谈到了京都的传闻、旧友的近况、袁傪现在的地位、以及李徵对他的祝福。青年时代就声气相投的两个人,用没有任何隔阂的语调谈了上面那些话之后,袁傪问寻李徵是何缘故变成现在的姿容,草丛里的声音讲了以下的话语。
大约距现在一年多以前,在下出差夜宿于汝水之滨,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的瞬间,就听到门外有谁在呼唤在下的名字,应声走出门外时,那声音在幽暗处召唤着。在下不自觉地就跟着声音跑了出去。象在梦中一般忘记自我地跑着、跑着,不知不觉一直跑进了山林。
并且在不自觉间在下的左右手都可以着地奔跑,感到身体内部犹如灌注生气一般充满了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飞跃岩石峭壁。当在下清醒过来时,手指和臂肘的部位都长满了毛。天色微明后,看到山谷溪涧映现着的自己的身影时,在下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老虎。
起初在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想这是仍然是在做梦,就犹如自己曾经历过的那种一个梦中还套着的另一个梦的境域一般。等觉悟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是梦的时候,在下茫然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在下完全无法判明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因而内心感到非常惶恐。
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下不名究里。其实有时侯,我们完全不需要判明是怎么回事。不需要判明真相地接受强力意志的胁迫,不需要追寻理由地活下去,这就是我们作为生物的命数。在下想到了即刻去死。就在那时,当看到一只兔子从眼前跑过的刹那,在下身体内“人”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人”的知觉再次在体内苏醒的时候,在下的嘴巴已经沾满了兔子的鲜血,周边散落着兔子的皮毛。这是在下身为老虎的最初经验。自那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下接连不断地还做了些什么,实在是不忍再次提及呀。
只不过,每一日里必定会有几小时会复苏人的意识。复苏的时候,和从前一样,可以说人话,也具备复杂的思辩能力、可以背诵四书五经的章句。以人类的心灵尺度,审视自己变为老虎之后残虐的行径。
反思自己的命运时,是悲哀、恐惧、慨叹的。可恢复为人的时间随着岁月的推移日渐缩短。到如今,居然想到自己以前为什么会是人?实乃非常恐怖之事啊!或许再过一些时日,在下自己身体里的人性,也会完全消失于身为野兽之后习性之中吧?犹如古老宫殿的基石慢慢被砂土掩埋一般,最终,在下会彻底地忘却自己的过去,完全作为一只老虎疯狂旋转,啸傲山林。
像今天这样,即使在途中遇到年兄,也无法辩识年兄是至交好友,将年兄生吞活剥了也不会有丝毫的悔愧之意吧。
兽也罢,人也罢,究竟应该如何区分呢?刚刚觉识到这类问题,旋即又可能会忘记,难道在下不是一开始就认定自己应该是如今的模样吗?唉,那事无论如何都无所谓了。
或许,自身里面的“人类之心”消失净尽,反倒会是在下的福分吧!可是,在下自己的“人类之心”现在却对此事感到无与伦比的恐惧。成为兽类,那该是多么令人恐怖、悲哀,难以想象的痛苦啊!在下这样的心情谁人能理解?谁人能体味?除非他自己也变成在下现在这样。可是,那样的话……在下的“人类之心”完全消泯之前,想请年兄答应一个请求。
袁傪一行屏住呼吸,凝神倾听来自草丛那不可思议的谈话语,那声音还在继续着:
其实也没别的。在下本来打算作为诗人文名远播。岂料夙业未成,就遭遇如此命运。在下曾作诗文数百篇,尚未在士人中流传,原稿也不知散遗何处。幸好现在还可以记诵其中数十首,烦请年兄代为笔录。并非想藉此成为诗界名流,也不晓拙作工对是否恰切。但不把这些令在下家产尽失,心神迷狂,曾经半生执著的诗作,哪怕是一小部分传之后世的话,在下即使去死,也会死不瞑目的。
袁傪令部属取来笔墨,跟随草丛的话语逐句笔录。李徵的声音从草丛朗朗响起。长诗短章计约三十篇。作品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一诵既知作者才情超凡。袁傪一边慨叹,一边隐约感觉:不错!李徵禀赋一流是毋庸质疑的,可即使如此,要达致诗歌神品,他的诗在那非常微妙之处,似乎又缺点什么似得。
吟罢旧诗,李徵的声调突然一变,自嘲的说道:
真是令人羞愧呀,纵然在下变成现在这可怜模样,可在下仍然梦想自己的诗作为长安城里风流雅士传诵。这是在下横卧在石窟岩洞里做的梦。耻笑在下吧!耻笑梦想成为诗家却错变为老虎的男子吧(袁傪记起青年李徵有自嘲之癖,悲切地默然倾听着)……那好,既是笑柄,我就即兴吟诗一首,见证这老虎中存活着的仍然是当年的李徵。
袁傪又命部属记录此诗,李徵的声音(老虎)吟道:
偶因狂疾成殊类 灾患相仍不可逃
今日爪牙谁敢敌 当时声迹共相高
我为异物蓬茅下 君已乘轺气势豪
此夕溪山对明月 不成长啸但成嗥
这个时候,月残、光冷、晨露侵袭大地,穿越树林间的寒风告知人们拂晓将至。可每个人完全忘了事情鬼谲,寂静地在内心感叹诗人的不幸。李徵的声音复又响起:
在下先前曾说不解自己为何遭此命运,但仔细思忖,也不能说是全然地意外。在下为人的时,刻意回避与他人的交往,导致所有人以为在下倨傲自满、妄自尊大。其实,他人并不知道,那是一种近乎自卑的羞耻心作祟。不言而喻,被呼为故乡鬼才的在下,不可能没有自尊心。
但(现在看来)那是近乎怯懦的自尊心罢了。在下一面想成就诗名,一面却不愿拜师求教、也耻于和诗友探讨,切磋诗艺。固守高洁,不与流俗为伍,而这完全是在下怯懦的自尊心和可怜的羞耻心导致的。
既忧虑自己并非珠玉,又不愿刻苦磨砺,另外,又有几分相信一己或可以琢磨成玉,因此,不屑于与碌碌无为的瓦当共处。渐渐地远离世间,疏远人事。其实是愤懑和羞惭越来越的育肥了内在本来孱弱的自尊心的结果。
每个人的性情中都有兽的一面,各人都应是自己的驯兽狮。在下的猛兽就是妄自尊大的羞耻心,是猛虎。在下的羞耻心使自己蒙受损失,使妻子儿女痛苦,也使朋友受到了伤害,结果,自己的外形和内心变得难以相称。
而今反思自己,完全空耗了仅有的才华。所谓 “人生何事都不做嫌太长,凡事都做则嫌太短」之类警句,简直是文人的卖弄,只不过是暴露出自己才情不足、卑怯的危惧感和厌憎刻苦的懒惰而已。那些比在下更缺乏才识的人,为了成就梦想,经过专心致志的努力后,成为威风凛凛的一代诗家者大有人在。
如今变为老虎,在下终于明白了一切。想到此,真是灼胸透骨般地痛悔。可是,在下已经无法回复人的生活,纵令头脑仍可成就妙诗美章,可又能靠何种手段去发表传播呢?更何况,在下头脑一天比一天更靠近老虎。
真不知如何是好?在下白白耗费了过去时光。一旦想起都难以承受。每当此时,自己就爬上对面山顶的巨石,向着空谷咆哮。多想向人倾诉自己烧灼心胸的痛苦啊。
也就是昨晚,在下无法排遣心中的伤痛,在那里对着月亮怒吼。但是,兽类听到我的狂嚎,只有恐惧、畏服,而山峦、明月、露珠,全都无法体会是一只老虎捶胸顿足地狂怒咆哮,伏天抢地地哀婉嗟叹,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痛苦内心世界。就像为人时,无人洞晓在下那容易受伤的内心一样。濡湿在下老虎皮毛的,又岂只是夜间的露水?
渐渐地天光微曦,暗夜淡去。黎明的号角穿响彻林间,哀怨凄婉。
不得不告别了。“在下不得不去陶醉了”(不得不还原为老虎了)李徵的声音道。“辞别前,在下还有一事请求,事关妻儿。如今家小依旧居住虢略,尚未知晓在下运命。年兄若从南方返归,烦请告知舍中在下已经辞别人世,万万不可明告今日实情。此乃在下的厚颜之请,年兄勿怪才是。年兄如若怜悯寒舍妻弱子孤,帮补一二,使其免受饥馑冻馁,也算对在下恩遇啊。
言罢,草丛里传出恸哭之声。袁傪也噙着热泪,欣然应允。李徵的话语很快回复了先前的自嘲口吻:
“在下果真是人的话,应最先请求此事,可惜,在下关注一己微不足道的诗名远甚于饥寒交迫的妻儿,沦落兽道不足怪也!”
李徵又道:“另有一言,请年兄谨记。兄从岭南返程时,万万不可再走此路。那时,在下或许沉醉虎身,不识老友而袭击!今朝一别,年兄登上前方百步之遥的山岗,请往此处回首,再看一回在下如今的模样,非是夸耀好勇,乃是希图再现丑陋身姿,年兄就不愿再路经此地看到在下了。
袁傪面向草丛叙说道别之言,抬身上马。草丛里传出难以抑制的悲泣。袁傪频频回头,泪眼朦胧地登程上路。
袁傪一行走上山丘,依照李徵的嘱咐回首眺望方才停留的树林草地。他们看到一只斑斓猛虎从茂密的草丛跃出。老虎朝着失色的残月仰天长哮,数声之后,再度跃入草丛,消失了踪影。
[①]陇西,位于甘肃省西部,陇山的西面,故称陇西。
[②]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公元742-755年。
中岛敦(1909年5月5日~1942年12月4日),小说家。1909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市四谷区箪笥町。1岁时父母离异,由祖父母养育至7岁,并先后在两位继母的教养中成长。内向抑郁,体弱多病。中岛祖父及父亲都是汉学教师,终身从事教育。
受家族影响,中岛有深厚的汉文学造诣。1933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国文学科,毕业论文题目为《耽美派研究》,以420页的篇幅,对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明治时期作家进行评说。4月进入东大大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研究主题为《森鸥外研究》。1934年3月从大学院退学,任私立横滨女子高等学校国文、英语教师,1941年3月退职。1942年末在因哮喘病发作逝世,享年33岁。
中岛敦1932年在东京第一高等学(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校友会发表《有警察官的风景——一九二三年的速写》,描写在日本统治下朝鲜人的意识。以后他在校友会发表作品多篇。昭和17年《文学界》的“古谭”2月号发表了他的《山月记》、《文字祸》,受到文坛注目与好评,接着的5月号刊载了《光与风与梦》,被推荐为介川文学奖侯选作品。
中岛敦的主要作品除上述以外,还有《环礁》、《斗南先生》、《狼疾记》、《悟净出世》、《李陵》、《弟子》、《盈虚》、《牛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