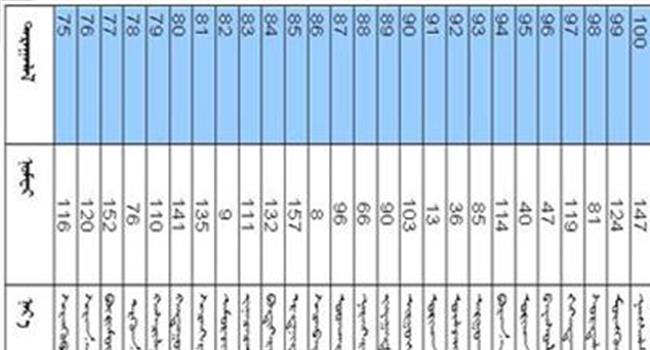吉光片羽歌曲 我的吉光片羽——民居线条之美后记
近日,王其钧的著作《民居线条之美:建筑白描写生摹本》将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中央美术学院王其钧教授是知名的中国民居专家,在本书中读者可以领略到作者用毛笔来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民居之美的热爱。本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首次出版,王其钧在攻读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时,便把自己民居调查的速写与笔记撰写成了本书的第一版。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因书中绘画功力深厚、意境优美的白描插图,而成为国内建筑学和美术学学生学习建筑线描画的最佳临摹范本。
下面是王其钧为《民居线条之美:建筑白描写生摹本》撰写的后记:

后记
我始终相信,人的一生,总会有一次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吉光片羽。
1988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1994年改名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攻读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我正值二年级,我的研究方向是“建筑壁画”。我的导师漆德琰教授应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建筑系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加拿大工作,我属于没有导师指导的状态。

和我的情况不同,建筑系同届的四十多位研究生,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叫到深圳、海口等南方沿海城市跟他们的导师做建筑设计去了。毕竟那是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建筑兴建的高潮阶段,同学设计的建筑规模都是几千甚至几万平米,而且很多方案都被实施建造,几十层的大楼就这样被盖起来,在这个地球上耸立着。这对于西方学建筑学的学生简直就是神话般,因为很多西方建筑师一辈子都只有设计若干几百平米房子的机会。

去到南方工作的同学们,他们的导师还是富有人情味的,每月会付几百元的薪酬给他们。这个酬劳在当时是一个能叫年轻人感觉到手头阔宽的数额,因为那时我母亲退休后继续工作,每月能够多收入150元,她就已经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了。
我母亲那时每个月固定寄给我50元,支助她五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我。我能够读研究生是父母的骄傲,尽管那一年我已经34周岁,与范进中举的年岁相差无几,但是母亲在听到别人夸奖我时,她还是会格外地高兴,因为在我父母那一辈人中,别人家的孩子真的很少读过大学。
看着空空的研究生宿舍,想想自己的同学平均年龄比我小10岁甚至更多,自己心中就产生了一种压力。别人能设计出大楼,我能干什么呢?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建筑学专业出身,少数是工民建专业出身,但我是美术学出身。1974年至1977年我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读书,毕业后的十年都在文化系统从事专业的绘画创作。现在别人都去做建筑设计了,我在学校好像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当时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竟是建设部和国家的重点院校,图书馆的藏书很丰富。为了学习中国建筑史,我借了一本名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书。等图书馆里的老师把这本书递到我手上时,我发现居然是1959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作为编写单位之一的上报书稿。
书的正文全部是用蜡纸打字、手工油墨的油印机印出来的一本讲义一样的、尚未出版的“内部读物”。这就是后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的油印草稿,装订也是用手工缝起来的。
那一刻我感觉我拿到了一本“内部”人才能读到的核心机密资料集。在后来的阅读过程中,我好像不仅是在学习这本讲义,甚至有了一种参与感,书中的内容似乎都不是白纸黑字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变动的内容,我仿佛成了随时要为这本书重新誊抄的编写者之一。
图书馆的资料室是面对建筑系的教师和研究生开放的部门。老师和研究生们都忙于在校外干实事,所以来资料室的人很少,于是这里便成为了我每天读书的地方。资料室里的图书基本都是外文的原版书,当时觉得真是琳琅满目,让我只将它们的封面看一遍都看不过来似的。
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我的专业背景是美术学,建筑学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学科;二是我的英文不好,原文版的书看起来很吃力,有时候书名还得仔细思考一下,才知道这本书大致的核心主题。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资料室对于我来说就有了无穷的诱惑力。
英语几乎是上世纪80年代高校学生最为热衷的学习项目,学生们都梦想能考过“寄托”(GRE和托福)到美国去读书。我们一年级时学校请来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白格勒(James R Bagnall)教授,专门给建筑系的研究生讲授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克里斯多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
由于白格勒是亚历山大的学生,所以学校就请他来讲课,看来名师的学生确实是能沾光的。
当时重庆建工学院的教师英语好的不多,白格勒夫妇的课余时间没有人陪伴。我是一位痴迷于学习英语的人,因为我上中学和大学时正值文革,没有英语课,我是为了考硕士研究生从1986年起才从音标开始突击学习的英文,也从来没有机会与外国人用英语交谈过。
因此有这样一对美国教授夫妇在学校,我自然就主动找上门去给他们当翻译、当导游了。我蹩脚的英语,一开始完全不能和他们交流,但是后来专心练习开始有效果了。
慢慢地,我能够和他们语言交流了。直到今天,我回忆起那一段英语学习的时光都依然觉得激动,因为后来在清华大学学习时,外教都被教师给包了,只有老师有机会课后和外教交流,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和外教接触。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当红的建筑师之一是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大师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那时后现代主义在国外正是流行的鼎盛时期。后现代主义的标志之一,就是反对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的所谓国际主义风格,强调从传统、从地域出发设计建筑,国外许多学者也比以往更加重视乡土建筑和传统建筑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学校附近的沙坪大酒店是一座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当时也是沙坪坝的地标建筑。
白格勒一谈到丑陋建筑时,就会拿沙坪大酒店作为典型案例。可是他对于重庆临江门的大片传统民居、沙坪坝附近的磁器口古镇的民间建筑总是赞不绝口,常常喜欢去这些老重庆的区域行游。我以前也一直觉得这些民居很美,但对于它们美的认知也仅止于出现在我早期创作生涯中的一些连环画作品里。
而在陪同美国教授的行游中,对于他们将中国传统民居的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于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启发。也正值自己的导师不在国内,将中国传统民居作为1988年我给自己制定的研究课题便成为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研究课题虽定下来了,但从何入手又成为了困扰我的问题。反复思考之后,我的思维开始向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的经历聚拢。那时正是提倡“开门办学”的时候。为了画连环画,需要收集乡村的风景作为连环画的场景。我在上海画过一批钢笔写生,后来在苏州乡下住的时间长,更是画了大量的钢笔写生。
我自己的体会是,线描的写生速度快、画面效果好,而且也更方便应用于连环画的创作之中。后来,我在文化系统从事了10年的绘画创作,有相当多的机会去全国各地写生,这种写生民间建筑和住宅并将其收集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已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我想到把之前收集素材的方式和成果与即将要进行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
但是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困难,即在技术和结构上对于民居建筑的理解。具体地说,这本书的插图对于我并无大的挑战,所以将这本书的全部插图用毛笔画出来并没有问题。而这本书的文字,对于当时的我绝对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
好在民居建筑结构和技术本身与中国古代的皇家建筑、宗教建筑等官式建筑相比还是简单很多。于是我的同学汪克在我们一起出行的火车上给我快速地讲述了一次中国古建筑知识。汪克的本科毕业于清华,那一次的讲解就像是专门为我开设的讲座。
后来我自己凭借着对资料的学习,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在初稿完成后,我的另一位同学,现在担任“南方建筑”杂志主编的邵松,还熬夜和我一起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把全书文字都推敲了一遍。现在每每想起这些,总是让我感动。
1989年春天我完成了这本书稿,怀着非常迫切的心情离开重庆去找一家可以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顺便也出去给自己找毕业后的工作。从重庆去上海的轮船要开5天,我只能买得起四等舱的票,但是运气很好,是一个下铺。我当时就把这张床铺作为写字台,参考书摆了一床,因为我还需要誊写正稿。那时没有电脑可以打字,更不要说是笔记本电脑了,书稿都是要用钢笔来抄写的。在到上海的外滩码头之前,我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文字修改和誊抄。
我到上海并不是为了找工作,唯一目的是奔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出版这本书。当时接待我的责任编辑叫孙国斌,他立即把这本书稿给他的领导看了,而且当时就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可以出版。”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不能出版,我就拿到北京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去争取出版。上面是发生在三十年前春天的事。
当年的冬天,我就去了北京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工作。我刚到北京没几天,就从家信中惊悉我母亲患了癌症,并且已经到了晚期。在举目无亲的北京,那个冬天格外的冷。母亲于1990年3月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最终没有等到她资助的这本《中国民居》的出版。
《中国民居》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我拿到了三千多元的稿费。和做设计的同学相比,平均报酬也不相上下。我感谢那个时代。我上大学不要学费,每月还能够拿到13元的补助;我读硕士研究生不要学费,每月能拿到95元的补助。
1993年,我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从吴焕加教授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博士,并于1996年顺利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我父亲是银行的普通职员,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但是我在国内的三家著名大学分别读了书。
在没有托关系、也没有人引荐的情况下,这本《中国民居》就得以出版。回头看看,我的确称得上是幸运的。而《中国民居》这本书也一直畅销,2006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这本书改名为《白描画典藏——中国民居》继续出版,并且一次又一次地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