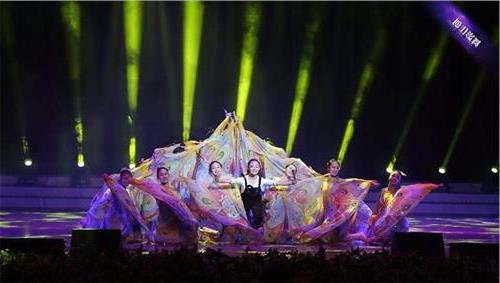吴晓邦舞蹈思想 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拾遗
晓邦老师的道德、人品,作为一代文人的楷模,在建国后一波高过一波的“运动”之中,就我们所知的“名人”,几乎难有出其右者;晓邦老师的思想节操,作为近现代舞蹈史中一笔精神财富,我辈建国后的门生弟子,自觉难以
晓邦老师的道德、人品,作为一代文人的楷模,在建国后一波高过一波的“运动”之中,就我们所知的“名人”,几乎难有出其右者;晓邦老师的思想节操,作为近现代舞蹈史中一笔精神财富,我辈建国后的门生弟子,自觉难以望其项背,能得其九牛之一毛,亦足以挥写一个脱俗的人生。
艺术需要晶莹剔透的胸怀,如痴如狂的追求,其超凡脱俗的境界,又在心不旁骛,尤其难以做到“士而不仕”。千古以来,不肖营之苟苟于功名利禄者,青史之中也是稀客。艺术家没有自身的真善美,又何从体现艺术之中光明磊落的品格?
建国初(1950—1952年)笔者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舞运班做晓邦老师的学生,是初进舞蹈圈;也是初识晓邦老师这位名人。因为还拿不准主意是否就干一向陌生的“舞蹈行”,在众多“同道”之中,我绝不是老师的好学生,既无心下力练舞,对据说是新舞蹈缔造者的晓邦老师也只感新奇。
虽无不敬,却眯眼旁观。耳际所闻的一句评议是说晓邦老师有点“怪”,是褒,是贬,一时还无参悟。
先生让同学们搞编创习作,不知大家何以不约而同地都编骑马。也许因为学过《鄂伦春》,有摹拟骑马的动作吧;我则利用编创的课时,躲到宿舍,躺在床上闭起眼睛背唐诗。
当被责问:“你怎么睡大觉?”回说:“没有,我在构思。”到回课,先生要一一检评了,眼看大家轮番“骑马”,忽来灵机,即兴来了一段“骑驴”——你们骑马我骑驴。实难预料先生的评语居然是:“好哇!有创意!”同学们知道我从来一招一式的“设计”尽在“闭眼”构思,对先生于我的褒奖有点忿忿然,而我,自知先生不会看不出“骑驴”暗藏着调侃取笑的顽皮,一件小事,先生的态度引起了我的惊诧!
到毕业,我又在睽睽众目之下,领取了毕业文凭的“l”号,并继续留校。为什么?透过“组织决定”,我久久思索着晓邦老师对我的期望和评定。再透过期望和评定,领会到知遇之情。
1952年组建中央民族歌舞团,先生任团长,同时受中央委任,以中央访问团名义,赴贵州省“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参加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县(黔西台江县)的建政工作。
途经西安,团部决定为先生配备秘书、勤务员各一名,而先生却提出:“把孙颖给我,秘书兼勤务员!”由此起,我从先生随行的近二十名学生中,得以零距离和先生接触,得以一言一行的解读,参悟晓邦老师究竟是怎样一位时代的艺术家。
耳濡目染虽只“勤务”了数月,却从先生处领悟了人的价值是什么,艺术创造需要什么胆气。作为获得先生厚爱的一名学生,回顾先生的教诲,未辱厚望;苦苦创业也得益于先生;同时又愧而自馁,委实缺少了师承先生胸怀的资质,想学也学不来。
1954年,文化部教员训练班结业,同时宣告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成立。文化部委任先生做校长。先生从中央戏剧学院舞运班、舞研班留一批学生分成古典、民间两个教研组筹备教材,旨在为了开展较为正规的舞蹈教育。
但文化、艺术一并学“苏”,请来前苏联芭蕾舞教学专家,将在中央戏剧学院正式建系改为建立舞蹈学校,先生却拒任校长一职,并在事后得知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不当洋奴才。”(这句话在太仓发言时我略而未说)我辈不意政事的学生,只觉震惊,不知先生不就校长一职是何意;闻到“不当洋奴才”,几经思谋才觉得事关民族气节,一个全无中国文化素养的芭蕾舞中专教师,能怎样指点江山,导演中国民族舞蹈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取向呢?多想则堪虑,时代决策很难保障民族艺术的“自主权”。
先生之所虑,或许当时不被理解。而其后的思潮,乃至今日的大势,又当怎样认识先生早已预见的“自主权”问题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仿苏学苏的历史功过已成为有“教训”的历史,舞蹈这门艺术也是从那个时代同步走来,是否既受益,也后患无穷呢?
先生拒受校长一职成为事实后,我去找先生,望能透过现象多知一点其中的内情,然而先生的思想深藏不露。若干年后方知先生的谨慎,不能损害于没有承受能力的小小学子。然而除“勤于学习,好好工作”之类的叮嘱,却还是道出了“真谛”:“要自主,要学会自己走路!
”不厌其烦地说了几遍,恰好点拨了迷惘之中的我朦朦胧胧的一些思考。几十年中之立志重建中国古典舞,也在于先生当年的一句话,变成誓言一直回响在心间。
恰在学习、思考,欲辟的事业门径悄悄地在头脑中开启之际,老天又为我的人生安排了二十余年的劳改生涯,一道沟坎,跳不过去充其量跌到沟底爬上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十年八年望不到尽头,可就难以乐观地跋涉了。
还讲事业,(本文来自领舞网)还讲追求,还讲“自主”,还讲创造吗?记得是在“文革”狂飚即将横扫全国的前夕,因为被庸医误诊为“食道癌”,费了不知多少口舌,才获恩准,怀揣此人是“五类分子”沿途军警严加监管的路条到北京就医。
到京数日就想去看先生,而当年舞运班教务干事潘继武老友还却一通的“挡驾”,劝我不要去见吴老师,我只好采取迂回战术,避开老潘“直捣”先生涂梅写竹的画室。
相见之下先生依然笑嘻嘻地打招呼:“孙颖你好哇。”而我已知先生的处境。停立许久也没能说出一句得体的话来,我很自知,心想能得一见其愿足已,不可久留。先生看我不说话,无疑是认为我心情悲怆、沉重,收起悲诲的笑容,有点严肃地凑近,犹如耳语低声说:“你受苦啦……你不会垮的吧!
”一时间彷佛又跳回到一九五二年,跳回到贵州苗家小楼,围着火盆听先生讲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艺术、为理想而拼搏的故事。
不同样是面对创业的艰难吗,只顾愣神却忘了回答先生的话,只说了一句“老师保重”,遂即抽身离开画室。到了街上,才让两行泪流下。也只两行,我不想哭泣,回望画室,斩钉截铁的心语只有四个字:“我不会垮!
”即有其师,就有其徒。学得先生的精神,足可笑对风风雨雨,足可笑对坎坷人生,先生能生存于你所处的时代,我也能生在于我所处的时代。你能开辟,我就能继承。先生能守君子之道而不二,学生也能情系中华而不移。跟先生上课,我溜边偷赖的时候,不敢说我是先生的学生,到如今,先生虽已仙逝,我也是耄耋之年,却因为半生创业得益于先生光辉思想的感召,并因此而小有成效,才足以扪心无愧地自诩曾是先生的弟子。
此文作为对先生的缅怀,不过一枝一节,而我辈后人,又怎敢说完全认识了吴晓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