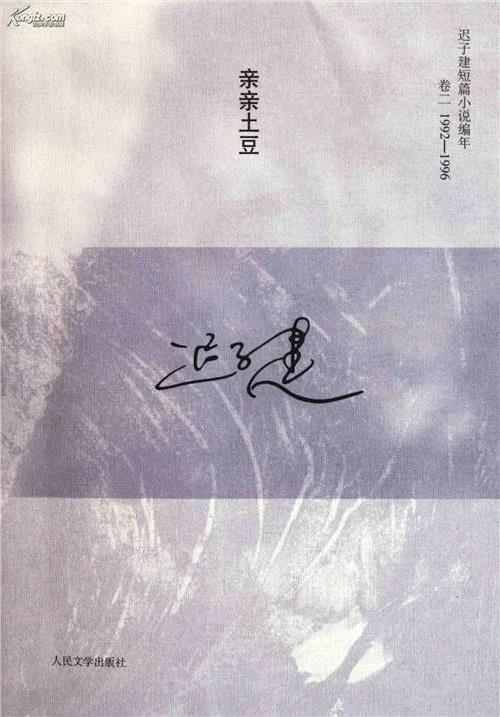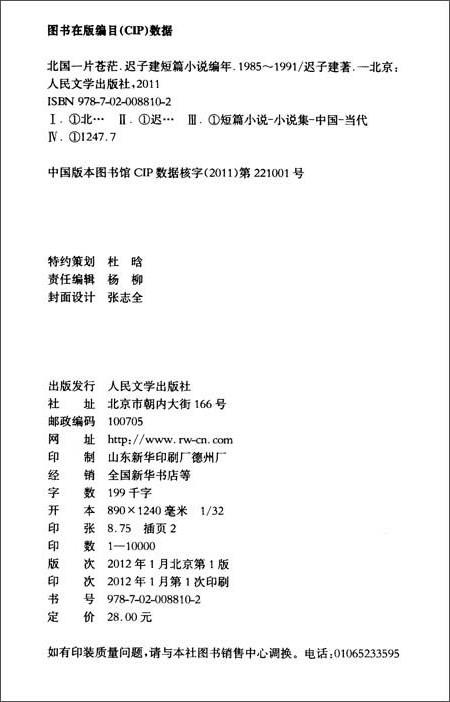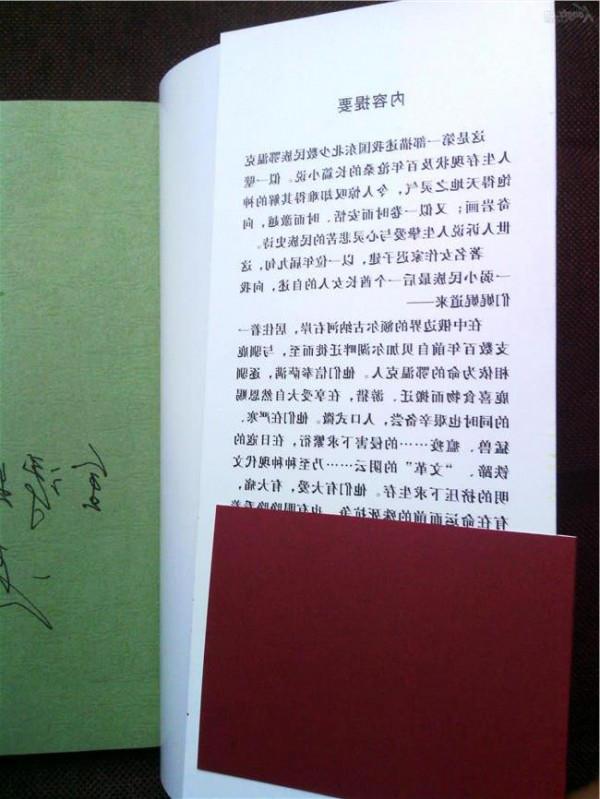迟子建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集,迟子建分别从其中挑选了一篇来统领各卷:《北国一片苍茫》、《亲亲土豆》、《花瓣饭》,在迟子建眼中,它们也能代表各个时期,自己短篇的特质。
“最初写作时,对世界的认知,可以用‘苍茫’一词来相容,朦胧,微微的隔膜,但也有一股天然的美好;进入《亲亲土豆》和《花瓣饭》的写作时,体味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世界的迷雾渐次消散,知道最朴素的情感才是最美好的。这一时期的写作,非常踏实;而到后来,我真正理解了‘沧桑’这个词的含义,懂得随遇而安对人生和写作的重要。‘土豆’、‘饭’它们是我生命的命根子,也是我写作的命根子。”
从写作开始,短篇就没有离开过迟子建,而在旁人看来,短篇仿佛有些“费力不讨好”,很多曾经以短篇成名的作家都转移了阵地,开始了长篇小说或是剧本的写作,只有迟子建,还在坚持着,在这二十多年来,无论外界的诱惑多大,她都从未想过放弃短篇小说的创作。“其实好的短篇,依然会给人以震撼!契诃夫和鲁迅先生,都是以写短篇见长的,他们的短篇直到如今,依然为大家喜爱。短篇小说确实极少有改编成影视剧的,在这个时代,这是它们受冷落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不会放弃短篇的写作,因为它们是我写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的故事和题材,只有短篇来演绎和承载才是完美的。”
作家某种意义上是裁缝
《亲亲土豆》和《清水洗尘》是很多读者最喜欢的两部作品,它们既有生活的哲理,又温馨,在迟子建的心中,这两篇也很受偏爱,也很受偏爱,并且也确实是来自生活的启悟。“有一年我去省医院开药,在一楼大堂,遇见一对农民夫妇。男的躺在担架上,面如死灰,女的守在他身边,满面忧愁。他们之间不说话,只是彼此相望着,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一楼大堂人来人往,他们毫不在意,好像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存在,我被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想那男人也许得了绝症,他们才会有如此情态。什么是爱情?那个瞬间我看到了。
写作《亲亲土豆》,我就是照着这对农民夫妇的面貌来写的,那种穿越了生死的爱情,是大爱情!而《清水洗尘》的故事,则与我童年生活的经历有关。在大兴安岭的小山村,每到腊月二十七,我们就要‘放水’,所谓‘放水’,就是洗澡。一家人都要在这一天洗个澡,辞旧迎新。因为那晚家人都要洗澡,烧热水比较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得用大人洗过的洗澡水洗澡。而任何一个小孩子,都特别渴望着能独享一盆清水。这样,便有了《清水洗尘》这篇小说。”
迟子建很多的作品都来自于生活,如何来处理这些素材,迟子建用了一个幽默的说法。“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裁缝,如果提供给你的布料,只够做件短衫,你却偏要缝个斗篷,或是可以做个斗篷,你非要做件短衫,都是不可取的。体裁,在我理解就是对素材量‘体’裁衣,只有恰当和适度的裁剪,你掌握的材料才会‘出彩’。”
快五十还能拿到压岁钱
人情味、自然、和谐是迟子建短篇小说的一部分主题,在其中能看到她对幸福、人性的理解。其实,生活中的迟子建对生活的定义很简单,与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她只求生活简单、朴素、自然、安静。“简单、朴素、自然、安静的生活,在我眼里就是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时刻有很多,它们都在普通的生活中。比如我这个快五十的女人,在除夕夜给母亲行大礼拜年时,依然能从一双衰老的手上,得到自童年以来一直得到的压岁钱,你知道即使自己有了白发,但在一个人面前永远是孩子,这个时刻无疑是幸福的。”
生活中的幸福可以是由自己定义,在写作中的幸福却有很多是外界加注在其上的,比如奖项,迟子建获得过三次鲁迅文学奖、一次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在本次的短篇小说集中《雾月牛栏》和《清水洗尘》分获了两次鲁迅文学奖。当如此多的荣誉向迟子建扑来时,她更多的是淡然与从容。“人们真正记住一个作家,不是因为他(她)得过什么奖项,而是因为他(她)塑造的人物。真正的荣誉不在奖项中,而在读者对你作品的熟知和喜爱上。”
短篇小说就如同是一个个生活中的小片段回放,在这些片段中,有生活中的辛酸,也有满足的一面,能看到它们都来自于生活的细枝末节,一个作家要想走进生活难,要想走进笔下人物的内心更难。在二十多年来的短篇之路上,迟子建又该如何去揣测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呢?她把人生比喻成了一条长河,“人生是条长河,世界上没有一条长河是笔直的,总要有这样那样的曲折。没有曲折的人生,也就失去意义了。一个作家进入小说,尤其是塑造笔下的人物时,要细心揣摩人物的性格。人物性格多重多样,那么作家在勾勒他们的形影时,就要用不同的笔墨。如果能在生活中认知形形色色的人,认知善人,也认知恶人,无疑对塑造人物有好处。至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那就是人生的滋味啊!”
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生活做一次规划,那么,迟子建对自己创作之路的规划怎么样的?在她的答案中,看得到一个用心写作的人,将它看的如同生命重要:“我想一个作家年事已高的时候,仍有创造力,像托尔斯泰和雨果那样,是最幸福的。因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结束了,生命可能就变得虚空了。所以,我不给自己设置写作的终点,因为写作跟我的生命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