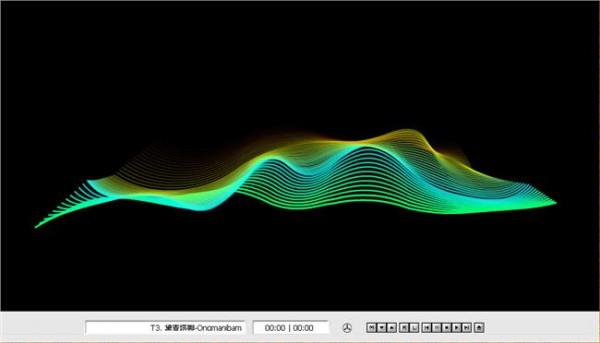张全胜和黛青塔娜 黛青塔娜:唤醒与天地和好的初心
9月9日,HAYA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他们独特的以蒙古音乐为基础的世界音乐,将再一次为北京的上空带来能够纵深于心灵探索与艺术表现之间的音乐图景。世界音乐的含义为融合,跨界。HAYA的音乐,将蒙古马头琴、长调、呼麦、萨满舞、非洲打击、印度鼓,与印第安笛等等这些世界各地最神秘、最美妙的声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主唱黛青塔娜,回归自然天性的歌唱,曾被誉为晦暗城市中的一盏明灯,穿越悲喜的迷雾。
9月初,我们有幸在中央民族大学HAYA的排演室采访了黛青塔娜。她清淡脱俗,谦和平静,很难想象这样白皙文弱的女子竟能在舞台上发出那么强大的气场,震撼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灵。她从容安静的外表下,会冷不丁冒出一股顽皮,偶尔又直率精辟地针砭,迅速拉近了我们与音乐的距离。
《投资者报》:为什么给乐团取名为HAYA?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黛青塔娜:为乐团取名时并没跟家人说,当我告诉父亲时,他非常惊讶!在他小时候,牧民在草原上迁徙会路过一个叫HAYA的地方,那是一个气候异常多变的地段。HAYA是蒙古语,意思是“世界的边缘”。我们也是取这个“边缘”的意思,“边缘”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天高地远,更接近自然。“边缘”相对“主流”具有无限伸展的可能。
目前,少数民族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变着,非常质朴的价值观、世界观被边缘化,渐渐被遗忘。但往往是这些没有被现代文明彻底浸染的民族,蕴藏着更多如何与天地自然相处的智慧。可是现在矿山、旅游点太多,争名夺利的事情充斥了这个世界,这些智慧被掩埋了。
第一次去草原的人们往往被直接带到旅游景点,看到被杀死的动物做成了标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听到的也不是真正的草原音乐与歌曲,让他们误解了游牧民族、游牧文化。这里面没有无辜者,每一个蒙古人、藏族人自己都是参与者。因为当金钱冲进来的时候,比沙漠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家园从我们内心开始瓦解。
HAYA乐团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我们不希望闭着眼睛歌唱我们的家乡有多么美好,我们希望听者在音乐中从内心照见自己,因为我们在城市时间久了,忘记了自己是谁,心已经沉睡了,已经失去了和天地沟通的能力。只有当你与大自然相对,才能意识到“我们是那么渺小。
《投资者报》:你出生在青海湖边的德令哈,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父母是什么样的?那时候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黛青塔娜:德令哈是蒙语,是蒙世界”的意思,我从小循规蹈矩地上学,接受“汉语”的教育。父亲是牧民的孩子,他的家乡格尔木与西藏接壤,那里非常偏僻,小时候上学要走好几天的路,后来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母亲也是牧民的孩子,后来是民族乐团的民歌手。
她从小生活在蒙藏混居的地区,她的民歌很多与藏族相似,有的甚至我们一唱出来,藏民们会唱出相同旋律的藏文。我的外祖父有可能是藏族人,小时候是他的养父母从拉萨抱回来的。
母亲也有俄罗斯血统,也许是基因的原因,我从小对蒙古族、藏族有天然的亲近。我没有兄弟姐妹,从小在乐团的环境中长大,最大的爱好就是幻想,曾幻想怎样做一个翅膀飞起来。或许因为太熟悉了,小时候不太喜欢听母亲唱歌,反而更喜欢西方的音乐。
如果说我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16岁之前我都特别疲惫,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被梦困扰,噩梦很多。母亲经常带我到寺庙中给这个仁波切看看,给那个仁波切看看,有的仁波切说我丢了一个魂魄,妈妈请他们给我念经。现在佛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遇到问题之后的救命稻草,而在我的成长中,就像妈妈的歌对我再自然不过了。
与此同时,我的性格又非常张扬,凡有演出我肯定是第一人,凭着天生的原始自信,无比的开心。我曾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也不在乎能考多少分,自顾自地叛逆地活着。
《投资者报》:在大学时是什么专业?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
黛青塔娜:我16岁来到北京,在民族大学学习声乐,从非常自在的状态跌入谷底,开始迷失,我开始认知自己,开始长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系统,我的叛逆让我在很长时间内完全不会唱歌了。环境变了、价值观变了,周围人唱歌的方式都是跟自然或跟自己的内心没有关系的。那时候,我反而更欣赏地下通道里唱歌的歌手。结业答辩时谈大学四年的感受,我说,人是必须用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去感受音乐去唱歌的,歌声对我来说,不管是地下通道里的歌者还是高贵的音乐厅里的歌唱家,只要用心和灵魂来唱歌都是感人的,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老师却说:你太狂妄了,我歌唱了一辈子,也不敢说我在用灵魂演唱,你的文章必需重写。我就在想,一个以歌唱为生命的人,都没有资格谈用灵魂来演唱,那么歌唱是什么?是实现某些任务的手段和工具吗?
毕业以后,我知道自己决不会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因为从小在歌舞团长大,我太熟悉那样的环境。只要我可以用歌声赚取生活的费用就好了,直到2006~2007年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方向。
其实,在德令哈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外国人做的“世界音乐”,那时虽然没有“世界音乐”的概念,只能找到非常有限的作品,但我有一种本能,知道那里面既有民族的东西,又不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它能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
可母亲和周围的人都说这样的东西离你太远了。的确,虽然喜欢,但我够不着,因为周围没有这样的土壤,没有可以跟我共鸣的人。直到上了大学,遇到全胜老师,我从仰望他,到开始交流。我才意识到小时候喜欢那种音乐是原因,后来就遇到这个人,这个人也喜欢“世界音乐”
全胜老师教马头琴,他告诉我怎样歌唱,告诉我如何让内心安静下来,如何倾听自己的声音,如何相信自己……他一点点唤醒我的自信。让我终于找到自己声音的,是我跟他录制《HAYA的传说》,那天,我一个已经不敢开口唱歌的人,即兴地玩声音并录了下来,全胜老师说:原来我找了那么久的声音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那个阶段,我在HAYA乐队中写一些自己的东西,沉浸在自己喜欢的音乐中,至于能否在其中歌唱都是无所谓的,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开口唱。现在想来是很厚的感觉,是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探索过来的。
《投资者报》:是否一个民族的音乐更适合本民族的语言?怎样突破语言与族群的界限?
黛青塔娜:我们生下来就开始接受逻辑的训练,任何事情都要去分析,必须有语言的参照才有安全感。但是音乐需要丢掉常识,如果不是仅仅为了娱乐、仅仅为了忘记痛苦而暂时分散注意力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语言的参照,才可以打开内心的世界。好的音乐可以唤醒直觉,而直觉可以指引我们接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蒙古民歌一定要用蒙语演唱才美,汉语古诗词与古琴相配。不可言说的语言之美无法翻译,蒙语每句都像诗一样,但它带局限性的美只能在自己的族群中分享。但原生态的东西是缺乏生命力的,就像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凝固在那里。如何让民歌像河水自然流淌,像花一样继续开放,这是最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要做人性共通的东西,做这个地球上所有人都能感知的东西,如果我们的音乐具有了这样的品质,就能超越语言。
如果我们放下界限,从心灵出发,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是接受常规的教育,只是循规蹈矩地生活并乐在其中的话,可能只用了百分之一的能力,剩下的都在睡觉。在HAYA乐团的成长中我感受到,很多能力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生命不是遗忘的过程,而是恢复记忆与能量的过程。不是向外索取的,一定要收回来看自己,这个很奇妙。其实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就像生活习惯、民族语言,只要有向往,它们在基因的作用下会慢慢醒过来。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直沉睡的人,有半梦半醒的人,有醒过来的人,我可能在半梦半醒到醒过来的路上吧。
《投资者报》:Ongmanibamai可否看成是你踏上音乐创作旅程的第一步?能否讲讲那次创作经历?
黛青塔娜:这首最初是听一位藏族姐姐唱的高高的山歌,特别好听,我把她录下来,但怎么模仿都觉得她不属于我,只能先搁置下来。那时,我已毕业,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有一天梦见一个声音,那是我不曾发出的声音,那声音美极了,就在唱这首歌,和我听到的别人唱的都不同。
马上醒过来,就在吉他上定了调。接下来几天就在家里用全胜老师给我的简单录音设备,一个人对着麦克听着耳机一遍遍地录,直到最后我知道应该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拿给全胜老师。也是个晚上,他制作完成后一个人在路上听,流泪了,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被你感动。
很多音乐人都会从梦里获得灵感,平时的创作永远不会达到梦中的美。我有多少美妙的音乐被遗忘在梦里面,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遗憾和迫切,我才学会了在梦中记录,有多少次我都是唱着醒来的,为了更快地记录,我有一套特殊的密码谱,只有自己看得懂。
《投资者报》:在与全胜老师的合作中,你们是怎样将蒙古音乐中最精彩的部分(马头琴)与现代先锋音乐交融,创造出全新的音乐?
黛青塔娜:马头琴先是一个乐器,其次才是民族的乐器,当乐器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跟其他任何音乐的融合都是有可能的。但要有一个科学的和声,才可能更美。比如说马头琴是旋律型的乐器,音色是线型的,就需要一个合声,颗粒的音色,我们有吉他、贝斯、钢琴,还有鼓。
因为蒙古音乐的优势在于旋律,劣势在于节奏,节奏特别厉害的是中东、印度、非洲等地区的音乐,我们就把他们引进来弥补蒙古音乐中的弱点。我们研究怎样把音乐变成一个美好的有机体,并完全在脑海中去实现他。
《投资者报》:在录制《寂静的天空》时HAYA的创作是什么样的状态?从《寂静的天空》到《迁徙》又有哪些改变?
黛青塔娜:《寂静的天空》在制作时,乐队都要分崩离析了,2005~2006年,乐团刚刚走上世界音乐的创作之路,我们颠覆了人们的听觉习惯。那时真的很难,没人理解,没有舞台。大家各自谋生,就剩下全胜老师和我,希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过来弹琴。
HAYA乐团只剩下一个名字和我们两个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异常安静,有一天在操场散步,忽然就出离了。我们决定录一张安静的音乐,把那些花哨的东西都扔掉。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因为你要面对内心本质的东西。
《寂静的天空》是我在家里自己录制的,因为没有隔音设备,虽然声音不大,但有时候也会有跺脚的声音,那一段就算作废了,再从新录。在台湾出售30000张之后,很多寺院、灵修中心、SPA馆,包括中山纪念堂都在放我们的音乐,这是在完全没有宣传的条件下达成的。我们去灵柩山,发现放的也是我们的音乐,一个卧佛在云雾缭绕中听我们的音乐,这是很棒的感觉!
台湾蜂巢唱片希望继续代理我们的唱片,他们希望我们继续出类似的所谓“疗愈”的东西。我们于是开始思考什么是“疗愈”的什么是灵修,什么是瑜珈……既然是疗愈,希望修复提升自己的灵性与感知,对自己的精神有要求了,那就不能欺骗自己,就不可以沉寂执着在某种舒服的状态而无法自拔。
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现实是草原已经不再是我们歌声中的草原了,现代生活在让牧民变成农民,农民变成城里人,我们的草原在消失,游牧在消失。
这就是《迁徙》的缘起,大草原是大自然可以呼吸再生的关键,如果人还可以跟草原接触的话就必需游牧,牛羊只会让草水更加丰美。我们的内心也必须经历一次迁徙,我们必须认知我们的内心有无数面向,我们都要去认知,而不是只有平静是好的,不能愤怒。
有的音乐会就是要大家闭上眼睛,现场必须安静,我们就是要摆脱这样的概念,希望来现场的人可以感受到安静,能感受到愉悦,也能感受到愤怒,能感受到人性,能感受到坐在舞台上的那个人和坐在舞台下的自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当人们离开音乐厅的时候会带着自己的思考,也可能会意识到原来自己离自然已经很远了,而不是又一次被催眠。
当《迁徙》与唱片公司见面的时候,他们对音乐甚至封面都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觉得太粗犷了。大陆版的封面是朝戈老师1989年创作的油画,大草原上的一个裸女。她与性别无关,是一个人完全揭开所有的掩饰,以她内心的能量拥抱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拥抱她,她勇敢地站在那里,不怕把自己的任何一面暴露给世人。我特别喜欢它的大气,有点像六七十年代摇滚音乐的封面,很复古很有力量。而台湾版的封面是一只蝴蝶落在我的手指上。
《投资者报》:最近HAYA乐队在国内音乐界的影响如何?
黛青塔娜:除了参加国外音乐节,去年我们第一次跟国家文化部门出国演出,徐沛东老师带队。开始他只邀请了全胜老师一个人去拉马头琴,但是全胜老师不遗余力地推荐乐队,徐沛东老师很没有把握地答应了。我们只去了四个人,第一场用了一些小的扩声设备,效果特别好,非常轰动。
结果第二场就不准用了,因为别人没有用就显得效果不好。不让用麦克,但效果仍然很好。这样巡演了一圈之后,有一天,徐沛东老师在大巴上很有感触地说:大家需要开个会,这次演出给我感触很深,我们的民乐太老了,我们在国家的体制里无忧无虑地搞创作,但在舞台上已经忘了交流这件事情,真的需要一次更新。
我要向HAYA乐队致敬,他们虽然只有4个人,但这4个人在舞台上会跟2000名观众交流。他们每个人的状态都展现了他们的自信。
我们非常受鼓舞。不论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音乐最需要的是平台。因为音乐不会撒谎,有什么样的心智就有什么样的声音,语言可能会掩饰,但只要开口唱,就无法掩饰。也因此我们感到非常自信,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是非常真诚地去做的。
《投资者报》:目前的生活与创作状态如何?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黛青塔娜:我感到很幸运,但这辈子一定要珍惜。有时候我会观察自己,天哪!我的灵魂都经过了哪里,走了多久才来到这个身体里住下来,跟我一起经历这一生,完全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一辈子能找到可以抛弃一切而投入其中的最挚爱的事情,就能找到,灵魂的印记会印在我们挚爱的事情、挚爱的人、挚爱的梦想里面,也许就是这些零星的片段,被拼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是我每天最爱的思考,停不下来,太有趣了。
目前HAYA音乐比较全面,现场演出也非常好看。平时,可以在民族大学全胜老师的录音棚排练,我们很感恩!我自己也在享受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乐团里,我们经常提醒彼此: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最高点,还有一段非常享受的生长阶段。一旦完全成熟了,像垂下头来的麦穗,就要开始新的轮回了。
今年底,我们要发行纪念HAYA五周年的蓝光DVD,我们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庆祝。
明年,我们希望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