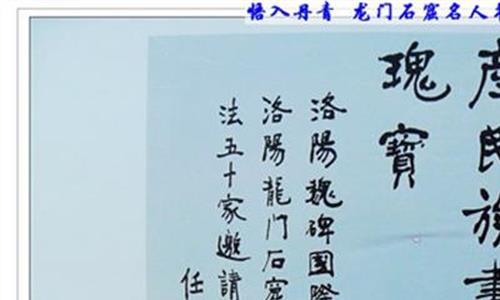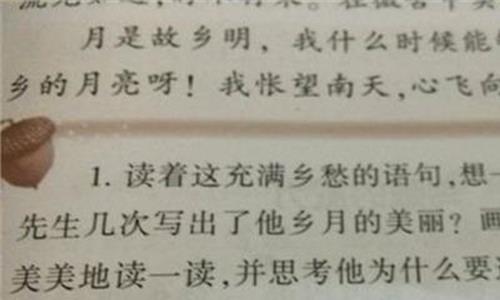季羡林与任继愈 季羡林、任继愈:那个时代培养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总归是静水深流的。季羡林、任继愈,就是这样的大师,他们都是真正有思想的人,我们很多人都会怀念他们。
徐迅雷
98岁的季老季羡林、93岁任老任继愈,在2009年7月11日同一天辞世。
“人生不满百”,一语成谶。季羡林先生尽管久居医院,但对高寿者来说,他的身体算是较好的,精神状态更是不错。逝世的头一天他还在挥毫题字,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等,是因心脏病突发,突然离开人世的。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路坎坷起伏,而他的人生之境丰富多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季先生留给公众的,更多的不是沉重的记忆而是诸多的美谈。最典型的当属“副校长季羡林为新生看行李”。毕业于北大的名记唐师曾,称季羡林先生为老师,他的描述最生动:整整20年前,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学兄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
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
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学兄对老者千恩万谢……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学兄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学兄再次差点晕过去。
人品学品俱佳,思才文才双馨。网友悼诗说:“季节变换人无常,羡慕大师学识庞。林中顿减千秋树,世界都在喊彷徨!”季羡林先生精通12种语言,其中包括偏僻得很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尽管他在《病榻杂记》中一辞“国学大师”,二辞“泰斗”、三辞“国宝”,但资深教授的名头是辞不了的,还有一串“家”的头衔: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任继愈先生的名头没有这么多,但这几个也是分量沉甸甸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前馆长、现名誉馆长。一国之“国家图书馆”,得是一个国家的饱学之士,方能出任馆长。解放前,梁启超、蔡元培都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也只能是派上一个副馆长当当。这有点像担任国家大辞书《辞海》的主编,得有真才实学真水平,而不是你官儿大去挂个主编的名就受到公众承认的。
任继愈先生在生前非常勤奋,多年以来坚持每日凌晨4点钟就起床工作,住院治疗前还在编纂《中华大典》,以及续编《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的编纂已完成了一多半。此外还有“佛教思想史”和“哲学史”等著作的编纂工作还未完成。
任先生为人处世低调,不图虚名,宁愿多做实际工作。他生前交代过几件事:第一,不出全集;第二,不过生日;第三,过世后不用进行很隆重的告别式。之所以不愿做这几件事,是因为任继愈认为,人做这些事就会让别人说违心的话,比如过生日时,别人会说“长命百岁”,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长命百岁不可能”,这与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言的“人生不满百”,多么相似!这才是人生真正的通透与洒脱。
低调的任继愈先生,不像季老那样有大量的通俗篇章问世。季羡林正是因为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化的文章,为公众所熟悉的。尤其可贵的是一本《牛棚杂忆》,是反思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与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样,具有不一般的思想性与深刻性。
著名杂文家邵燕祥先生说:“季羡林先生从文革以后,就一直很坚定地反思文革,他的《牛棚杂忆》,由于比较直率地写出了文革的遭遇和他的心路历程,最真实,最生动的就是他讲自己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当他准备到校园北面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遇上学校暴徒来敲门。
这改变了他的计划和命运。他得出的结论非常好:对恶人不要软弱。暴徒的到场反倒使他抗拒暴力,维护自己宝贵的生命。试想,他在1968、1969年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无从写出那么多的学术专著并做那么多的贡献了。”
季羡林先生有句广为传播的名言:“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我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的扉页上,手写了这一名句赠予朋友。“真话不全讲”,就是一句老老实实的真话。作家张承志说得没错:“中国现在是散文时代、杂文时代,读者更愿意看到的是真心话。”在我看来,纯粹意义的真话是真理性的话;而“真实的话”≠“真话”。
在著名的强国论坛,见到一个帖子,那是一句真话,很让我感慨:“那个时代,为啥出了这么多大师,而‘新中国’成立后,居然一个也没培养出来呢?”这个问话,确是真话,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60年来确实没能培养出一个真正大师,你急死也没用。季羡林、任继愈,都是那个遥远的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大师。你想一想罢,真正可以称为大师的人士,可以说无一例外都是在那个遥远时代完成“而立”的。哪个领域、哪个行当不是这样?
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从山东官庄一个农民家庭中走出,读私塾,读小学,9岁时就开始学习英语,12岁读中学,15岁初中毕业后读高中,开始学习德语。1930年19岁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为德文,1934年23岁清华大学毕业。
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41年30岁从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10年后,在1946年,在他35岁时,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的受教育、完成学业锤炼,是在上世纪前半叶。
同是山东人的任继愈,1916年生人,比季羡林先生小了5岁。任继愈所读的高中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时,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于1938年。那时抗日烽烟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入云南。
任继愈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西南联大,空前绝后,人才辈出,有口皆碑。任继愈尽管没有季羡林那样的出洋留学,但他的学问同样做得深入扎实。“三十而立”,他们在那个时代完成了品格与学识的“而立”,由此才有后来的“不惑”,才有后来在学问上的“随心所欲”。
那个时代,纵有千般乱,可学人的心境不乱;那个时代,纵有万般恶,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恶。蔡元培曾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季羡林、任继愈,就是那个时代馈赠给我们现在这个“未来”的大师级人物。
没有好的教育,不可能产出真正的大师。看看其中的教育公平,可谓今非昔比。譬如,那个时候的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是全国招生的,山东人任继愈这样才能去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高中学生真正的北京青年不多,外省的倒很多。哪里像今天的一些名牌大学,坐落在某地区,几乎就变成某地区的高校,超大量招收本地区的学生,教育公平无从谈起。
与那教育体制相比,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教育理念,洋溢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的教育,先是学习苏联模式,那是被“计划”的教育、被“统一”的教育;再后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应试教育,大家都被模式化、格式化的教育教育成了火柴盒里一模一样的火柴。
这样的教育会培育得出大师吗?这样的教育能培育得出诺贝尔奖得主吗?事实已经清楚地说明与证明了一切,只是那些不愿意听真话、见实情的人,依然陶醉在美好的自我感觉里而已。
如今这个没有大师的时候,称为“大师”的人可以满地走。但与季羡林、任继愈这样的老大师相比,“新大师”们可是大不一样,写点文章暴得大名之后,就到处抛头露面,凭借不错的脸蛋与流利的口才“通吃天下”,尽管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问世,那也不要紧,老本够吃一辈子的了。何况这是没有真正大师的时代,顶个“大师”名头就可以招摇天下。
可是,真正的大师,总归是静水深流的。季羡林、任继愈,就是这样的大师,他们都是真正有思想的人,我们很多人都会怀念他们。而对那些新的、轻浮的、飘然的、所谓的大师,我们除了鄙视,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