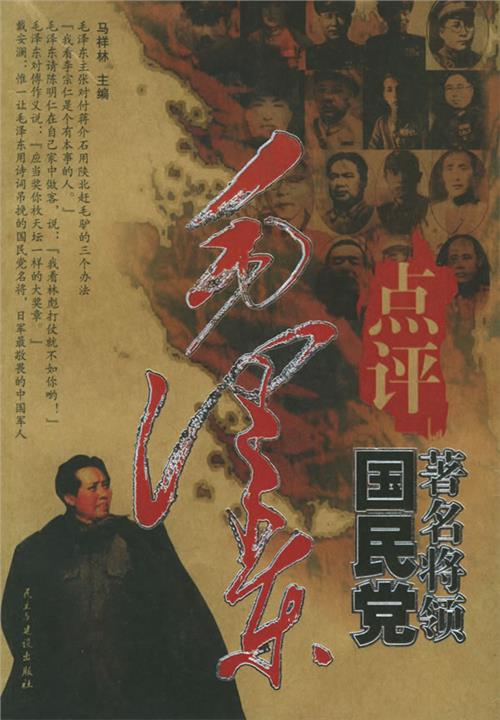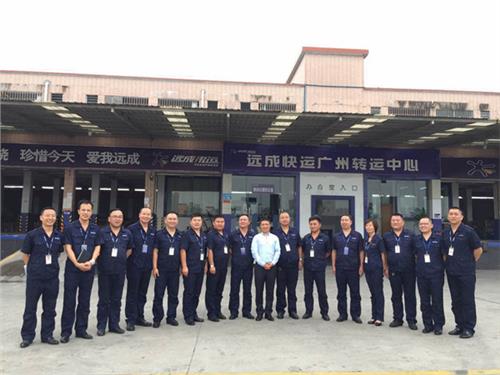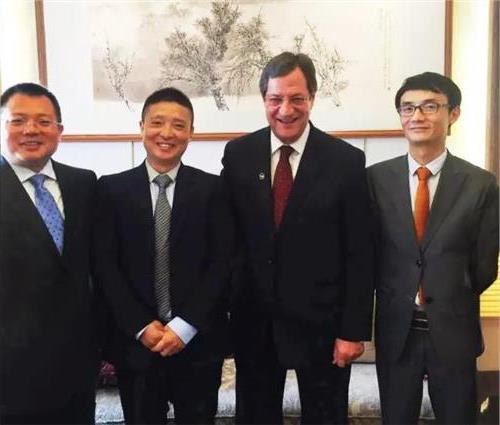黄声远幼儿园 黄声远:田园给予我们生命中的本真
黄声远领导的设计团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田中央工作群,这正是他们工作状态和生活环境的生动描绘。其事务所坐落于田地的中央,"我们刚刚在宜兰工作的时候,经常就坐在稻田旁边讨论和开会。"黄声远这样描述,"熟悉这里的环境很重要。我认为要做好一个地方的建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扎根在当地。"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扎根在宜兰的设计团队。
黄声远的家到事务所只需十分钟的路程,田中央工作群一般只有车程在半小时内的工作。这样,他们可以随时赶到现场与当地使用者讨论,随时发现不妥就修改。工作起来严谨而自在,经常的装扮是一顶斗笠、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一双拖鞋,放弃了外形的束缚,工作更显方便自在,在施工时很多设施都鼓励年轻人亲力亲为。
提到田中央工作群的生活状态,黄声远介绍道:"大自然可以教给我们更多。我们工作室中午饭后会自己处理食物残渣,我们乐于做些农事,比如尝试过收割稻子。在水灾后年轻的同事主动积极支持,做些专业规划,同时学会了解水。"
提到理想中的城市,黄声远这样表述,"应该有足够的留白,能让每个人过自己的生活。一个地方的幸福应该是大合唱。路要窄一点,人才会相遇;灯要暗一点,鸟才可以歇息。自由,是最窝心的生活质量,相互支持、体谅。原来,田园早已跟在这群年轻人身边"。
他希望城市回到"原来"——"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小孩可以安全地骑脚踏车,进出政府机构像出入自家后院一样方便。发生过的故事,在以后都可以找到痕迹。"
建筑的友善提供人和自然的伊甸园
黄声远在美国期间曾供职于洛杉矶一家名为Eric O`Moss的建筑事务所,经历过专心的生活在一个小区域中,然而在去美国之前,也像很多年少有为的高材生一样生活在台北大都市,并在办公室为远在台北以外的地方设计公共建筑。
但他很快便知道这并非自己的强项。"从内心里,我无法有冲劲持续这样为建筑而建筑的工作,我觉得建筑还有其他,最好不要只因为设计者常被限制的片面理解而太快地诠释周遭环境或居民的习性。如果它是一种陪伴多好,与环境谱出共鸣。"黄声远回忆,也开始四处去寻找新故乡。
这种谦卑的态度体现出了对人和自然的尊重。在黄声远看来,"农民往往比我们更懂得生命,大地中资源有限,人人都知道必须做出对的事情。比如修栈道时,当地居民建议将路修得比较窄,法令上容易解释,不会有人占用,也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打招呼。路灯不要那么亮,否则住在附近的水鸟会孵不出来。"
在宜兰一个别具一格的建筑要属户政事务所了。整栋楼灰灰绿绿、歪歪斜斜的,各层房顶上都长了树木,走廊的扶手好像是钢筋剩料的再利用。但是不能否认,这栋建筑的可爱和平易让人会心一笑。户政所主要负责管理户籍事务,这样的一个政府机构没有选择严整而庄重,而是接受并认同如此"自然、颓败"的建筑,也许本身就传达出某种开放的心态。
"做公共建筑的初衷,是营造一个谁都可以进出的空间。建筑师创造一个建筑不是为了否定日常生活的价值,不能让人进去后有挫折感,一下子变得缩手缩脚。
好的设计和好的环境,其实是不造成压力的。所以我们努力让环境很友善,钓鱼的人自在地靠坐。"黄声远这样解释田中央工作群设计的一个河边公厕。他在点点滴滴中践行着自己提出的让行政机构和城市建筑与人友善的理念。
津梅栈道
在2010年,以最高票数入围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并获奖的津梅栈桥同样充满亲切感。原来当地有一座水泥桥,来往的两条车道宽度够供机动车行驶,多年来行人过桥非常困难。后来,田中央工作群历经多年整合,最后提出了一座新的栈桥附挂在旧桥之下,刚好能够支撑不太宽的桥面栈板,最狭窄的地方,只能供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经过。
栈道的围栏种满了花草和藤蔓植物,在灯光和水汽的滋润下,植物不需要人养护,可以自由生长。桥的两侧靠近桥墩部位的地方,吊着几个秋千,孩子们在上面挥霍着童年,美的像一个遥远的梦,却又真实存在着。
黄声远表达着自己对建筑的想法:"多么希望整个环境没有歧视,甚至在生态上,对青蛙、虫、蛇都是无歧视的。"田中央工作群早期设计的竹林养护院充满了竹子,可以让老人晒到太阳,看到水圳,想办法让鸟停在二三层楼的露台上,另外又开辟出可以种菜的区域。提到温暖的圣嘉民启智中心,黄声远仍不无遗憾,照顾院童的老师和他一直希望庭院里可以养羊,但是劳动田园的意见到最后不敌总务部门弄成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干净的一般想法。
慢而自由的节奏诠释细腻的关怀
面对日益成为流水线机器大生产的建筑业,田中央工作群做建筑显得太慢了。建一间普通的住宅,其他人大概花一年,他们愿意花六年的时间不忘春夏秋冬。他这样解释:"一直怀疑效率这件事情是把多样化变成单一化,想以手工艺精神面对当代材料,培养一个因为慢所以多元,因为慢所以能了解的城市。
还好甲方了解后也认同,我可以慢慢把事情想清楚,慢慢修改。"而这样的架构一旦掌握住,黄声远的目标是,能够面对数十年的变化有能力调整,与时俱进。
在田中央工作群,他们并不把所做的建筑看成所谓的项目,而是将其视之为整体生活背景的铺陈活动。"项目是有工期,有限制,有始有终的。而环境的改造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就先停在那儿,暂停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别的事。其实在这里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紧迫,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压力,如果是对的事情多数总有一天会再动起来,这段多出来的时间一边修改方案,一边再找经费。
"而常常是在停工的阶段,找到了更完善的想法,在修改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挣扎,慢慢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愿意修改,才能真正面对机会。
最后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不完全是建筑师或事务所的作品,而是工匠、村民、业主所有人的安慰。他相信绝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不会特别顺利,也不会真的失败。要的就是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一直不放弃。宜兰火车站到2012年止已经花了八年多时间,黄声远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按照多数公众而非少数人的想法,慢慢照顾一个环境成长,让它趋于完善。而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建筑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
黄声远对于建筑中的无障碍设施格外关注,"建筑物的无障碍精神可以是一种美,是价值观的呈现。如果我们觉得对任何人都接纳的感受是美的,那无障碍的设计就是指向美。我们期许自己一定要做,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付诸行动。
一些体贴,其实不难,但是要愿意付出。除了关注建筑物本体,在建筑物与户外空间之间,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可以更友善,至少要做到有障碍者在有人陪同下,可以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做到无人陪同时也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更是努力的方向。"
在一次台北关渡讲座中他谈到圣嘉民启智中心(残疾人收容院)时,黄声远对各种细节的关注令听者动容——"教室之间的墙壁都在特别的位置打洞。可以互相看到互相支持,想办法使有限的人力发挥最大作用。
另外,老师也要去上厕所,短时间内可能有孩子关照不到,启智中心的建筑设计虽需要尽量无时无刻感觉到彼此,但是我又希望人人有尊严不要被监视,很复杂。我们都希望启智中心的学生不会永远都待在里面,不要保护过度,所以水龙头的开关把手设计就有各式各样的,所有的台面高度也都有不同姿势的考虑,要给他们非常多样的环境条件,多练习,以后才有机会顺利地回到这个社会。
后来因为我自己有了小孩,一天到晚都需要照顾孩子,自然体会过哪里需要平整。
所有的空间都要像自己家一样小心翼翼地处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受伤,如果手指受伤了,就可能没办法转开喇叭锁,所以会选择装设用手臂就可以压开的水平门把。无障碍这件事情不能只是符合法规,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要去体贴。"
有一句话至今萦绕在记者的脑海中,"培养房子不是被谁所有,是由地方上长出来的,有生命的存在。房子和人同样要被尊重,在建造中享受生活慢下来的脚步,是美好城市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