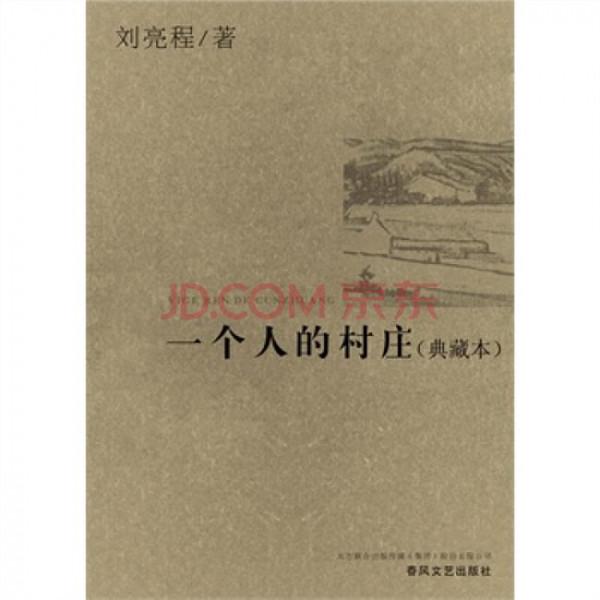刘亮程我的树 刘亮程:走在人群里 我是一个区分不出民族的人
我去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在新疆》。在新疆生活跟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外地人来说,新疆是一个在远处的生活,但对新疆人的生活来说,现实近在眼前,无所谓远近。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任何地方生活都一样,一个作家不需要有那么大的一块地域,那么悠久的厚重的文化来成就自己的文学,那样太浪费了,即使完成一部传世之作,也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人文资源。
在一个小地方生活很多年,思考很多年,独自想一些事情,感悟一些道理,完成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使命就此完成了。
我是新疆人,我在新疆出生、长大,这么多年未曾离开。新疆是我的家乡,家乡无传奇。对外地人来说那些遥远的新疆传奇事物,对我来说都很平常,我没有在我的家乡看到外地人想象的那个新疆,那个被遥远化、被魔幻化的新疆。至少我个人的生活,我认为是平常的,我从来没有书写过新疆的传奇。我从来没有猎奇过新疆,因为新疆的一切事物都是平常的,我看着它们生活了半个世纪,在我眼中这就是一个我生活的新疆。
如果说新疆有什么特别的话,我觉得它最大的特别之处就是让我长成了这样,而没有长成那样。它赋予我这种新疆人的长相,我是一个汉族人,我这种长相大家看上去觉得会很怪,像“胡人”。我在自治区文联上班时,经常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或者蒙古族朋友推开办公室的门,用他们的语言跟我打问一个人,或者说一件事,我知道他们把我当成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或者蒙古族了,确实在我的长相上聚集了新疆各民族的特征。
早年我留点小胡子,到街上,人家都跟我用维吾尔语说话。
后来我把胡子剃了,好多蒙古族人认为我是蒙古族人。你看我长得既像维吾尔族人,又像哈萨克族人,还有点像蒙古族人,回族人也有点像,所以我走在新疆的人群里,就是一个区分不出民族的人。
新疆这样造就了我,它可能确实很特别,它怎么能把一个人造就成这样呢?确实,它有它内在的特别的东西。也许是新疆的干燥气候,它的这种遥远的地理环境使我有了一种看东西的眼神。新疆人的眼神,看东西跟内地人不一样,我们的汉史中有“胡窥中原”这个词,胡人老是窥视中原。
新疆人的眼神就是“胡窥中原”的眼神,当然望得有点远了。这种眼神确实跟新疆那种遥远的地理环境有关,一眼望不到边,太阳直射下来,你的眉毛必须朝下沉,你的眼睛也要朝里凹,久而久之你的眼窝就深进去了,眼球就朝里面长了,你就变成这样看人的一种眼神了。这是新疆与其他地方的区别之处,它让我长成了一个新疆人。
我曾经倡议,我们的汉语读者要多关注一下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我们不要把眼睛只盯在欧美、拉美那些国家的文学上。其实在新疆肯定有同样的有价值的文学,它们被翻译成了汉语,它是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文学,是另一种语言的另一种思维,我们需要关注。
不妨读点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我一直在读,只要是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我都读,我生活在新疆,用汉语写作,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作家他们用维吾尔语、用哈萨克语、用蒙古语在写作。
写作本身是一种秘密。我们需要知道别人的心灵秘密,我们需要知道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着同一种生活的作家们在想什么。当我用我的一本书呈现出我的新疆生活的时候,我非常希望知道阿拉提·阿斯木(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用维吾尔语呈现了怎么样的一种新疆生活?
当我写到有关新疆的一个事件、一段生活的时候,维吾尔语是怎样表达它们的?我们需要相互倾听,相互看见,这几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每一种语言都在表述同一个地方,但是表述的肯定千差万别。所以写作的秘密真的是这样,作家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通过文学来显露心灵秘密的职业,通过文学来沟通。我在新疆也谈过,假如汉语人群和维吾尔语人群都不相互阅读了,那么这将是一种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