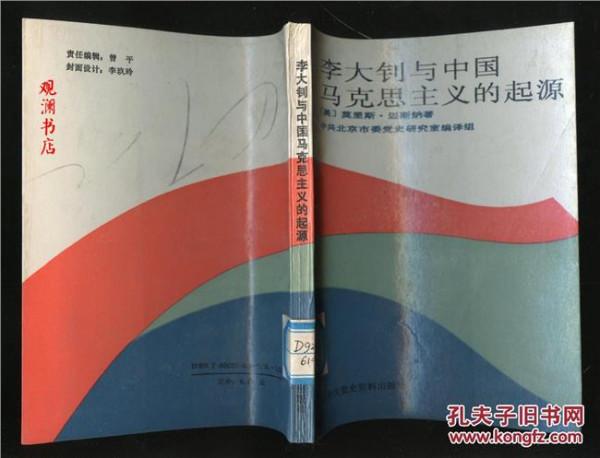李星华的简介 李大钊的后人李星华 网友lxpii:罗学蓬:李大钊身边的一对红色恋人
公元1927年4月28日下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时刻。
北平,京师第一监狱内,高墙环绕,军警林立,黑云如帐,悲风呼啸。随着一串叮叮当当的铁镣曳地声,以李大钊为首的20名革命志士,大义凛然地登上了耸立在监狱内的绞刑架,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在这一批殉难的烈士里,有一位来自四川省江津县的年轻人,叫谭祖尧。
1922年,刚满19岁的谭祖尧考入了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西画系,第一次离开巴山蜀水,来到了繁华的京都。
二十年代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压榨剥削,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谭祖尧到北平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并很快在斗争中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李大钊先生的器重。1923年,谭祖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李大钊手下的一员干将。
当时,李大钊先生既是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北方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则身兼两处秘书,直接在李大钊领导之下工作。这时,陈独秀创办的以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巳经停刊,谭祖尧便创建了“新军社”,并创办了《新军杂志》,为团结北平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人誉《新军杂志》为《新青年》之再现。
年轻英俊,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并具有出色的组织与宣传能力的谭祖尧,也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著名领袖人物。一次,艺专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与几位西画系的同学前去观看。蓦地,一幅笔法细腻的工笔画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在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位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
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旁芭蕉立,
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不仅对诗画颇为欣赏,此画的作者李婉玉,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原来,这李婉玉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谭祖尧知道她文章犀利,文风泼辣,却未料到她的诗画也如此出色。两人虽系同校学生,但一个在西画系,一个在中画系,一直无缘认识。
谭祖尧观赏良久,对陪伴他的江津老乡、中画系同学朱近之感叹道:“真是诗画双绝,倘能画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此时正站在他身后,听见他这话,莞尔一笑,悄然离去。对这位出自艺专的风度翩翩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李婉玉早巳仰慕在心,如今得着这么一个好机会能与之结识,她自然不会放过。
佳人与才子的初次相识,颇有点罗漫蒂克的色彩。
几天过后,这位胆识过人的姑娘居然只身来到西画系,主动拜会谭祖尧。
这倒真让谭祖尧又惊又喜,出现在他眼前的李婉玉,布衣素衫,清丽脱俗,犹如一朵出水芙蓉,一株临风玉树。通过交谈,谭祖尧了解到李婉玉乃是一大家千金,其父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供职,她幼秉庭训,有很深的文学休养。李婉玉拿出一把精美的杭州折扇递给谭祖尧,大方地说道:“谭先生,我曾多次听过你的演讲,对你是久仰在心。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请你也在上面题一首诗吧。”
这分明有一点“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味道了。
好在谭祖尧也是个才思敏捷之人,他将折扇展开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画展上的条幅的内容一般无二。他起身去桌上提起毛笔,在砚台上润润笔尖,略一思忖,便挥毫写到:
休教年华付白头,
横刀跃马逞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
不为家愁为国仇。
谭诗紧步李诗之韵,然情志意趣,则远非李诗所能比。
“好一个不为家愁为国仇!李婉玉不禁失声赞道。“谭先生忧国忧民,志向高远,真是令我汗颜啦。”自此以后,谭祖尧与李婉玉往来就更为密切,在谭祖尧的帮助下,不久,李婉玉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她利用其家庭的有利条件做掩护,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员,成为谭祖尧亲密的战友和恋人。
决不离开李先生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展开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遂联合美、英、法、比等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时称“大沽口事件”。
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政府开门揖盗的这一霸道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热浩大的群众抗议大会。谭祖尧是这次大会重要的具体组织者之一。李婉玉也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场斗争。
会毕,数万群众拥往铁狮子胡同,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反对北洋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唆使鼓动下,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用大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砍杀。
激愤的群众(主要是学生)在谭祖尧等人的率领下,宁死不退,向铁门冲去。卫队开枪了,当场遭射杀而死的爱国学生有47人,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在北平读书的朱近之、吴平地、龚灿滨几位江津籍学生也都跟随谭祖尧参加了这场斗争。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迫下野,张作霖则在日本的支持下入据北平。
其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巳挥师北伐,下长沙,克武汉,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大军即将挥戈北上。而日本和张作霖则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的组织,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在大战爆发前坚决铲除之。
霎时,古都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共两党的组织连遭破坏,党员被捕被杀者众,生死关头,李大钊只得带领谭祖尧等三名得力助手,避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即使在这充满危险的日子里,他们仍然通过李婉玉和外界保持着联系,继续领导着外面的同志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
当时,谭祖尧如果愿意的话,他有两次机会可以逃避开这场斗争。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李婉玉的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火速让婉玉去东交民巷通知谭祖尧马上离开北平去广州,他巳用电话通知广州方面的朋友为谭祖尧暂谋一事为安身之处。
李婉玉也真地愿意他离开,并表示愿和他同赴广州。但谭祖尧却毫不犹豫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巳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
第二次则是谭祖尧的江津老乡、中学同学、时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从一位在《京报》任兼职记者的同学口中打听到张作霖要动手了的消息后,深夜冒险跑到东交民巷通风报信。龚灿滨在使馆楼上见着了谭祖尧,告诉他情况巳十分紧急,必须马上离开。
谭祖尧带上龚灿滨,一同来到李大钊单独住的苏联驻军营房,让龚灿滨直接把情况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听罢情况,问了一下消息来源,虽不太相信,但仍向龚灿滨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领馆区。
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进使领馆区抓人,他张作霖虽是东北的胡子出身,我看他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嘛,北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
谁知道,4月6日的半夜时分,张作霖悍然派出一千多名军警,封锁了东交民巷使领馆区,在苏联大使馆苏军营房内强行捕去了李大钊、同时又在使馆楼上捕去了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3人。躲藏在四川会馆的北师大学生、江津人、共产党员吴平地也同时被捕。其余在各大专院校被捕的爱国师生有五百多人。
事后证明,各国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消灭“异党”领袖,秘密与张作霖勾结,不惜暂时放弃一点特权,充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领馆区抓人。
在李大钊和谭祖尧等人被捕的同时,敌人还拥进李府,抓走了李婉玉和也为地下组织送过情报的妹妹李柔玉,把姐妹俩和李大钊的家人关押在草街子胡同的监狱里。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事后回忆到:
“下午约摸四、五点钟,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抓进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婉玉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受谭祖尧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她和祖尧同志感情很好,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去东交民巷劝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祖尧说什么也不肯丢下我父亲离开,……”李星华还回忆说,“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作斗争,连那几个女禁子都有点害怕她呢。
烈女殉情而亡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等20名志士殉难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购置两具棺木,两匹白绸,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另一位同时殉难的江津籍烈士吴平地的遗体,雇车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
李婉玉在母亲的陪同下,也赶到义地为谭祖尧送葬。
生前在江津县志办供职的龚灿滨老先生系笔者忘年交,曾对笔者回忆道:“当薄薄的棺木揭开时,只见两位烈士的颈子上各有一圈乌痕,谭祖尧胸前还有碗口大一团血斑,可能是死前遭受毒打所至。李婉玉目睹爱人惨死,奋身扑向遗体,跪伏棺前抚尸痛哭,直至昏劂。我赶紧雇了一辆黄包车,让她母亲送她回家。”
江津籍画家朱近之先生则在他为江津市委党史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写到:“我当时是和谭祖尧一起考入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他是西画系,我是中画系。祖尧是我老乡,婉玉是我同学,我们三人的感情非比寻常。我和婉玉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是受谭祖尧的影响。
祖尧自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后,不仅要里里外外联系组织工作,而且每次斗争无不亲自参加,战斗在第一线。诸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斗争’、‘三、一八惨案’……诸役,他都冲锋陷阵,非常勇敢,实为进步学生的楷模。
在‘三、一八惨案’中,他因救护李大钊先生而受伤,为此还被送进医院抢救。我回四川时,祖尧、婉玉和我相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话别。婉玉不仅诗书画皆佳,还擅弄琴。那天她抱琴而来,是准备送我登车后还要赶去城南参加一个琴会。
我怕误了她的琴会,坚持要婉玉先离去,祖尧一人送我就行了。我抱琴和祖尧送她登车,待她坐定后,我就跟她说:‘婉玉,我将于巴山蜀水间,敬待你和祖尧相伴归来。’她开心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祖尧牺牲以后,婉玉曾与我通了若干次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到:‘君以英杰之姿,年轻有为,而乃以爱恋革命甚于爱恋吾,甘赴危境,致罹于难。悔恨当时吾未能决然要求君与吾离开北平,同赴广州,而今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处?惟有抱恨终身,以泪洗面耳!’她那时真是悲痛到了极点。”
更为感人的是,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买来一把匕首藏在腰间,渴望杀死张作霖为祖尧和遇难的同志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座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巳经被冻死在雪地里。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谭祖尧和李婉玉虽早巳魂兮归去,但他们用生命演绎出的悲壮的爱情故事却会长留人间,让后来者认识到: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中,不仅有着众多大马金刀义薄云天的热血儿男,也有着缠绵悱恻风流潇洒的才子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