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比较法律文化 法律是如何发展——《比较法律文化》带来的启示
对于比较法的研究来说,除了说明各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的具体异同以外,大致还有两个命题是需要回答且无法绕过的,其一是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的法律呈现不同的面相,其二则是不同的法律是如何得到发展。
当然,这是两个宏大因而似乎永远只能是众说纷纭的问题。不过,当埃尔曼批评Holmes关于“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于立法,不在于法律科学,也不在于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的评论过于宽泛时,他已经试图另辟蹊径,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法律发展的力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移植和借鉴的可能性。
在埃尔曼看来,法律并非仅仅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其应被作为文化环境的一个子系统(Subsystem)来看待。这种强调重点的转变意义在于,不仅仅将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从作为制度的法转变为作为文化的法,而且扩大了比较法的研究范围。
埃尔曼确信,由于“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因此透过“包含着不同伦理观并运用那种可以产生不同法律后果的信条的其他法律文化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分辨不同社会中伦理规则、法律规范,以及社会控制的其他技术手段所处的位置”,而这样便可获得挂怒不同文化族群法律得以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密匙”。
二 法律如何发展
“法律是如何得以发展”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容易回答,且容易生出许多争论来。 不过大致分为分为理性建构论与历史进化论大概不会带来多少非议,其中前者的杰出代表便是英国的边沁(Bentham ,1748~1832),而后者的杰出代表则是德国的萨维尼(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1779~1861)。
在边沁看来,普遍的法律发展具有不受约束的力量,人类可以依靠理性对于自然法则的把握构建自己自己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其甚至建议除了作为批判之外,可以“完全不顾所有的先例而把英国法律全部重新写过。
”萨维尼强烈发对了这种观点,其认为,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和语言、风俗一样可以被视为在无限深厚的民族意识指引下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作为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今天的法律产生于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因此只能通过历史学来把握并使其得以维系和发展。
然而,在埃尔曼看来,边沁过于狂热的理想和萨维尼律谨慎地诉诸民族精神的做法都不足以说明法律文化演化的的真相,相对于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法律文化的发展远要复杂:一方面法律可以是理性建构,因而是可以进行法律移植的,因为当改革是由于物质的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时候,一群法律精英或者一个权力集团在分析、比较和借鉴地基础上从域外引进法律制度进行“移花接木”式可能取得完全或者部分的成功”,这时,新的立法所精心设计的冲击可以打破传统,使法律制度从一个族类走向另一个族类;而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相反的例证,在新的环境中,一项外国的设计常常被加以彻底地改变,结果与其意图相反,输入国的法律制度实质上继续依照其先前的传统发挥作用,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美丽的“外壳”而已。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社会国家力量的不断扩张。普通法系国家也愈加重视通过立法对于权利界定以及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在英国法这样的“判例法”母国,立法也已经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渊源。
然而对于“大规模法典编纂的迟疑、勉强的心理仍然没有被克服”,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制定了在数量上甚至并不逊色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典,但是“这些法典除了外观以外,并没有表达与欧洲法典同样的文化内涵” ,因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他们似乎既不适应也不乐意,当然也没有必要“必须转载法典之内寻找依据,相反,他可以并且也经常依据其他渊源。”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法律文化的积极和消极地影响。
于是,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本身的特性。即,尽管不同的法律制度相互借鉴和融合并非不可能之事,而且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现代各国法律制度中从未曾吸取外国经验或借鉴外国模式很少见;但是,由于文化本身顽强的内聚性,某些承袭了这种文化本身的因子却并会因为外来之物的吸收和借鉴便瞬间消失,它们与外来的制度以及观念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有时会在改头换面后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保留下来,有时则因为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而被抛弃。
因此,法律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单向和线性的,而是多向和复杂的,在法律趋同的背后存在趋异的潜流,在法律全球化的同时存在着法律民族主义的反叛,在现代主义的法律潮流中存在着法律原教旨主义的吁求。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法律文化融合”。
三 几个疑惑的问题
行文至此,却并不表明我也完全赞同此书的观点。似乎有点讽刺的是,尽管本文的写作几乎完全是围绕本书的第一章展开,然而对于什么是“法律文化”这样一个概念我仍然理不出头绪,而初读本书时,亦是困顿此。什么是埃尔曼先生界定的“法律文化”呢?它是指一种法律传统,还是某种法律观念?如果是这两者其中之一,那么它和它们又有什么区别或不同呢?如果不是,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从方法论上讲,“法律文化”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界定和解释——尽管埃尔曼并非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并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进行探讨,但是其试图从“政治文化”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法律文化”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其能够说明的仅仅是法律文化在“法律制度的执行者与运用者(以及受害者)的信念、情感与法律制度起作用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于此相关的问题是,尽管埃尔曼按照“法律文化族群”的标准将世界上的法律分为四大法系,然而,其并没有能够说明为何以此标准就只能分为四大法系,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这四大法律文化族群各自最为鲜明的特征又是什么呢?作者在序言中宣称本书始于这样一个假定,即“法律与政治是相互依赖的,要对二者有真切的理解”,但是除了第一章以外,我们似乎并不知晓,存有这样真切的理解对于本书到底有何意义?对于一本严谨的系统讨论法律文化的著作来说,不能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甚为遗憾。
四 多余的话?
自清末以降,伴随着中华法系的逐渐瓦解,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法律。期间大致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浪潮,其一是清末民初,其二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然而,在法律发展和法律移植领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似乎从来没有在中国“绝演”过。对此,我们似乎往往总是只能限于自嘲或者苦闷的自我批判,无奈却没有任何办法,以至于有学人开始追问“中国法学(以及其背后的中国法律)向何处去”的问题。
答案的寻找自然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过,埃尔曼的忠告或许是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即,在当下这样一个法律规则如同各种病毒一样潜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规则之网密而不漏,试图将人类的事务一网打尽的时代,尽管“中国的法律制度仍然是独特的。
但是这种独特性不再是由于象以往那样孤立地寻找解决其问题的乌托邦式方案所导致,而是因为他为了实现现代化、高效率和公正的全面目标而博采西方、日本的民法、苏联法律,以及中国传统法律等因素并将其融合为一体……今日世界,在国家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以来已经扩展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法律文化的这种融合似乎提供了成功的希望,虽然还不是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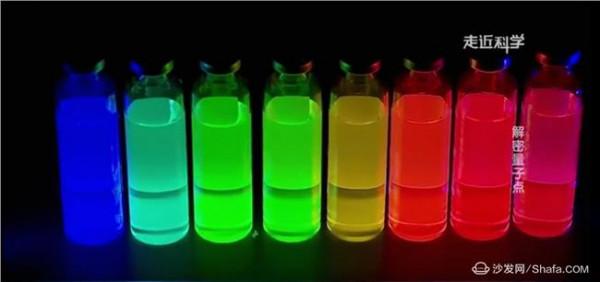



![清华高鸿钧 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https://pic.bilezu.com/upload/7/43/74321564f207431a4ea5823b8711099d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