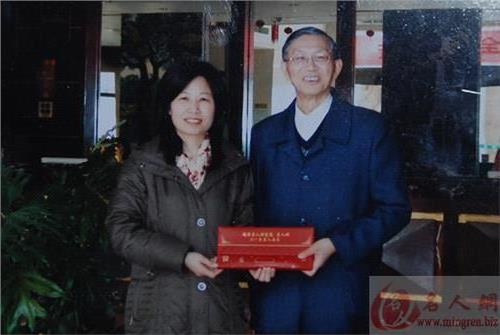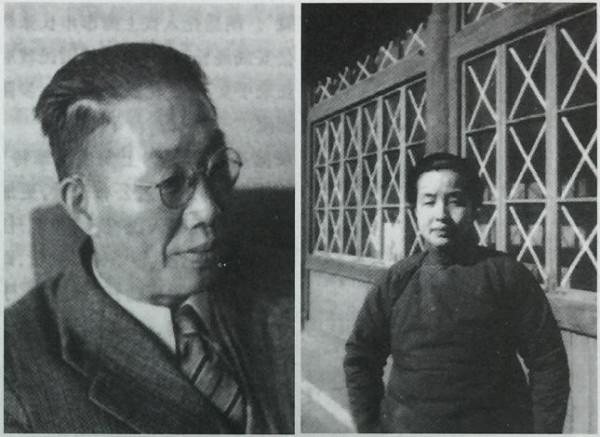【文人风流】罗隆基:永不疲倦(1)
1919年5月4日下午,时在清华大学就读的罗隆基知北京城里很多学生在游行示威,即邀王造时、何浩若进城了解情况,回来后号召大家:“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第二天,清华学子上街,罗隆基则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5月5日下午,罗隆基在西单街头演讲,逃脱了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的追捕,却在次日声援北大时被捕关进监狱。段祺瑞曾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说的江西三只虎,就是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后来,罗隆基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对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 “五四”之火的举动,李大钊赞誉为 “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清华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校友潘大逵说:“罗隆基是清华的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1922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是政治学。后转赴英留学伦敦经济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3年,罗隆基和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在成立国家主义团体“大江学会”。罗隆基在给清华同学的信中说:“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
1928年秋,罗隆基从英归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政治经济系主任,还主编《新月》月刊和《益世报》。
1930年11月4日下午,罗隆基被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之罪名逮捕,后来在胡适、蔡元培、张群活动下,于6个小时后被保释出来。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罗隆基好谈政治,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隆基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新月社在今日自然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一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1932年天初,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兼任天津《益世报》主笔,走马上任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局》,目标就直指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1932年1月26日,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两天,罗隆基发表了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从此以后,天津《益世报》的社论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发表了一系列的批评言论。一时间《益世报》销路大增。
但是罗隆基的社论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益世报》总编辑多次受到“警告”,要求报社与罗隆基解聘。1933年底,《益世报》被迫停刊,罗隆基终于失去了主笔之职。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蒋曾找人拉他做官,一种说法是让他当中华民国驻某国大使,另一种说法是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的任何部长都可以尽他挑选,但他都拒绝了。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1941年,罗隆基与张澜、陈伯钧、左舜生一起组建了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报纸戏称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的他为“罗隆斯基”,闻一多则被称为“闻一多夫”。
罗隆基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并成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他和章伯钧被划为头号大右派,称为“章罗联盟”。其实,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但他拒不承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在每次批判会上,他往往“舌战群雄”。于是,等待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
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志在会上热情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在座谈会上,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为1957年参加批判“章罗联盟”而说了一番向罗隆基先生冥灵致歉的话后,激动地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
罗隆基一生热衷于政治,但最终沉沦于政治风波。究其原因,除了大的政治环境外,与他的性格也有着莫大的关联。少年时代曾和罗隆基接触过一段时间的学者章诒和认为:“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之君子,也是长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
早年好友胡适,对罗隆基也有经典评估:“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除了因“不能划清公私界限”而犯下“政论家之大忌”外,罗隆基的另一个致命处,就在于他才子型的风流倜傥、多情多欲。他长期游弋于政学两届,斡旋与各派之间。先天的禀赋加上后天的造化,让这位玉树临风的“帅哥”,如鱼得水,深得异性的青睐。不成想,风流一世的他最终却落得个“无家可归”的下场:“我是个鳏、孤、独。我是颠连无告的人!我是孤独,我是伶仃,我是举目无亲,我是死了无人知道的下场。”
罗隆基12岁那年,媒人给他说了个药店老板的女儿。那姑娘叫关英兰,比罗隆基大三岁。向来志趣高远又颇具叛逆精神的罗隆基是不依什么“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一口咬定不答应婚事。
1927年在英国留学期间,风流倜傥的罗隆基,在舞厅里结识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侨留学生张舜琴。她父亲张永福是新加坡富商,早年加入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正是张永福私产。罗隆基与张舜琴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不久,他们在新加坡举行了结婚仪式。
1928年双双返国,住在上海霞飞路的花园洋房里。张舜琴在英国学法律专业,回到上海挂牌当律师,并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教英语。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的罗隆基则身兼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及《新月》杂志主编等职。1929年张舜琴给他生了个宝贝女儿,使这个家庭更增加了快乐与生机。当时,罗隆基请了个上海保姆来关照孩子,张舜琴却不同意,说中国妇女没有文化,不懂育儿科学。她每天给婴儿洗冷水澡,赤裸着晒日光浴。时近初冬,气温很低,襁褓中的婴儿哪能经受得了,一个多月就把孩子折腾死了。罗隆基十分伤感。
根据他们的熟人传出来的消息,这夫妻俩在上海时矛盾很深,常常吵架,似乎还动手互殴,以至于罗隆基有时候脸上带着纱布绷带出去上课。张舜琴外表本分朴实,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徒,与罗隆基的性格迥然不同。
那时,罗隆基看上了徐志摩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罗隆基加入了张君劢的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他变本加厉,时不时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张舜琴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住,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