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版资治通鉴72册 (38)《柏杨版资治通鉴》这23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我打从出生(1920年?月?日)活到今天86岁,才领悟过来的话。 我的第二次出生──我一生有好几次惊涛骇浪、死去活来的经验──我自认第二次出生是1968年3月7日,因文字贾祸,被捉进牢的这一天。
直到1977年,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获释出狱。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入狱的那一天作为第二次的生日,理由很多,仅仅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今年(2006)在“北岳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并与大陆读者见面一事来说,不但要归功于牢狱之灾,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如果没有这场牢狱,我无论怎么摇笔杆,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闻名于世的美国包可华(Art Buchwald),只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
坐牢九年二十六天,使我潜心读史,开始我对中国绵长历史的爬梳工作,也建立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我选择1968年4月1日作为我第二次的出生,理由岂不已足够?提携我最多的至友、更是我的良师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说:“……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呢?……”(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德刚教授是主题演讲者。
)唐教授这番话,实在是我一生的点题之笔。他甚至嘉许我这本《柏杨版资治通鉴》说:“柏杨,柏杨,这就是你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至友与良师这句话,我万分不敢当,但感激与惕励之心,确是我人生舞台中不绝于耳的支持与鼓掌。
语言是思想网络上的坐标。把距今九百余年所完成的《资治通鉴》(公元1067年,宋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赐序给《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用我们这一代的语言──现代语文,把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几年的中国历史,重述一遍给读者听,除了语言的演化之外,我当然不能保持封建时代的思想价值标准。
新的时代当然有新的坐标,所以在“臣光曰”之余,我有我的“柏杨曰”。这是我这一套译书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特点。
今天我们进入信息发达的计算机时代,我们的社会也由绝对的单一信仰,进入到开放多元的时代。语言结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等等演化的速度比过去要更快。今天年轻的一代,在计算机的使用中不但出现新的语言,甚至发展出图像文字。
在有变、有常的生命长河里,我相信历史是我们人类文化累积的资产,属于恒常不变的湍湍长流,语言文字表达却会随着时代而演变。我相信将来会有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出现,更有不同人物的史观评价,补充“臣光曰”和“柏杨曰”。
出版前夕,想到我自己一生的转折,祸与福相倚的吊诡,就要拋开目前流行的短线操作,而学用历史深邃的眼光来看待世事,《资治通鉴》正是一本宝典。
2006年6月1日 于台北新店
柏杨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开始问世时,曾经写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当七十二册平装本,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再提笔写这篇“再序”。二“序”之间的距离,在书本上不过只差一页,但在时间上却差十年。
这十年对全世界而言,是一场巨变。执笔之初电脑还是一个神话,于写到尾声时,它已完全进入人们生活。而在台湾,执笔之初对警备司令部和调查局,还心存惊恐,于写到尾声时,人们已开始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巨变影响面之大和影响程度之深,过去从没有过。在发生之前,也从没有人认为它会发生。 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的是: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于写到尾声时,两岸已交流频繁。
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于写到尾声时,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以致,我们的后续工作,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加倍复杂。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资治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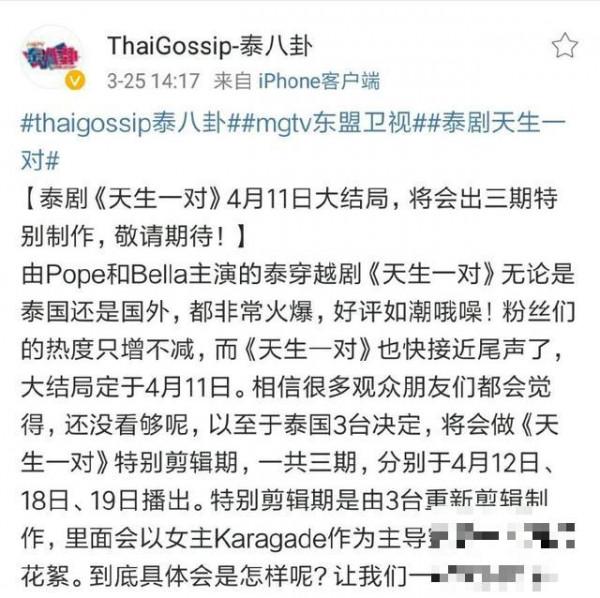




![>《南怀瑾选集(典藏版)(全12册)》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6/7b/67ba33ba663a3aa081f84374e4ec41c4_thumb.jpg)
![>[周润发国语版]>>周润发替身杀手国语版>>赌神5周润发国语版](https://pic.bilezu.com/upload/b/86/b86f03905f3d2601cab42d237123eff0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