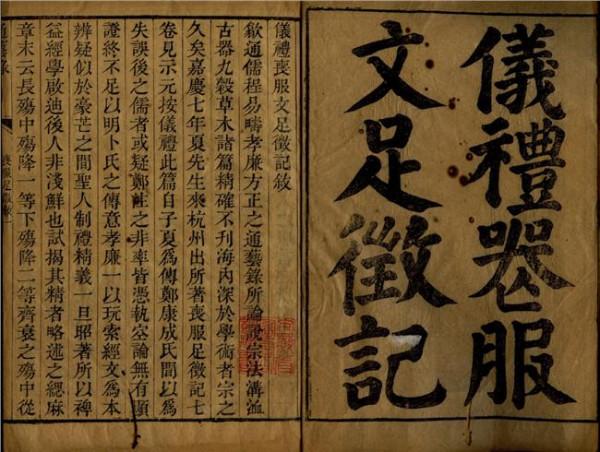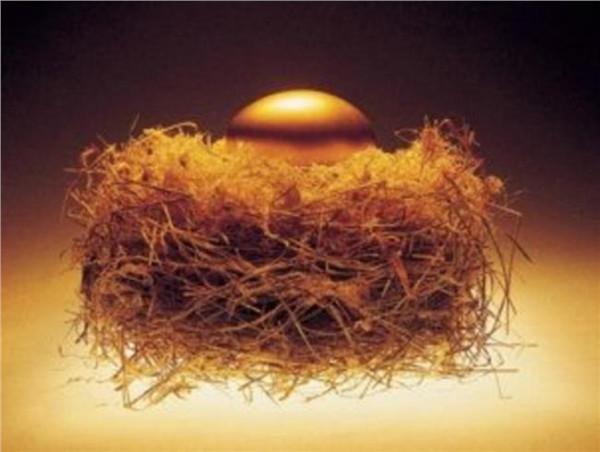子夏丧服传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仪礼·丧服》篇除“经”文、“记”文之外,还有“传”文,这在《仪礼》十七篇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传”文即是着名的《丧服传》(也称《服传》)。《丧服传》的撰作者是谁?子夏与《丧服传》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对此,学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今不揣浅陋,试对这一问题略陈管见如下。不当之处,唯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是幸。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记”与“传”三部分,是经、记、传的合编本。该篇缌麻章后标有“记”字,此前为经文部分,此后为记文部分,而经、记部分均有标注“传曰”的解释性文字,这就是相传为子夏所“传”的《丧服传》。
起初,《丧服传》与《丧服经》(含记文)别本单行,亦即今本《仪礼·丧服》篇曾经以单经本与单传本两种本子分别流传。这从东汉班固所撰《白虎通》的称引中即可见其迹象。如《白虎通》卷四《封公侯·为人后》、卷七《王者不臣·不臣诸父兄弟》与《子为父臣异说》、卷九《姓名·论名》、卷十《嫁娶·事舅姑与夫之义》等篇章中凡五次称引《仪礼·丧服》篇之传文均曰“《礼·服传》”;而卷八《宗族·论五宗》、卷十一《丧服·诸侯为天子》等篇章中凡两次称引《仪礼·丧服》之经文均曰“《丧服经》”,又于卷十《嫁娶·卿大夫妻妾之制》中称引《仪礼·丧服》之经文曰“《礼·服经》”。
[1]可见汉人是严格区分《仪礼·丧服》中的经文与传文的。又据东汉熹平石经所刻《仪礼》只有《丧服》经文,而无《丧服传》的史实,似可推论出《仪礼·丧服》的经与传在汉代别本而行的结论。
现代考古发现也可证明《仪礼·丧服》的经与传在汉代曾别本而行的史实。1959年7月甘肃武威县出土了比较完整的九篇《仪礼》,一篇写于竹简,八篇写于木简。这九篇简本《仪礼》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三种本子的《仪礼·丧服》:
甲本--木简,较乙本字大而简宽。简长55.5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三寸。第一、二简之背面题曰“《服传》”、“第八”。简文内容为《仪礼·丧服》的经、传、记,但经、记俱不足今本经、记的二分之一,而传文却基本上与今本传文相同。
乙本--木简,较甲本字小而简窄。简长50.5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一寸。第一、二简背也题曰“《服传》”、“第八”。简文内容与甲本《服传》相同。
丙本--竹简,简长与甲本相同。简背无篇题。内容为《仪礼·丧服》的经、记之文,而无传文。其经、记之文与今本相同,当是别本单行的单经本(含记文)。
由于甲、乙本《服传》所录的经、记之文均不及今本经、记之文的二分之一,因而陈梦家先生曾误认为甲、乙本《服传》为删经删记的《丧服经传》本,是汉人依据西汉时施行丧服的实际情况而删去部分经、记后所形成的本子。[2](p.
17-33)而沈文倬先生论定甲、乙本《服传》并非删经删记之《丧服经传》,而是《仪礼·丧服》传文的单行本,其部分录有经文者,“是出于撰作者为解经所需的引述;有些经记之文意义显明,可以错互参见,没有撰传必要,其文就不见于单传”。[3](p.73-95)[4](p.33-52)沈氏之说理据充分,可为定谳。
关于《丧服传》的作者,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相传本篇传文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或“作”。《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曰:“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今本《仪礼·丧服第十一》篇题下标有“子夏传”三字,贾公彦疏曰:“传曰者,不知是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为。
……师师相传,盖不虚也。”唐开成石经《仪礼,丧服》篇标题作“丧服第十一子夏传”。不过,据阮元《仪礼·丧服)校勘记,石经此题原刻作“丧服经传第十一”,无“子夏传”三字,后磨改为现今的样子。
而前述简本《服传》亦无“子夏传”三字。可见隋唐以前人们还只是传说《丧服传》为子夏所“传”或“作”,至隋唐之际,人们始将《丧服传》的“传者”或“作者”明确着录为子夏。
后世经学家对于子夏“传”或“作”《丧服传》的说法,疑、信不一。朱熹相信子夏作《丧服传》。他的学生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朱熹回答说:“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5](p.2187)
元代礼学家敖继公则对于夏作《丧服传》之说很不以为然,他在《仪礼集说》卷十一《丧服·记》后按语中说:
先儒以传为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记明之。汉《艺文志》言《礼经》之记,颜师古以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是也。而此传则不特释经文而已,亦有释记文者焉。则是作传者又在作记者之后明矣。今考传文,其发明礼意者固多,而其违悖经义者亦不少。然则此传亦岂必知礼者之所为乎?而先儒乃归之子夏,过矣。[6]
方苞则怀疑《仪礼·丧服》经、传均经王莽、刘歆增窜。他说:
余少读《仪礼·丧服传》,即疑非卜氏所手订,乃一再传后门人记述而间杂以已意者;而于经文,则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时憯然不得于余心。乃试取《传》之云尔者剟而去之,而传之文无复舛复支离而不可通晓者;更取《经》之云尔者剔而去之,而《经》义无不即乎人心;然后知是亦歆所增窜也。
盖丧服之有厌降,见于子思、孟子之书。惟尊同不降,则秦、周以前载籍更无及此者。而于莽之过礼竭情以侍凤疾,及称大皇太后,义不得服功显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为比类焉。[7](p.24)
曹元弼《礼经学》卷五《戴氏震与任幼植书辨〈丧服经传〉》”云:“幼植奋笔加驳于孔冲远、贾公彦诸儒,进而难汉之先师郑君康成矣,而訾汉以来相传之子夏《丧服传》为刘歆、王莽傅会矣。进而遂訾《仪礼》之经周公之制作为歆莽之为之矣。呜呼!《记》不云乎:毋轻议礼。……俗学肤浅,往往求之不可通,辄肆指摘云:刘歆窜入若干。”可知清儒任大椿(字幼植)认为《丧服传》并非子夏所传,而是刘歆、王莽辈傅会伪造。[8]
着名礼学家胡培翚虽然认为“歆莽增窜《丧服传》说”是“丧心病狂”,但他认为《丧服传》是否为子夏所作还难以定论。他说:
今案:经文精微详悉,非周公莫能作。记、传亦皆圣贤之徒为之。但此传为子夏所作与否,似当在阙疑之列。近儒乃谓传文有莽、歆增窜者。《礼经释例》云:《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莽、歆伪撰,若《仪礼》自西汉立学以来,从无有疑及之者。为此论者,自非丧心病狂,不至于此。盖深恶其说之足以害经也。[9](p.1340)
另一着名礼学家曹元弼则在批驳歆莽傅会增窜《丧服传》说的同时,进一步申说、论述了子夏作“传”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他说:
疏云:人皆云云,师师相传。则作传者为子夏,自周以来旧说也。作者创始之辞,后儒传述增续,但可谓之述,不可谓之作。故《孝经》有子曰、曾子曰,而郑君《六艺论》以为孔子作。《史记·弟子列传》以为曾子作。《诗》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而统言则曰子夏序。
《公羊传》数传始着竹帛,传内有子公羊子曰,而贾云公羊高所作。此传云子夏作,盖同斯例。传文兼释经、记。经走周公所制,释经者实子夏原文,记是七十子后学所为,释记者皆后师增续。
其释经处有一二未安,为郑注所驳者,或数传后失其本说,而以意补之,未能尽善。浅妄之徒,因传有释记处遂谓此传全出作记之后,非子夏所为,致启歆、莽增窜之诬。殊可叹也。此传既为子夏作,不题子夏传者,诗序亦不题子夏序,故陆氏《诗·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也。[10]
大概是受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影响,现当代学者已很少有人相信和坚持《丧服传》为子夏所“传”或“作”的说法,连力主子夏作《传》说的曹元弼的入室弟子沈文倬先生也再不相信此说,他认为:“《丧服》称子夏传虽始于唐人,但当时并无一致之说。
简本无此三字(‘子夏传’),解决了这个悬案,子夏撰传之说不足信据。”[4](p.33-52)在不相信子夏“传”或“作”《丧服传》的现当代学者中,以陈梦家与沈文倬二先生关于《丧服传》撰作时代的说法最有代表性。
陈梦家先生推论《丧服传》当作于汉宣帝甘霹石渠会议之后,“有可能为后仓或其徒庆普所作或流传”,“它的撰作或行世,当在昭、宣之世”。因为庆普与大小戴同为后仓之弟子,故又推定其为今文学。其根据有二:其一,宣帝甘露三年二月举行石渠阁会议所写成的《石渠议奏》,引有《丧服》经文“庶人为国君”与记文“宗子孤为殇”,这些都不见于简本《服传》。
陈氏遂以为此等经记之文已被《服传》作者所删削,从而判断简本《服传》之成书“当在甘露之后”。
其二,根据《石渠议奏》与大小戴等说解《丧服》之义与《服传》有同有异,陈氏遂以为《服传》“不可能出于后氏诸徒小戴、闻人(通汉)之手”,“是二戴以外的家法”,从而断定《服传》“可能是庆普之学”,属今文学,而“删经与撰传同时进行”。[2](p.17-35)
沈文倬先生虽然也不相信子夏作过《丧服传》,但他不同意陈梦家先生将《服传》的成书时代定在甘露之后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其一,《通典》所引《石渠议奏》中有三处引用《服传》之文,可见《服传》作于甘露之前。
其二,石渠会议参加者皆为今文家,从大小戴、闻人通汉等人对《服传》抱无视、曲解、非难的态度,可推定《服传》不可能是今文学,而可能是古文学。其三,郑玄所作《仪礼》注,于《服传》无今、古文校勘,但以其他篇目中所校古今文异字来核对简本《服传》,则简本《服传》之文每同于古文,从而可推定《服传》当为古文。
其四,《服传》中有引用小戴的《礼记》中的《丧服小记》、《大传》、《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檀弓》、《丧服四制》等篇之文,而这些篇目大多为七十子后学所记,故断定《服传》撰作时代之上限在《礼记》论礼诸篇成书以后,即周慎靓王以后(公元前315年),其下限在秦始皇焚书以前。
[4](p.33-52)
沈氏据《石渠议奏》有引《服传》之文,驳陈氏以为《服传》作于甘露后之非,又据郑玄校古今文之例,推论《服传》为古文,均有理有据,可以信从但他与陈梦家氏及其他当代学者彻底否定子夏与《丧服传》有关的观点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说《丧服传》完全由于夏所“作”,可能与史实不符。但将《丧服传》看成是由于夏所“传”,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虽然唐人说《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似乎是出于传说,但传说不一定无据;虽然由于文献不足征,现已难以确切认定子夏与《丧服传》的关系,但种种迹象显示《丧服传》由于夏所“传”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也就是说,子夏具备“传”《丧服》的资格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