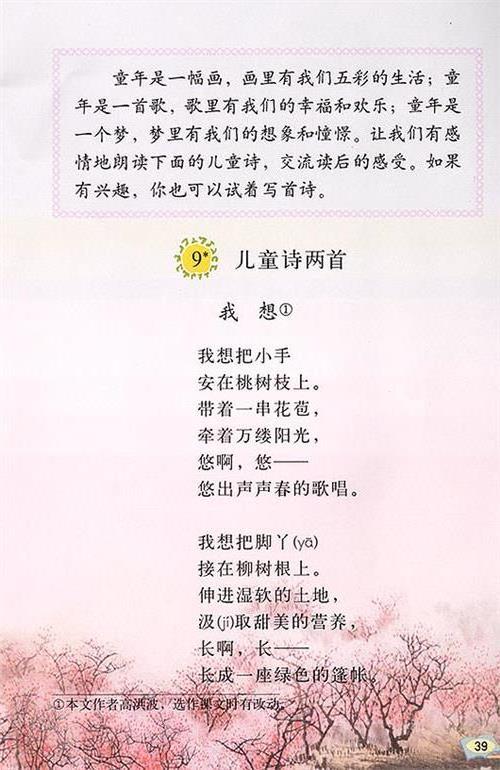孙甘露诗意常在 别让诗意只存活在诗里 2015我的阅读:短篇小说
文学是美的艺术,一部文学作品,思想再深刻、题材再独特,都必须蕴含在优美的艺术之中,才能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这是一个常识,但这一常识经常有被忽略和被遗忘的危险。诗意,应该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应具有的品质,诗意不仅仅属于诗。
小说是讲故事的,故事里要不要有诗意?是记述人物事件的,字里行间要不要追求美感?这些问题单拎出来谁都知道答案,但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文本时,却有意无意会省略一些东西,而那被省略的部分或许正是一部作品理论上必须具备而实际上缺失的内涵,诗意与美感常常被这样省略。文学因此"具备"了很多东西,却背离了它的本真。
鲁迅先生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史家",司马迁完成的是一次"绝唱",如果说这还是一种比喻的话,一部史传作品能让人读出《离骚》一样的诗意,更能说明鲁迅肯定其价值所示意的"方向":《史记》是艺术,是一部蕴含着悲壮、悲悯与悲凉情绪的"叙事长诗"。
这是非常值得人去寻味的评价。当我们从司马迁的书中努力寻找历史人物踪迹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读到司马迁为后人营造的历史风云背后更具立体感、更令人回味的人心世界。
帝王的面目、义士的风采、春秋战国独有的精神气象,这些可贵的品质才是《史记》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也是这部史书成为伟大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我们常说时代需要史诗般的精品力作,而忘记了只有"史"与"诗"真正融合为一体,作品才可能是传得开、叫得响并能传之久远的经典。
伟大的文学作品说到底都是诗,经典的小说、经典的戏剧、经典的散文,无一不是如此。诗意是文学的基本特征,而不只是诗歌艺术的一种形式。
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到了文学批评应该发挥的作用。直至今天,很多批评家既没有把批评本身视为艺术的一种,没有在"诗意"创造方面做过切实的努力,更要命的,是把生动丰富、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当作分析社会事物的材料,只求意义读解,而忘却了从一部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出发去评价作家作品。
所以批评界讨论的问题,通常都是与社会思潮相贴近,与时尚话题相关联的"非文学"问题。从美学意义上去阅读阐释一部作品,从诗学的立场去评判一个作家的创作潜力,这样的功能似乎已经从当代批评中削减至无,这或许是当代批评面临的最大危机。
批评家对文学的热爱程度、对诗性的理解能力、对作品的感悟能力并没有成为对其批评资质的考验,而看上去可有可无。所以才导致批评于作家、于读者都无益的情形。
回到常识,从常识出发,为文学找回诗意,是作家、批评家共同的职责。
孤独到底的《石泉城》
不得不说,《共产党》是我这些年读过的最美短篇之一。故事很简单,一个16岁的少年,被母亲的情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带着去打猎。猎物是湖里成千上万的野鹅。母亲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也许在她看来,让一个朝三暮四的情人带着儿子打猎本身是件不靠谱的事。
对少年来讲,母亲的情人是活力和青春的象征——骑着辆棕色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脚上穿着黑红两色的长套鞋,反戴一顶棒球帽。少年甚至想:"我觉得他肯定在CIA干过,看见或发现什么让他觉悟了,并最终被CIA赶了出来。
"狩猎的过程惊心动魄,关于野鹅的描写更是让人惊艳。狩猎结束后,母亲发现一只受伤的野鹅,并要求情人将它打死。她说:"你必须把它打死。难道规矩不就是这样的吗?"情人在她的胁迫下最终打死了那只鸟,而他与母亲的关系,也在这场狩猎中彻底终结,他甚至把枪递给少年说:"你难道不想开枪打死我?没有人想去死,但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少年没有动手,他只是想:"我为他感到难过,就像他已经死了一样。
"小说的结尾,是少年和母亲站在阳台上,母亲问他:"你觉得我还有女人味吗?我已经32岁了,你不懂这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你觉得我还有吗?"少年抬头看着阳台前的薄雾,虽然看不见野鹅,但是他能听见它们飞翔时发出的声音,能感觉到它们翅膀下面流动的气流。于是他说:"有,我觉得你有。"
理查德·福特在小说集《石泉城》中,几乎全是这样破碎伤怀、意味繁复的故事。在阅读中我时常被简洁而极富张力的细节击中,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窗户抽支香烟。《甜心》中,"我"和情人阿琳送阿琳的前夫博比去警察局。
博比因为签假支票和抢劫便利店要蹲监狱了。这是古怪而不符合生活常态的送别,况且这送别是在一个孩子的注视之下进行。在警察局门口,博比把手枪扔到座位上说:"我本想杀了阿琳,但我改了主意。"博比入狱后,"我"和阿琳把枪扔到河里,然后是场貌似寡淡的对话。
阿琳问:"你不会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抛弃我吧,会吗?你仍是我的甜心。"在小说中,字里行间流逸着叙述者的无奈、疲惫和尴尬,仿佛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堪事时所采取的态度:默默承受,然后让这承受成为一种令人狐疑的美德。
理查德·福特的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要不是"我"、"我"的情人或孩子;要不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母亲的情人。《石泉城》如此,《大瀑布》如此,《乐天派》如此,《甜心》和《共产党》更是如此。
他们的职业也很雷同:男人大部分失业,要不就是诈骗犯、偷车贼;女人通常是酒吧女,人物背景之单纯让人咋舌。可以说,跟卡佛一样,理查德·福特小说中的人们也通通是在社会底层煎熬的人。
如果说这些人拥有什么,那么,永恒的孤独感和持续坠落是惟一、也是最好的描述。但就是这些不断重复的人物身份,不断重复的背叛与出走,在哀而不伤的叙述中一点点凸显出貌似模糊实则鲜明的个性,最后以优雅简洁的方式打动我们内心里最静穆也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卡罗尔·斯科莱尼卡在传记《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曾数次提到理查德·福特与雷蒙德·卡佛交流的场景。卡佛认为,福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一片心》是"几年来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书"。
他们还常在吃早饭时谈论打猎和钓鱼——在他们的小说中,打猎和钓鱼都是司空见惯且异常重要的场景。他们都是小人物的代言人,然而他们又如此不同(朋友们在谈论他们时,还常常提到布考斯基。
可我觉得,布考斯基小说的粗鄙叙事和糟糕文本没有任何意义,《苦水音乐》是这些年我读到的最无聊的小说集)。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普通人:卡佛、福特和蓝领现实主义》中提到,卡佛的简约主义是一种"经过现代主义的怀疑与绝望情绪锻造的现实主义"。
而卡佛和福特的区别在于:卡佛绝望,而福特在绝望的缝隙里,埋藏着不易察觉的怀疑和微弱渺小的希望(譬如《焰火》,女人为了让丈夫重燃生活希望,手持焰火在雨中舞蹈)。从个人口味和对小说的理解上说,我觉得理查德·福特比雷蒙德·卡佛更富有才华,且能将才华物尽其用,不浪费一毫一厘。
如果说理查德·福特的缺陷在哪里,我认为他有点饶舌。几乎在每一篇小说的中间或尾部,他都会很合时宜地来上一段议论(他那么懂得分寸和技巧,让你无话可说)。尽管这议论不无道理,我还是很想用铅笔将它们重重划掉。如果去掉这些文字,我承认理查德·福特的所有短篇小说都是完美无瑕的短篇小说。
阴冷不乏光亮的《死水恶》波
初读《死水恶波》会以为是篇类似约翰·斯坦贝克《菊花》那样的小说:水泵修理员哈里应邀到乡下修理水泵时,碰到了农妇艾达。艾达的丈夫不慎触电身亡,哈里亲眼目睹了艾达变成寡妇的过程。接下去艾达有意无意接触哈里,在干萎的草丛里聊天的细节甚至有些引诱的意味——读到这里,我还在拿艾达跟《菊花》中的艾丽莎比较,觉得她们骨子里是一类人:渴望逃离,只不过一个无意识,一个有意识。
在哈里看来,艾达的眼里"充满了对他的欲望"。
他为她情迷意乱,幻想带她逃开这一潭死水。可他却无意间发现了秘密……离开小镇时艾达跟哈里说:"我能跟你走,我会对你好的。"哈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并且道出她谋杀了丈夫的事实。
结局是艾达用扳手打晕了哈里,而哈里只能躺在地上看着天上的"宇宙碎片"。到了这里,蒂姆·高特罗用更冷酷的叙述将自己跟约翰·斯坦贝克彻底区别开来。
在蒂姆·高特罗的小说中,类似《死水恶波》风格的不少。《晚间新闻让人胆寒》里,杰西·麦克尼尔醉酒后驾驶的装载化学药剂的火车终于出轨,造成爆炸伤亡,他惟有在一路狂奔中等待着末日到来;《灭虫人》中,以灭虫为职业的菲利克斯似乎就是上帝的一双眼睛,窥视着每个家庭分崩离析的过程;《合法偷窃》中,被妻子抛弃的酒鬼拉多想找份工作,不成想廉颇老矣,更沉重的灾难在等候着他;《赌桌上的调味酒》是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读起来五味陈杂……可以说,蒂姆·高特罗笔下的主人公,全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农村,他们都是小人物,而且是已经被麻烦缠身、或者即将被麻烦缠身的小人物。
虽说蒂姆的小说跟美国南方的小说传统一脉相承,但与他们不同之处也颇为明显,那就是小说中的亮度更强烈,人心更软嫩温厚,瞬息的人性光芒让人心生敬畏,远不是奥康纳小说里那种邪恶到底的冷酷,也未如福克纳的小说客观冷静、芜杂广阔——有时你甚至觉得他的小说有些说教的意味。除了对这个世界邪恶的想象和憋闷的呼喊,他似乎更在意让那些明亮的光照耀在身心俱疲的主人公身上。
蒂姆·高特罗极少重复自己。理查德·福特的小说集《石泉城》中,几乎每篇小说里都有离家出走的母亲、失意的父亲、情人的丈夫或母亲的情人。蒂姆跟福特的区别在于,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是独特的、无重叠的,《死水恶波》里的哈里是水泵修理员,《晚间新闻令人胆寒》里的杰西·麦克尼尔是火车司机,《赌桌上的调味酒》中的一帮赌徒身份各异,他们是挖泥船上的厨师、司炉工、水手、焊工、领航员……蒂姆·高特罗会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使用一些陌生的名词和专业术语。
我想,蒂姆·高特罗肯定是A型血。他对细节和陌生领域的热爱让他在写作时千方百计地搜罗大量的相关资料(那个时代还没有google),为了掌握这些陌生的知识他曾煞费心血,所以在小说中要不遗余力地展现、小心翼翼地卖弄。
这无可厚非。我喜欢A型血的人。如果没有猜错,杜鲁门·卡波特肯定也是A型血。
永远的《逃离》
有个好哥们儿私下里跟我说,其实艾丽丝·门罗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挺失望的。他的理由出乎我意料又让我忍俊不禁。他很郑重地说:"我倒是希望村上春树获奖,那样的话门罗就不会被更多人关注,她只会成为我的‘秘密武器’。"我必须承认,他是个可爱的老男人。
我知道艾丽丝·门罗是2009年,当时买了她的短篇小说集《逃离》,可并没有读。2011年在鲁院上学期间,北大教授陈晓明在给我们讲课时极力推荐她,我才回过头去细读《逃离》。说实话,当时的阅读体验是,这个生活在小镇上的女人真的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那本集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侵犯》《逃离》和《沉寂》。
《侵犯》讲的是刚搬到小镇上的女孩劳莲,意外地交上了一个在酒吧当女招待的朋友德尔芬。德尔芬对劳莲似乎怀有一种格外的关注和温柔,这种温柔和关注让人心生疑窦。但我们很快知道,德尔芬多年前有个私生女,送给了别人。
她认为劳莲就是她曾经失去的女儿。劳莲以为自己知道了真相,感到很痛苦,也许对于一个10多岁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经历足够让她寝食难安。在此门罗显示了高超的技艺,她是怎样描写劳莲的呢?"她肚子里既感到胀又感到空虚……因此她一进屋就直奔厨房的碗柜,给自己倒了一大碗早餐必吃的燕麦片。
家里没有枫糖浆了,不过她找到了一些玉米糖浆。她站在冰冷的厨房里吃了起来——连靴子和外套都没有脱,一直看着新变白的后院。
白雪使得外面的东西清晰可见,即使厨房里灯光是亮着的。她看见自己在玻璃上的影子映衬在白雪覆盖的后院、岩石和长青树枝之前……"门罗没有对女孩进行心理描写,可女孩内心的波动起伏却分毫毕现。
接下去她装病休学,直到德尔芬登门来访。事情也真相大白,原来劳莲的父母确实领养过德尔芬的女儿,不过她已在一场意外中丧生。劳莲确实是父母的孩子,而不是抱养的。
最后一幕,劳莲和父母以及德尔芬把夭折女婴的骨灰撒到雪地里。回家路上,劳莲的睡裤上粘了很多蒺藜。她发疯似的想把它们从裤子上摘下,可很快所有的手指上都粘满了蒺藜。她惟一能做的,仅仅是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一场心灵风暴袭过,那些貌似消逝的伤害,还是如这细小棘刺扎入灵魂,让当事人每每回望,仍感到不适和焦虑。
门罗在这篇小说里用的是全知全能的视角,让我惊讶的是读完时,竟忘记她是如何在人物间腾挪转换的。这是一种技巧上的高明,更是一种叙述上的高明,略显温吞的叙事中,她让我们全然忘记了自己挑剔的目光。
《沉寂》中,一个女人等待自己失踪的女儿归来。年华老去,她搬了几次家,换了几任男友,从著名的主持人变成了穷困潦倒的隐士。而离家出走、寻找心灵平衡的女儿仍无音讯。小说最后,将近20年过去,她偶遇女儿的同学,才晓得女儿早已嫁为人妇,养了5个孩子,过着富裕的生活……她被女儿彻底遗弃了,女儿的逃离将她置于一个滑稽悲凉的位置:她成为了曾经的女儿;而女儿,成为了曾经的她。
这篇小说中,骨子里绵延不绝的寒冷让人窒息,如枯棘扎喉。
门罗自己曾经说过:"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她委实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她的叙述永远那样平静自如、舒缓有序,如夜晚之巨河流,只听得河水流淌之声响,却看不到河流汹涌之姿态,而那种河水与暗夜交融的磅礴气势,却早已将我们笼罩其间。
有位好友曾在微博上力赞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克莱尔·吉根,认为就短篇而言,她超越了门罗。随后又有几位女作家附和。我不太赞同她们的看法。不过男人与女人的眼光总是迥异的,这很正常。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委实很好,小说集《南极》和《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精致典雅,举重若轻,刀剖一角,痛感隐约,可无论从语言结构,还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上,都远远不如门罗来得自如老辣。
吉根清浅,门罗则庸常、绵长、含混、歧义,"庸常"让读者有种冷暖自知的通感,"绵长"则让文字余味沉实醇厚,而"含混歧义",无疑就是黑夜里的那束星光——你不晓得它来自哪个星系,也不晓得它距离如今有几许光年,然而它委实闪耀在我们的头顶。
如今关于门罗的评论铺天盖地,也就不必再劳神去分析她的文本。也许,对一个已经盖棺定论的作家,质疑和借鉴才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