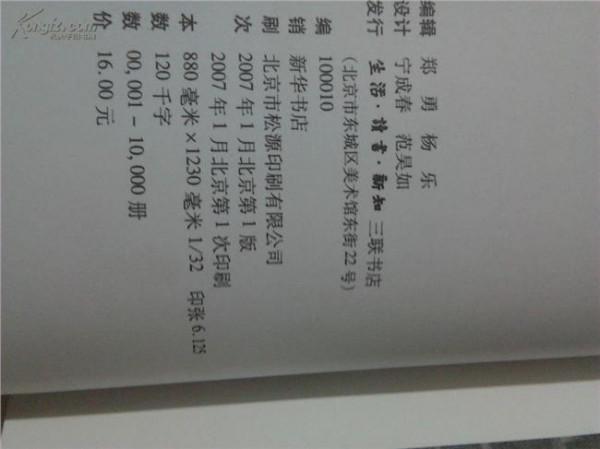曹景行父亲 对话曹景行:受教于父亲曹聚仁是一种奢望(图)
曹景行,1947年出生在上海,1968年下乡在皖南山区插队,伴黄山十年。
1978年曹景行与妻子一起考入复旦大学,携妻带女返沪。学历史四年后,曹景行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年逾四十,他去香港应聘做《亚洲周刊》撰述员,两年后成为资深编辑,1994年成为副总编,兼任《明报》主笔,写社论和评论。
50岁时,曹景行改行做电视,出任香港传讯电视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1998年加盟凤凰卫视,现主持《口述历史》和《景行长安街》。2005年开始在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
年已花甲的凤凰卫视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前不久出现在深圳,参加其新书《香港十年》的发布会。 曹景行有个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四界”的父亲———曹聚仁,曹聚仁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与鲁迅交往密切,写有《鲁迅评传》,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1956年起,曹聚仁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是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
曹聚仁去香港时,曹景行才三岁,虽然父亲以后频频北上,但和家人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
直到1972年,父亲即将辞世,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曹景行从安徽乡下返回上海,和姐姐曹蕾一起赶往澳门,却没能见到父亲在世之前的最后一面。曹景行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每当朋友说我在香港新闻界打工是‘继承父业’时,我难免肚中一番苦笑。
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 曹景行比父亲曹聚仁晚成名,但他比父亲的运气好,30岁之后凡事顺利。
现在,曹景行仍精力充沛,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七八份报纸。陈鲁豫曾这样描述他:“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刊出现在公司。
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多份报刊,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
”所以,凤凰卫视的同事们私下称曹景行为“影帝”(影印之帝)。他自称把吃饭睡觉的时间扣除,就是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就是他的生活。 “人生应该快乐而积极” 早期经历:一度比人家还困难 记者:早年对父亲有些什么印象?严肃吗?还是很慈爱? 曹景行:父亲就是父亲,因为不生活在一起,没什么直接的感受,那个时候也没选择,没有第二种可能性,所以,也无所谓遗憾。
我读高中以后,父亲给母亲写信的时候也会给我写几句话。我后来读父亲的文字就是对作品与作家的解读,没有非从“他是我父亲”这个角度去理解,也没有丝毫骄傲。
记者:今天去看,您觉得一个家庭的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在人生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您父亲曹聚仁先生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曹景行:很难说家庭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在人生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不能一概而论,大历史大环境很多时候决定了小人生。
我要是早生五年或者晚生五年,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乃至早生两年,我哥哥的人生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自己从来没有世家子弟的感觉,甚至比人家还困难,因为有海外关系,更麻烦。我母亲为了家庭几乎什么都放弃了,父亲去了香港之后,母亲要打理一个大家庭,赡养我奶奶我外公外婆等,全靠她。
我们从小受母亲的直接教育,她很正直,又很柔韧,“文革”那样的环境,她也能挺下来。1980年代后,大陆能出版父亲的文字了,我母亲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
母亲很善于安排家计,很能干,也很愿意牺牲,现在去看,还是很少看到像我母亲那样的女性。 记者: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上海给您什么影响? 曹景行:我出生在上海,会说上海话,上海和香港一样多元。
记者:在安徽农场的那十年是您最艰难的十年吗? 曹景行:也谈不上艰难,现在去想,还是觉得笑比不笑的时候多。
虽然很累,但是也很热闹,大家一起砍柴,一起做工,很快乐的。做工之后,我会找书来读,尤其是放年假的时候,大家都走了,我留下来守护连队,一个年假可以读很多书,我那时候重新读《红楼梦》、《水浒传》、《二十四史》、《聊斋》等。
记者:在安徽农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是父亲做战地记者的地方?后来去父亲教过书的暨南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曹景行:我当年给妈妈的信里提到过,但妈妈在信里讲做农民不错。
她本身是农民出身,我们家两代以前也是农民,对她来说,我去做农民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她还希望做好一个农民。后来我去暨南大学当然很高兴,暨南大学对我父亲来说很重要,暨南大学对我父亲也很好,他们的校史里用了很多我父亲的回忆文字,他们通过我父亲的关系找到了很多当年的校友,暨大很有包容心,很感谢他们能请一个25岁的中专生———我父亲曹聚仁做教授,又让我这个本科生去给他们讲座。
记者:十年的知青生活教会您一些什么? 曹景行:知青生活教会我吃苦,把苦都吃遍,后来就没有苦了。
我从上海下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要跟他们学习插秧学习犁田,但是,半年之后,我就能扛100斤一袋的水泥跟200人一起一步步走六个小时上山,200斤的米包我也能背得起。
知青生活还教会我跳出上海来看中国。 记者:回头看高考30年有什么感受? 曹景行:当时就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突然给了我一个机会,有机会就试一下吧。
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30岁了,不到3%的录取率,我跟妻子一起考,都考进了复旦大学,都31岁,于是,带着两岁的孩子和妻子一起回上海读书。
转行媒体:不快乐,做什么? 记者:怎么会40岁了还转行做媒体?到《亚洲周刊》做些什么工作呢?从经济研究员入行媒体有什么优势? 曹景行:在《亚洲周刊》是去打一份工,当时,内地的学历得不到香港的承认,很多内地的教授到香港找不到工作,我没精力再去读书,也没天分经商,无意间去应聘媒体。
在《亚洲周刊》做WRITING,看英文,再用中文整理成文。从经济研究员入行媒体有很好的优势,尤其在《亚洲周刊》这样大格局的媒体,掌握经济规律,有助于理解新闻报道,其实,新闻只是一个空的书架,有历史的基础与经济学的基础,才能更饱满。
记者:在凤凰台的十年又使您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您刚刚无意中说“人生不快乐做什么?”这是您的座右铭吗? 曹景行:在凤凰台的十年使我回到了大陆,被大陆的观众所接受,并被大陆的大学聘为老师。
是,“人生,不快乐做什么?”是我的座右铭。凡事都有两种态度,积极和消极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知青下乡,好不容易才等到大学向我们敞开,后来又经历很多事情,就更觉得人生应该快乐应该积极。
不快乐,做什么? 记者:香港回归十年之后有些什么变与不变?您的《香港十年》里特别提到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回归以后,香港的新移民有什么变化? 曹景行:十年之前,香港回归的日子,我们作为新闻人总有些担心,担心回归能否顺利进行。
那两天香港有8000个记者其实是来看出事的,我们自己也担心出事。
1997年7月1日晚上平静地回归,这比较意外,西方媒体同行很失望,那天下雨,雨后天气好转,也带来一种情绪上的好开端。10年过去了,香港从外貌上看没什么变化,多了些高楼。
但香港人的心理状态在改变,消除了10年前的政治障碍,人心的障碍也消除了,香港人说他们要面向世界,胸怀祖国。 前些天,香港的报纸有一个很小的消息:倪匡———卫斯理,回归之前,他从香港移民出去了,现在,他又搬回香港了。
这实际上很能代表一部分香港人:在香港生活得很好的中产阶级,因为对回归没有信心,先移民,后来,慢慢发现回归之后的香港和他们心目中原来的香港没有差别,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好了,于是,自己回来,或者他们的孩子们回来。
10年了,香港人心的回归就是最大的变化。 香港的新移民都在不断努力,不断改善自己的困境,香港是很让人发挥潜力的地方。
香港政府为加快家庭团聚,增加了50万新移民,对生活条件差的新移民给予社会救济与福利照顾,但新移民的生活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新移民的下一代应该能生活得很好。 记者:去大学教书后有什么感触? 曹景行:去大学教书之后我发现我可以教书了,教书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一个学期在清华大学开一门《媒体镜头与战争》,全校本科生选修,一周一节课,我可以做好它,感觉很好。
记者:可以简单数一下影响您的书吗?您最近看的碟是哪张? 曹景行:我所读的每一本书都影响我。
包括手头的这本《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大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他专门为媒体言论自由与老百姓的知情权作辩护,对抗政府的违法行为。最近看的碟是罗马尼亚的《加州梦》,非常精彩,我看完之后,感觉到中国的电影导演最好别再吹自己了,好好地学学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