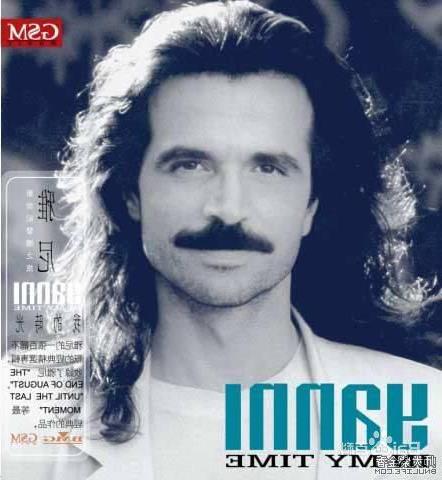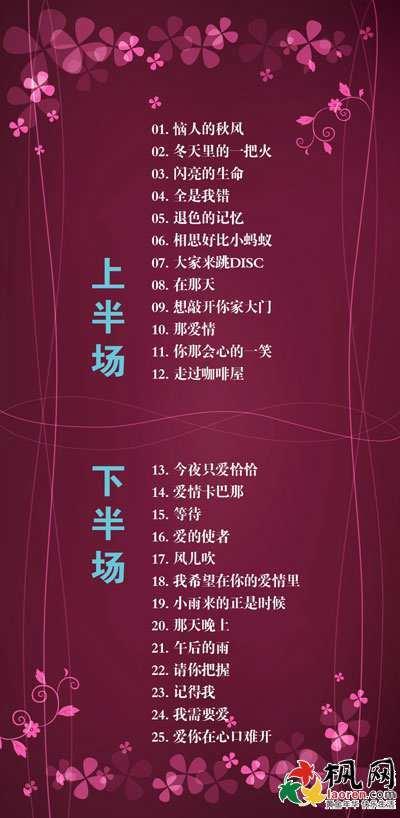陈进兴老婆 【经典老歌】【默哀】陈进兴三月三日去世!
音乐走进第二回合,制作人摇头晃脑随著节奏对著空中比著无形的指挥棒,帏幕另一边的歌手好像完全能看见,声音精准地落在每一个指挥所要的位置。重复的副歌,凤飞飞的歌声一波比一波高昂,声音愈来愈大,她手上彷佛有一支从心所欲的麦克风,可以无穷尽地调高音量,管弦乐在副歌最后已经全盘展开,百般乐器同时响起,彷佛千军万马奔腾,但凤飞飞金属般的清亮高音还在众多乐器的音浪之上,好像一架飞机飞翔在千里白云之间,人声与乐器相互抗撷,双双推到最高潮,最后铜管乐器喷洒而出,定音鼓也响起,凤飞飞的声音盘旋在三万呎高空,录音室里的扩音器彷佛要爆裂了,刹时,所有的声音同时停止,只剩一种撞击感还在我的耳际,我感觉内耳鼓胀,嗡嗡作响,一时之间有点喘不过气来。
「小吕,怎麼样?」凤飞飞已经平静的声音从喇叭音箱传出,制作人按下通话键,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第二段的情绪出来得太快,还可以再晚一点。」 「我也这麼想,那麼,我们重来一次吧。
全部从头,我还可以再抓一下感觉。」凤飞飞的声音从看不见的另一端传来。 录音师急忙倒带,高速旋转的录音带发出尖锐的嗞嗞声。制作人对著密闭的房间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来,take two,三、二、一,开始…。
」 遥远的钢琴声若不可闻地轻轻响起来,叹息般的女声轻唱也响起来,这一次像是喃喃自语,然后钢琴声逐渐清晰,我们也再次听到表演者倾诉般地描述她多年舞台生涯的甘苦,她唱得先是怀疑、犹豫,甚至带著伤痕,然后她再度通过她与台下掌声互动,产生一种自我解答与自我肯定,然后这种带著感激的自信步步升高,最后变成一种近乎宗教情怀的信仰…。
你闭上眼睛,几乎感觉到凤飞飞是站在舞台之上,聚光灯打在她身上,形成一环光晕,台下漆黑一片,你并不知道舞台下是什麼模样,直到高亢的副歌响起,巨大的灯光打到台下,这时候你才看到台下万头攒动,那是千百张看著你的渴望的脸,这样的场面即使是超级巨星也不得不感动…。
我在录音室里听得喘不过气来,凤飞飞在录音间里的配唱真可以用「奇观」来形容。
她不是到了录音间才进入状况,她显然已经在家练习多时,她已经完全体会这首歌的意义,她知道该如何诠释它,她甚至知道该如何应用技巧来表达歌中的「剧情」转折。
她好像已经算好了「空间」,前段她放轻音量,情绪平静,让出来后面可以发展的「余地」,随著歌曲进行,表情开始变得丰富,情感渐趋澎湃,最后才登上底峰;但这样说好像也不够,因为即使是后面高亢之处,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道也唱不出这样的味道。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在录音室听歌手配唱,但这麼「敬业」和「专业」的录音却是非常少见。凤飞飞很重视演唱的情绪连贯,她很少用「修补」的方式来录音,她总是要求整段重录或是整首重唱,有时她也会应制作人要求重唱某一句,即使是只唱一句,她也总是音准精确,连情绪的贯串也几乎是一致的。
本来一首被我嫌为简单、缺少转折的「平凡」歌曲,被凤飞飞唱成了「超凡入圣」的经典之作,词曲作家能得到这样歌手的诠释,应该是莫大的幸运吧? 大概是唱了七、八遍之后,我实在已经听不出有什麼可以改了,在重听一遍之后,凤飞飞在「密室」内问制作人说:「你觉得怎麼样?」 吕子厚在控制室里抓抓头,露出一点腼腆笑容:「凤姐,我实在听不出有什麼好改了,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 凤飞飞在里面说:「你再放一遍我们来听听。」 录音机快速嗞嗞回转,录音师重新播出录好的音轨,音箱飘扬出来的声音充斥在整个房间,整首歌唱得荡气回肠,听的人简直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那是一种近乎战栗的享受。
歌播完了,轮到制作人问她:「凤姐,你自己觉得怎麼样?」 里面沉默了几秒钟,凤飞飞开口了:「我觉得第二遍的唱得有点over了,我想我可以再试试。
」 我和吕子厚对望了一眼,大概是说,凤飞飞太吹毛求疵了,都已经唱成这样,还能有什麼进展吗?制作人说:「重唱第二遍吗?」 凤飞飞说:「不,我想全部重唱一次。」 吕子厚微微笑了一笑,示意录音师播放音乐:「准备好了吗?现在来,三、二、一,开始…。
」钢琴重新轻声响起,凤飞飞轻叹似的念唱,好像喃喃自语,又好像迟疑不确定,我想像她在布幕内调暗的灯光中闭眼轻唱,她十几年的起伏生涯应该像电影般一幕幕掠过眼帘:「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采,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我想像她眼角湿润,回忆起经历过的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楚与坎坷,然后她唱到掌声响起来,一切不幸与不堪彷佛都有了「回报」,艺人的最大报酬也许就是众人的爱,不一定是那些她根本用不到或不能用的金钱。
她的高音一层压过一层,她彷佛是内心的巨大旁白,「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但我也若有所悟,这浅白的歌词才是属於凤飞飞的歌词,我想像的那种「文人式」的歌词既不是她的语言,也不是她听众的语言,她对这首歌了解这麼透彻,就是因为这是她的简单却包裹她一生的语言…。
---------------------- 凤飞飞的信差(之六) 当天夜晚我离开录音室先走了,留下歌手凤飞飞和制作人吕子厚,他们还要继续挑灯夜战,录制其他的歌曲。
但〈掌声响起〉的录音过程却在我脑中盘旋不去,一方面是凤飞飞把那首歌唱得太好了,让我感到无比震撼;另一方面则是她从密闭的录音间走出来时,眼角泛著泪光,可见她在录唱时是哭过了的。
我在深夜的计程车上,默默咀嚼这些画面的意义;我拿出书包里的笔记本,在黑暗中草草写下几个字:「歌声停了,灯光亮了,掌声响起…。」 也许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对於一位表演者而言,世俗上的成功、光荣或者金钱,都是过眼云烟,在表演与舞台退去之后,时间才是最后的审判,而你唯一能拥有的就是其他人对你的感受与感激。
后来这几个字印在封套上,成为唱片文案的主轴,〈掌声响起〉也变成了这张专辑理所当然的「主打歌」,更在很多年后,成为凤飞飞演唱生涯的代表性经典作品,甚至成为她的演艺人生的写照,甚或是一个贴切的「象徵」,这是我刚刚接触这首歌时不能想像的事…。
在那个录音室的夜晚,凤飞飞已经成功「收伏」桀骜不驯的年轻的我,我变得心甘情愿为她工作。但接下来的工作却很不如意,我提出的各种行销想法,即使都已经得到凤飞飞的认同(这件事已不容易,因为凤飞飞是小心谨慎的人,每个构想她都要反覆推敲),似乎也很难得到唱片公司的支持。
唱片公司仍然要用同样老掉牙的方式做唱片封面,唱片公司也不愿为专辑的宣传提供任何资源或预算,唱片公司与艺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难以言诠的紧张关系。
一开始我对这个处境有点困惑,很快的我也察觉其中的端倪。当时凤飞飞与唱片公司的合约即将要到期了,唱片公司也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得到凤飞飞的下一个合约;唱片公司似乎「铁了心肠」,不想在这张新专辑提供任何的力气,他们为什麼要提供资源协助凤飞飞「转型」?如果此举增加了凤飞飞的声誉,不但增添续约的困难,也是为下一个唱片公司提供了助益,他们为什麼要帮助未来的竞争者呢? 每次我的意见被公司打了回票,下次见面时凤飞飞就充满歉意地看著我,安慰我说:「宏志,没关系,我们不要泄气,再找一些我们能做的事。
」她已经改口叫我名字,不再是有著礼貌距离的「詹先生」;我心里也完全站到她这边,我并不痛惜这些创意被埋没,我只是为凤飞飞所受的待遇感到十分不平。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专辑唱片出版在即,我仍然一事无成,没有一项构想能够付诸实现。凤飞飞与唱片公司的冲突也日益激烈,好几次她也动了肝火,但她只要看到为她工作的人,包括制作人和我,她的态度总是转为和缓,反过来安慰我们,她似乎是不愿我们卷入她的冲突,也不希望我们不开心。
终於到了专辑推出的时候,很出我意外的,唱片公司倒是同意我为凤飞飞开一场「发片记者会」的计划。 既然这是唯一能做的事,我把所有的力气拿来撰写预备在记者会上使用的「新闻资料」。
我想要寻找一种简易可解的语言,说出凤飞飞对我、对我们这个世代、对台湾的意义。最后我写下来的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台湾人心目中的台湾,可能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 如今回头看去,我几乎要谴责自己的词穷和笨拙。我有点找到了意义,也就承认凤飞飞已经形成台湾文化经验的一种内容,这不是唱了几首受欢迎的流行歌而已,她用她的「台味国语」为台湾找到一个推翻樊篱的经验,她更用她的力争上游的奋斗塑造了一个自然亲切又有代表性的「台湾形象」…。
虽然这句话不准确也不充分,但好像凤飞飞是深受震动。也难怪,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事,凤飞飞的歌唱表演还未受到「知识界」的重视,台湾的自我追寻在民主政治运动与高层文化论述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文化反省的范围还未及於像凤飞飞这样的艺人,她是受忽视也受鄙视太久了,我写的文字虽然笨拙,却也率先给了她一点「公道」,她是有感受的。
等到再过五年、十年,林强、黑名单工作室、陈明章陆续出现,「台味」不再是低俗的描述语,而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宣示,再等待伍佰登场,「台式摇滚」甚至可以转为一种骄傲,凤飞飞的意义就不必有人用这样委婉的方式来说,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说凤飞飞对这段文字是有感受的,证据是这段文字后来流传很广,很多讨论凤飞飞的文章都引述了这段话,并且说是「评论家詹宏志」说的。可是当年这段文字是写在没有署名的「新闻资料」里头,为什麼大家都说这段话是「詹宏志」说的?我猜想是后来记者和研究者访问她时,她出示这些文字(记得我前面说她什麼剪报和宣传资料都保存良好吗),并且告诉他们:「那是詹宏志写的呀!
」 回到一九八六年这张专辑出版之时,我受凤飞飞之邀参加了企划工作,但我的工作一事无成,唱片出版后销售也平平(〈掌声响起〉后来成为经典,是时光汰选的自然结果,和任何宣传行销都没有关系);凤飞飞似乎有点心灰意冷,她回去香港蛰伏一段时间,她再也没有和歌林唱片公司合作…。
虽然我说过我不要唱片公司的酬劳,但凤飞飞事先没告诉我,还是跑去向公司争取了一笔酬劳,她亲手把钱交给我时,充满歉意说:「实在对不起,钱太少了,我太任性,勉强把你找来,花了你那麼多时间。
」 「不,我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才是那个应该充满谢意和歉意的人。 唱片出版一个月后,我的小孩出生,凤飞飞又不由分说坚持亲自送来一个金锁片。再后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也许只在公开场合见了一、二次面,她总是要谢谢我当时为她工作的事;她开演唱会时,还托人带话来:「要不要来听演唱会,我会把票送去给你…。
」 我没有一次能够成行,最后一次她开演唱会,我心里念著想要去买票,当然也没有积极行动。
她的演唱会突然因为「喉咙不舒适」临时取消,我心里觉得有点不祥,等到新的消息传来,那已经是惊天动地的恶耗了。 一个本来有著若干文化傲慢的年轻人,在凤飞飞意外带来的奇缘之中,看见我不曾看过的真诚力量,也让我更加体会这些各式各样的不凡人物,才是「台湾」的真实内涵;我没有机会为她的生涯转型提供任何的贡献,她却以平实自然的笑容,结结实实为我上了一课。(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