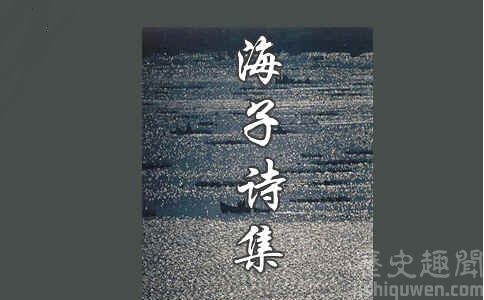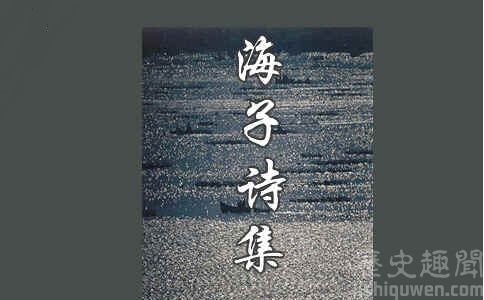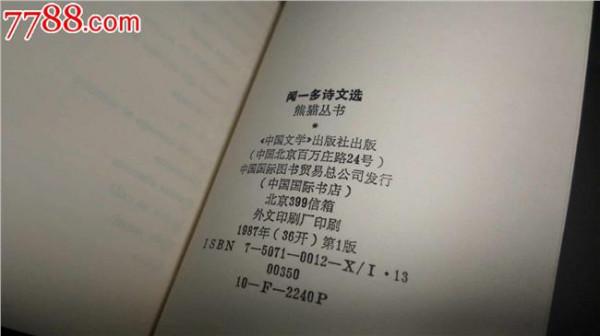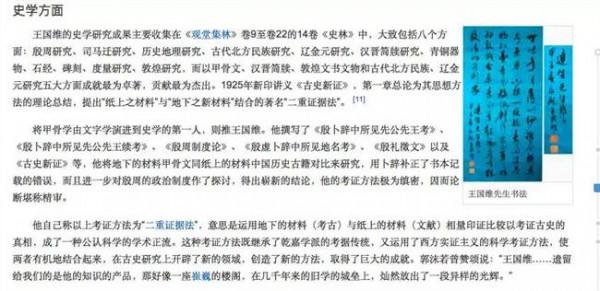刘小枫:诗人自杀的意义
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一开首就说:真正严重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一般人的自杀可以说是人向暧昧的世界的无意义性边界所发起的一次最后冲击。既然生没有意义,那么,主动选择的死就是有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毕竟维护了某种信念的价值。但是,诗人的自杀却是对这种最后发动的冲击的否定。通常的自杀是依据于某种信念,它认为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诗人的自杀却不依据于某种信念,否则他就不会自杀。因而,诗人的自杀不再是依据某种信念所发起的最后冲击,而是因对信念的彻底绝望而发出的“求援的呼吁”。
自古以来,自杀就成为人向暧昧的世界发起最后冲击的本钱。在与世界的赌博中,人仿佛能骄傲地高喊:活着没有意义,死总是有意义的。似乎这样一来,人就超出了动物的受动状态。
自杀的能力证明,唯有人才是万能的。因为神想自杀却无法办到。人能自杀,是神给予人的最大恩赐。
这种能力到后来被演绎成了人的意志力的最高表现。
这就是人的自决能力的顶峰,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理性的自杀”。意志力所依据的信念把意志自身推到极端,而这一极端(自杀)反过来也把信念推到了极端。信念成了自杀的根据和目的。事实上,正是信念为了个体的人提供了世界的某种价值意义。这些意义和价值的体系最终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的意义。信念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总是具体地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态度。
人类的信念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提出来的,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抛弃和变更的,中西方都有自己的最基本的信念,这就是儒家的天道观念与道家的超脱观念,注重知识和理性的Hellenism(希腊精神)和注重救赎的Hebraism(犹太——基督教精神)。
从此,有自我意识的人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
世界的意义在于绝对的形而上学之道,凡用国家、道德、仁义等形而下的仅有相对意义的形态来侮辱绝对意义的形态,都是不可容忍的。他们的信念已经把意志力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为了自己的信念敢于否定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这种本质关联有为另一个与此对立的现象多少抵消了,这就是与自杀相对立的行为:杀人。
人类的文明,无可否认地是伴随着自杀和杀人的历史成长起来的。历史理性主义以历史发展不可避免血和火为理由(这种理由当然值得审查),把“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轻而易举地就一笔勾销了。好像人类历史的进步完全有理由以二律背反为代价。科学理性和技术文明的进步也并没有消除甚至减少这一现象。相反,文明越发展,自杀的枪声越频繁,杀人的技巧也越精明。
在这两个不同的文明世界中,自杀和杀人都曾发展到自己的顶点:根据信念理性地自杀,根据信念合理地杀人。这不仅逼迫现代人承认,人性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改善多少,在人的天性中仍然还有一个黑暗的罪恶的渊薮;而且迫使我们怀疑,所有现存的信念——传统的也好,衍生的也好——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绝对可靠的。
在这种普遍的怀疑精神中,诗人自杀了。诗人死于对信念的彻底绝望。
于是,虚无信念在诗人中理直气壮地产生了,它以敢于荒诞和拒绝任何价值真实的新的信念来作为拒绝自杀的理由。
但实际上,虚无信念不仅不能挽救诗人于自杀的境地,相反却使诗人更加陷入绝境。诗人正是死于信念的毁灭,彻底的价值虚无当然不是问题的解决。
自西方在十九世纪进入全面的科学化的时代之后,对自杀现象开始了超价值判断的“客观的”科学研究。最突出的方法就是精神病学和实证社会学的探讨。
精神病学家把自杀归结为精神反常,归结为精神分裂的冲动。这种对自杀问题的彻底了结等于什么也没有解决。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精神分裂。
实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自杀:社会学探讨》一书,曾名噪一时。从而,研究自杀,重要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个人,他的动机和思想,而是影响自杀的百分比发生变化的那些不同的社会环境状况。
按杜尔克姆的见解,自杀行为从实质上说是个人根据社会的文化要求和规范、人类生活及其价值方面的观念而作出的一种故意的自觉行为。
随着这种实证定量分析的合理化,关于世界中事物和事件的意义问题被排除在外了。
根据古希腊宗教传统和犹太——基督精神传统,现世形态的世界本身没有意义可言。意义仅存在于一个柏拉图式的本质领域之中,存在于上帝的神圣存在的怀抱。
但是,人活在现世形态的世界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域或上帝提供的乐园之中。现世生活的嗜欲使人离开了本质之域,人的妄自尊大使人背离了上帝,现世的放任生活是以人背弃价值本源为代价的。同时,人又不能忍受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现实世界中存活,向现世世界索取意义就成了人的本质冲动。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现世世界中没有意义可言,不得不在这世界中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义。自杀因此而产生。自杀者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悖论。
超脱主义哲学力图通过取消人们向现世世界索求意义的本质冲动来解决这一悖论。庄子哲学和东方佛学都有这种意图。
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世界的虚无恰恰应该是被否定的对象。必须使虚无的现世世界充满意义。这正是诗存在的意义,正是诗人存在使命。诗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他必须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
诗的语言使生存的世界中的语言发生了一场翻转,从而把人引入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之中,使个体从日常的现世世界的虚空中进入充满着意义、恩典、温暖的现时状态。
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
诗的这一切成就必得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我们确实肯定有绝对价值的存在,二是诗人确实对这些绝对价值具有某种忠诚的信念。
当代俄罗斯杰出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沉痛地回忆到二十年代以来自杀的几位一流俄罗斯诗人时说,他们“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了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自杀表明他自己与自己过去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了。
既然没有神圣的绝对价值来源,总得找出新的观念来取代被摧毁的价值。废黜了思辨理性,也许历史理性是最好的替代品。于是,历史规律成为哦哦了绝对的价值真实,在历史规律之外,没有永恒的真理、正义、爱,所有价值都不过是历史的环境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是绝对价值本身。
历史规律是绝对的,真理和价值是相对的。没有任何真理和价值能够逃避历史的条件,当然也就消除了超历史的真理和价值的存在。否弃了超绝神圣的永恒的超历史的真实性,否弃了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永恒的超历史的本源,人们就再也找不到真理和尺规去据以判断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所提出的相对的价值和真理。历史说明一切,证明一切。历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性可以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地踩碎每一颗柔弱的心灵。
在价值的彻底毁灭中,诗人内心被一种巨大的苦恼所纠缠,这就是克尔凯戈尔所说的绝望感。
但是,绝望感不等于厌世感或虚无感。绝望感坚持价值的真实的意义,它像是对仿佛永远不要想得到任何解答的问题的追问,这就是对世界的无意义性的永远不可能消解的焦虑和操心。
自杀的诗人究竟对哪些价值和意义真实产生了怀疑?
屈原曾有很高的人生抱负和人格理性。他的价值信念首先在于个体的道德人格和情操的完善。
另一方面,这种道德人格的完美理性又是与历史形态中的国家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体人格的完满实现在屈原看来只能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完成。
从理论上讲,个体人格理性(善)超逾于国家的历史意识形态之上,它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价值。历史形态中的国家却并非必然体现了正义和完善。把个体人格理想盲目投注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把国家形态偷换到绝对价值的地位。然而,历史形态中的国阿吉真的具有绝对的价值意义吗?屈原的自杀尖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法国作家马尔罗说过:“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同样,诗人可以接受绝望感,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绝望感是一种确证,它提供给诗人一种景观,排除盲目、偏狭、迷拜和无意义的牺牲,赖此确立真实的信仰。
没有出路的情形只有三条退路:自杀或发疯,是第一条退路。所有真诚的诗人为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二条退路就是杀人。用钢铁的武器可以杀人,用精神的武器可以杀人。种种欺骗人的话也是暴力压迫。第三条路退路就是麻木或沉醉。
节录于《拯救与逍遥》 刘小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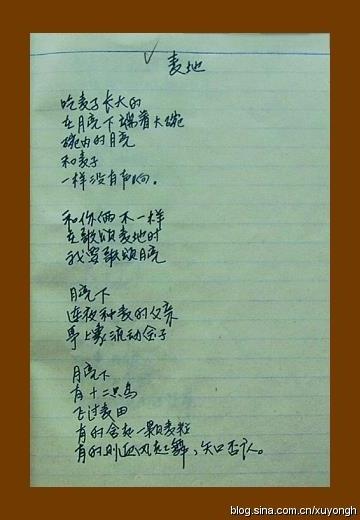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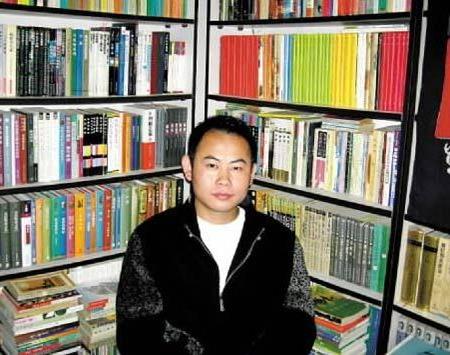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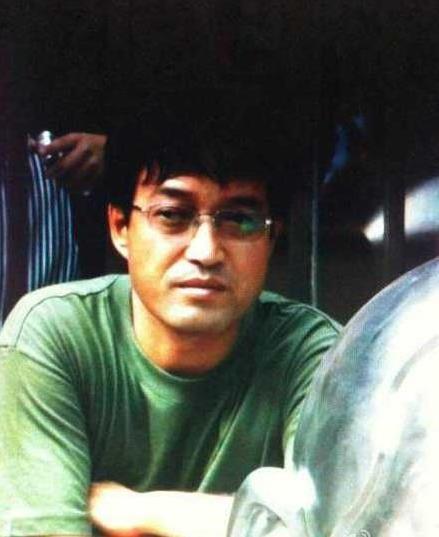






![朱湘图片 诗人朱湘之死:投河自尽[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0/e1/0e1f1fad5f2b19c3802917761e8d79d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