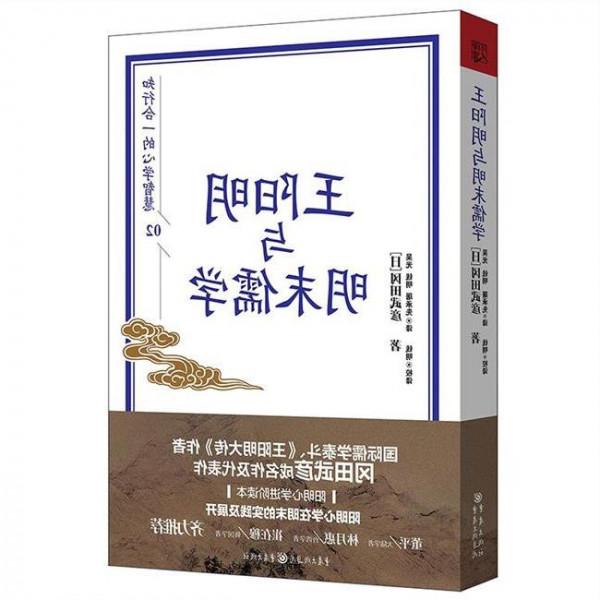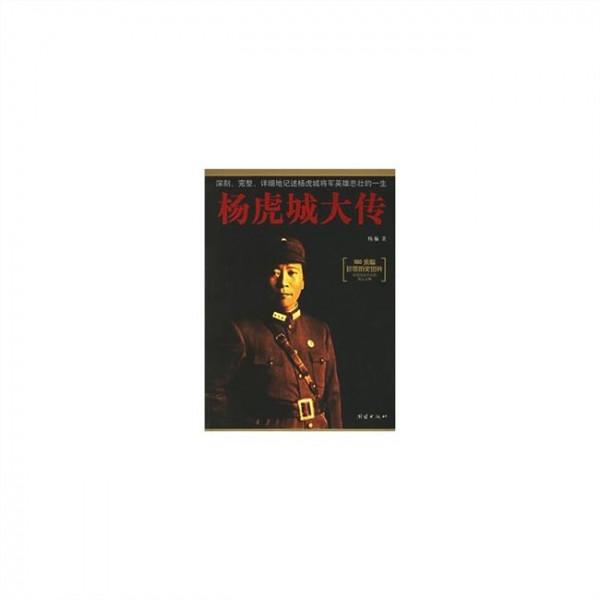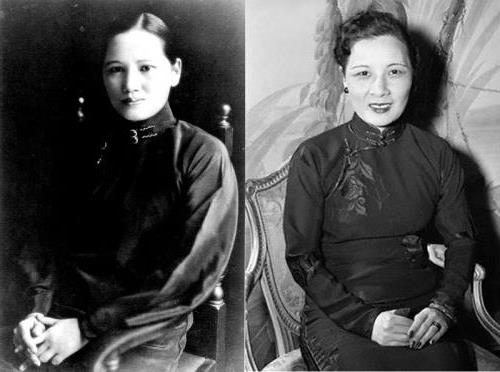陈布雷自述 《陈布雷大传》:陈布雷自杀前前后后
本书作者从陈布雷亲属捐献给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的20本、150万字的亲笔日记中获得第一手史料,详细记述了作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内心的矛盾、痛苦与思索,披露了陈布雷自杀身亡的原因。
沉浮政海二十余年 陈布雷如果没有跟上蒋介石当幕僚,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更大的可能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目。
可是他却偏偏走上了跟蒋的道路。 陈布雷是1927年春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蒋介石当时迫切希望有一幕僚长,会动动笔头,出出主意,又要有文采。
不是说没有其他文人可以供他选择,但是要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而且温和谦恭,毫无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确实不多。这是蒋介石将陈布雷倚为左右手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陈布雷是恩宠有加,使陈布雷感激涕零。
陈布雷对蒋介石并不是没有看法的,但是他始终不愿也不敢背叛这个“主人”。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是两个阶段。
1927年到1934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蒋介石要重用陈布雷,但陈布雷不愿当官,所以并不都在蒋的身边。蒋介石有重要事情,才把陈布雷叫来,所以当时有人一看到陈布雷动身到南京去,就说:“政局将有变动,一定又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了。
”第二阶段是1934年到1948年,这一时期,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陈布雷当上了侍从室二处主任,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后来侍从室撤销了,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文字上出谋、执笔,一直到死去。
陈布雷曾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的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2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
第二天,两人一同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很恭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
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此后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见状问道:“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
”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道:“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告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
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交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编写《西安半月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南京没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
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其间蒋介石曾去奉化溪口、杭州休养,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他叫陈布雷一直跟着他。
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
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
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重望。
”其实,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已经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蒋介石道:“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但写了不久,陈布雷感到心中很烦,写不下去了。一方面是来客太多,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他委实也编不下去了。
有一天蒋介石把他叫去坟庄,问:“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欠身子道:“这样吧,你到杭州去吧,到里西湖新新旅馆开一间房间,安安静静写吧!” 陈布雷于是到了杭州。
在新新旅馆的一间房间内,写字台上摊满了稿纸,有许多已团成一团。温文尔雅的陈布雷,一反常态,把狼毫笔在墨盒里乱戳,猛地戳断了一枝笔头,夫人王允默又递给他一枝,陈布雷蘸了蘸墨汁,在纸上又涂了起来,一会儿又把纸捏成一团,掷笔长叹一声。
站起身来,在房子内来回踱步,浓眉紧锁,脚步声也特别响。王允默婉言相劝,叫他慢慢写,可是陈布雷忽然大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 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布雷的亲妹子来,说:“你哥哥这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
我讲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比较肯听。”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
她说:“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妹妹的口气很温和。 “出去!你们统统出去!
”一向性情温厚的陈布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火,要伤身体的。” “唉!
你们懂什么,”陈布雷拿起笔,他愤愤地说:“叫我这样写,怎能不动肝火!”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把一枝毛笔头折断了。 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西安半月记》交了出去。
不过,他在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段话:“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自从跟了蒋介石近20年来,陈布雷就把自己和一支笔缚在蒋的幕帷之中。
人们一会儿把他比作蒋介石的“文胆”,一会儿又把他誉为“总裁的智囊”。
蒋介石的重要言论、文章,确实原原本本都在陈布雷的笔下泻了出来;可是陈布雷心中却有一腔苦水,满腹难言之隐。“为别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陈布雷好几次对他的知友、妹夫,侍从室秘书翁祖望说过:“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由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为他人之一体。
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为人捉刀是苦恼的。”“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陈布雷也多次向身边人诉说过内心的苦衷。有几次为蒋介石撰写文稿,被蒋介石删改得面目全非。清清爽爽的一份文稿,弄成像东一堆、西一块的三色拼盘,还要陈布雷作第二次第三次修改……“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这是陈布雷最大的苦恼。
21岁即为孙中山文稿翻译的陈布雷,对于上海棋盘街那段报人生活,一直难以忘怀;对于在宁波西门效实中学那一段育人子弟的教书生涯也有余恋。他有一次对翁泽永说:“啊,倘若让我重返报界那该多好!
”可是才思横溢的幕僚长,下笔如神的“文胆”,是蒋介石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他了解的机密也太多了,他已不能自拔了。 可厌的文笔事务和尖锐的内心烦躁,把陈布雷折磨得心力交瘁,忧愤不堪。
他觉得隐逸才是惟一的出路。陈布雷刚到南京,房子还未找到,夫人王允默只好住在上海。每两三个月,陈布雷赴沪一次;周六午后搭车去沪,周一返京,携一副官同行;两人车费,不报公账,后来通货膨胀,钞票贬值,车费狂涨,陈布雷只好一个人去,不带副官,以节省开支。
他在上海寓所对王允默说:“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夫人,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
” 他动用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买了一块田地。但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不曾作过他的退隐之处,却是作了他最后的归宿之所。
心力憔悴 蒋介石的幕僚和侍从大多是浙江人。这些幕僚差不多都穿着呢子和哗叽的西装和中山装,要不就是军装,只有陈布雷是例外,一身布料长衫,一介寒儒,一副落拓不羁的模样。
1948年11月11日,陈布雷穿的是一件马裤呢的长衫,这件棕黑色的长衫,裹着他骨瘦如柴的伛偻的身躯,越发显得矮小干瘪了。
当晚,他在南京湖南路私邸的卧室中来回踱着方步,脚步轻微得听不出来,一桌子香烟蒂头,他手指中还夹着一枝正在燃着的香烟。他不断地咳嗽,已经是初冬了,但是他黄瘪的脸上汗珠直冒。他心中在剧烈翻腾,他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离开这个生活了59年的人世间了。
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淮海战役序幕刚揭开,蒋家王朝即将崩溃。陈布雷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他比别的人更明白这个大势。
就在3天前,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他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一听,感觉不妥,当天他在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发火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至少在陈布雷面前蒋从来没有发过脾气。陈布雷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
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
”陈布雷惊呆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遭到蒋介石这样对待过。当时,他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退出了会场。 次日下午,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来访,劝陈布雷要“想得开一点”。
过了一会儿吴国桢又来访,待客人告辞后,陈布雷对陶副官说:“我要理一个发。”理完发后,即吩咐陶说:“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
”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当晚,陈布雷写完给蒋介石的上书,又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留下了一封封遗书。
然后,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让我安静些!”这是陈布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陈布雷大传》王泰栋编著 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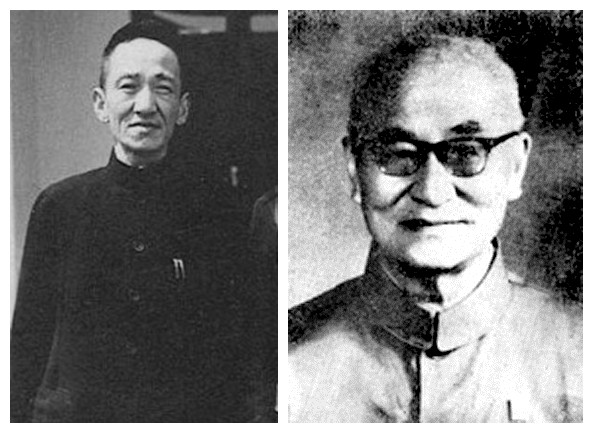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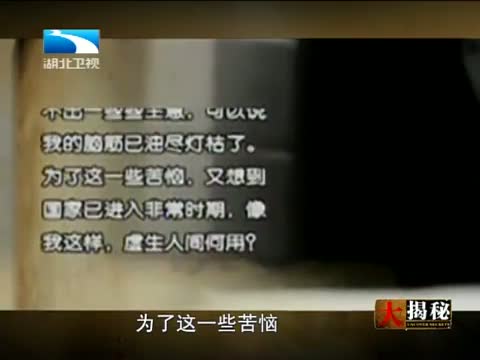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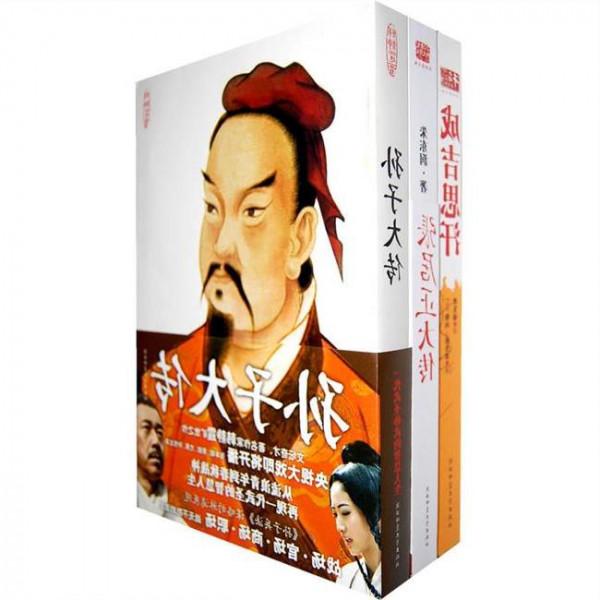
![王阳明心学智慧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三册)[当当]](https://pic.bilezu.com/upload/c/75/c753a16bd3ff1be068f61ad7ff19b2f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