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李流 李富春独生女李特特 “化缘”度晚年
她生活在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外婆当年裹着小脚赴法留学;三位亲人先后惨遭杀害;妈妈为了革命,在生她的产床上做了绝育手术——这样的家庭,影响了她的一生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 畅
北京木樨地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女李特特,已经在此生活了几十载。
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请叫我‘特特同志’吧,我最喜欢这个称呼,志同道合的朋友。”李特特坚持让记者这样称呼她。
今年已84岁的李特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洋气、率真。鲜红色熨烫平整的衬衣,配一条黑色短裙,白色的羊绒外套,典型一个干练的“女白领”。
李特特说自己退休后“累得要命”。她从写字台前翻出一堆电话簿,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家庭电话。
“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说到这里,李特特突然皱起眉头,“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随着岁月沉甸甸的积累,带着对现实生活的冲劲,李特特和记者谈了4个多小时。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成天求爷爷告奶奶”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之所以叫“终身”,是因为“这项工作老也做不完”,她已经整整干了20年。
“总生气”、“总受骗”、“总着急”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忙的时候,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和其他扶贫人员不同,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头头脑脑们,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李特特有一本随身不离的大相册,里面全是贫困地区百姓的生活景象:村民家里渔网般破旧不堪的被子,黄土高坡寸草不生的凄凉景象,孩子们可怜巴巴的眼神……李特特找到可以“化缘”的领导后,就把这些照片拿给他们看,向他们讲述穷困地方的苦,然后要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每到一个大机关,每见到原来家里的朋友,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大小官员们诉苦,惹得一些人都烦了。”
李特特露出一脸的无奈:“还有那些老板,你向他们要钱可真是跑断腿、磨破嘴。看他脸色,坐冷板凳,听冷言冷语。十有八九他们都不给,就是给了,马上也要向我提这条件、那条件的。有的要我帮忙搞批文,有的要我引荐某个大人物给他们认识。”不仅如此,李特特有时候好不容易要来的钱,在落实上又出问题。“有些县政府说好了拿到钱盖一个多大面积的厂房,一年后你再去看,结果只盖了个破棚子,钱塞进自己腰包了。”李特特急了:“他们就是看我一个小老太婆好欺负,好骗。我现在可有经验了,落实一步给一步的钱,究竟多少预算,我心里早有算盘。”
即便如此,李特特这个高干出身却见人就“化缘”的毛病,还是让许多人对她敬而远之,甚至风言风语。有人说:“老人家年事已高,脑子可能糊涂了。本来,她一个人,国家又给她配了个保姆,住着宽敞的三居室,别说安度晚年,就是游山玩水,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可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
“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李特特刚离休时,曾有企业看中她特殊的家庭背景,想聘她为“名誉董事长”,但被她拒绝了。她坚持要“化缘度晚年”。“我的外婆葛健豪,培养出那么多优秀革命子女,当年她在当地的县里创办女中时,也是拉着我走街串巷,求爷爷、告奶奶地‘化缘’要钱。”
李特特似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外婆的影子。“我现在继承了外婆做的事,成天也求爷爷、告奶奶的。小平同志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很多人当口号听,我是革命家的后代,父辈们未完的事业我要继续,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外婆对她影响至深
在李特特的一生中,外婆葛健豪对她影响至深。
“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她16岁结婚,生了三儿两女,其中舅舅蔡和森、妈妈蔡畅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革命家。我外公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外婆对他十分失望,一心只想将儿女培养成才。她50岁时卖掉了娘家陪送的嫁妆,凑足学费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之后又一起去法国留学,成了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太。”李特特笑得合不拢嘴,“毛主席叫她‘大家长’,因为她先后带出了4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特特兴致勃勃地给记者讲述了外婆的传奇家世:“我外婆是湖南双峰县荷叶乡桂林堂人。她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我外婆家里的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乡的最上层。”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而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又与葛健豪家相隔不远。听说秋瑾是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葛健豪常去拜访。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外婆常给家人讲秋瑾的故事,称赞她创办女学唤醒了妇女的觉悟,称她是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舅舅和妈妈也是从外婆的嘴里第一次知道了‘革命’这个词。”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噩耗传来,葛健豪非常悲痛。从此,她不断鼓励儿女要像秋瑾一样做人。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形成高潮。葛健豪利用与曾国藩外孙的亲戚关系,借来600元银元,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她都50多岁了,硬是跟着年轻学生啃法文,经常问得舅舅不耐烦,又去找妈妈,妈妈厌倦了,再去找舅母。外婆最后甚至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不仅如此,葛健豪每晚还带着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她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甚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供全家勤工俭学。
李特特对外婆的感情甚至超过了母亲,因为她的生命几乎是外婆给的。1923年,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为了革命,妈妈坚决要做人工流产,虽然法国的法律禁止堕胎,但她仍不放弃。但外婆极力反对,甚至说她宁愿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女。后来,母亲才同意生下我。革命意志坚决的母亲,在产床上便做了绝育手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生命,李富春夫妇为女儿取名“特特”。
葛健豪从此更忙碌了:做工养家,吃力求学,参加革命,还要抚养外孙女。这个三寸金莲的小脚老太太,硬是挺了过来,直到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李特特辗转归国。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革命家的后代”带给她无数的光环,也让她失去了常人最平凡的母爱。
1928年李特特4岁时,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也是李特特记忆中,全家唯一的一次大团圆。
“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一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每次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正当蔡畅一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艰难斗争时,他们突然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外婆最伤心,几天没吃饭。她最喜欢舅母,常说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一年后,舅舅再婚,外婆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葛健豪走后,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我总是被他们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战争让她成为“轻机关枪手”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
“我感觉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其他一些国际儿童院里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这意味着,她将随时被派往前线。
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我护理过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在零下40℃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在大学,她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寄托。24岁时,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件本该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得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看淡人生起落悲欢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回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李特特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反而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来到北大荒开荒,一呆就是3年。“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各种压力的包围下,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对于这段婚姻,李特特认为很平凡,不愿多谈。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她对记者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
李特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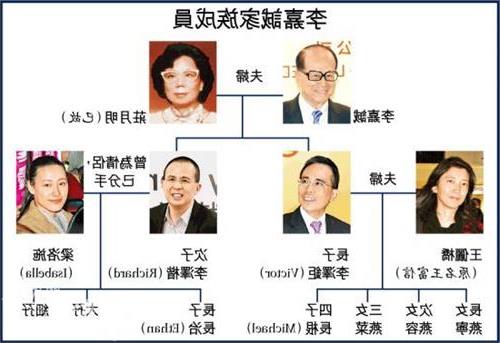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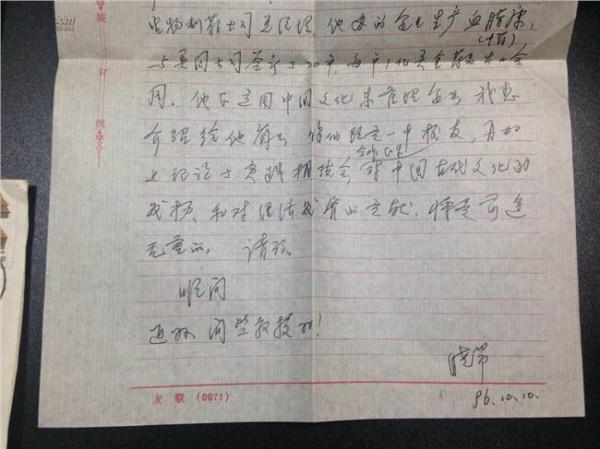




![>吕一杰图片 [图文]吕一杰和李嘉李有没有交往||吕一杰女朋友](https://pic.bilezu.com/upload/f/9c/f9c5eafcee8de584562d89b9a6f4cb9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