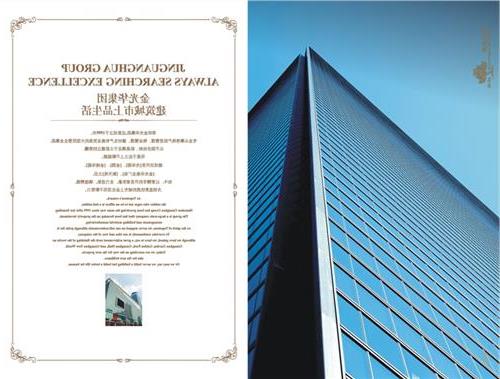【闲话红楼十年砍柴】十年砍柴:俺自产自销的《闲话红楼》
《闲话红楼》:大观园中的奴才是怎样炼成的
著名网络作家十年砍柴继《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之后,在语文出版社推出蜕变之作《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十年砍柴保持了一贯的“砍”风,来自现代眼光的观照,对国民奴性揭示,嬉笑怒骂的笔触以及无处不在的冷幽默,让一部言情说史的《红楼梦》成为了批判国民性的浮世绘。日前,记者专访了十年砍柴。

四大名著的文化基因活在当下
十年砍柴2004年推出的《闲看水浒》,在文化领域影响较大,尔后他的兴趣转向明史,还同时在多家报纸开辟时评专栏。《闲话红楼》的出版,是否意味着他的兴趣又回到了古典小说?“其实这些年来兴趣一直没变,就是寻求中国社会演进的因缘与脉络,我们民族的这个庞大躯体中间,一定有某种基因在起作用。”十年砍柴表示,读史之后,对现实的观察更加深入,更容易穿过表面的皮毛看到内核。

十年砍柴一直把四大古典小说和“三言二拍”、《金瓶梅》、《儒林外史》当成历史来看,和明清两代的史料对照互校。他认为,《红楼梦》描写的是中国传统家庭和家族的生活,宗法秩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架,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家族,无法了解中国传统社会。“这四大小说,分别侧重中国的庙堂、江湖、想象的天国和家族,可以说四大古典名著高度浓缩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且这种文化基因还顽强地活在当下。”

自产自销《闲话红楼》
据十年砍柴介绍,《闲话红楼》的书稿,五年前就已写成。2004年,《闲看水浒》畅销,开始为报社写关于看红楼梦的专栏。按一般逻辑,肯定是趁热打铁,再结集出版。就在2005年底,一本书让他产生了迟疑。“我看到民国时期大学者萨孟武的著作,岳麓书社80年代出版的,用政治学的方法论分析《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看完后我有些汗颜,觉得自己自以为不错的见解,前辈在40年代已经撰文写过了。

”他在自豪和前辈学人有观点暗合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思想资源,究竟比前辈多了多少,又先进了多少。
“因此,我想把闲话红楼的专栏文章闲隔下来,不急于出书。冷却一下,看几年后是否还有价值。” 2008年年底,十年砍柴告别了记者生涯,调入语文出版社,过上了读书、写书、编书、卖书的“四书”生涯,《闲话红楼》也得以面世。
“一个人最难突破的是自己,从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观察和分析而言,《闲看水浒》中,主要分析在逃离主流社会的边缘人,以及他们的游戏规则,而在《闲话红楼》中,我分析的是在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秩序下,主子和奴才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生逻辑。”十年砍柴说。
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
“在《闲话红楼》的封面,我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鲁迅说中国人只有两种生活状态:‘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当然是先生文学性的语言,不无夸张,但却相当有道理。中国古代是臣民社会,臣民社会的是礼法秩序主导。”十年砍柴这样阐释书名的由来。
在该书第二章“奴才是这样炼成的”中,十年砍柴把大观园中可怜、可悲、可叹、可敬的奴才们细细论说了一番。“《红楼》的奴才实在太多,我只能按失败的奴才、成功的奴才,大奴才、小奴才,自愿为奴而不甘为奴等等加以区分。
” 恃功自傲的焦大被主子灌了一嘴马粪,没有自知之明的李嬷嬤落得自取其辱;与此相对的是巧言令色的赖嬷嬷和赵嬷嬷。她们是成功的乖奴才典范。“自由的精神,独立的生活,是需要一种合适的土壤承载的。宝、黛那个时代显然没有这样的土壤。
我看《红楼梦》,为宝黛爱情悲剧而伤心,更为他俩所在的那块土壤而伤心。在《闲看水浒》的前言中,我说过要‘告别梁山’。我也希望中国人能告别大观园。只有大观园外,不再是梁山水泊的秩序和规则,贾宝玉和林黛玉才能率领那些可爱的男女,走出大观园,而不至于被吞噬。”十年砍柴这样告诉记者。
把《红楼梦》当成职场小说看
“完全可以把《红楼梦》当成职场小说来看。”十年砍柴举例说,贾府大家族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在博弈,在暗中较量。“像王熙凤这样的人,那确实每天睡觉都要睁一只眼。为什么贾母那么厉害?她就是从王熙凤那个地方走出来的,或者她教育过王熙凤,教育过王夫人,而且跟她的孙媳妇也这么说过。
”“要公公婆婆不要生气,老公还要宠爱自己,还要防着老公在外面有别的人,还要孩子不要学坏,还有你是掌房的,你要跟老二、老三要和谐。”十年砍柴眼中,当长媳的就像政治家,各个关系都要平衡。
《红楼梦》中所有的人都在找自己的生存方式,黛玉有黛玉的生存之道,宝钗有宝钗的生存方式,怎样的方式是最好的,没有答案。“‘人之砒霜我之良,砒霜有毒,但是有的人有的病还是要用那个砒霜,因为那种方式、模式对他会很合适。”十年砍柴说。
2008某天我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充当嘉宾。那一期的话题是少年儿童要不要读《三国演义》。我认为 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讲到四大古典名著的比较,我当时说,只有《红楼梦》具有现代性。 何谓现代性?显然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
美国在建国时,尽管没有今天这样的高科技,蒸汽机还未普遍使用,但这个国家一诞生就具备现代性;同理,有飞机大炮火车互 联网的社会不一定就是现代性。就文学作品而言,所反映的现代性,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对普通人的命运要有大悲悯,尊重普通人的尊严和自 由。
《三国》里多讲权谋,价值取向乃是尊刘抑曹、汉贼不两立这样的宏大叙事;《水浒》中讲造反,讲招安,《西游》借神佛世界展示官场的规则。
这三部小说固 然各有各的精彩,有好的故事,有很好的人物形象,但和《红楼》相比,就是没有对生命特别是卑微者生命的尊重,在前三部小说里,普通兵卒、小喽罗、小妖怪 的生命犹如草芥,只是大人物斗法的垫脚石。
尤其是女性,在《三国》、《水浒》两部书里,几乎没有做人的资格。 《红楼梦》里的人,特别是当奴仆的小人物,活得也不好,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忍受各种耻辱,但各色小人物,不像前三部小说那样,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各有各的 性格,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曹公是以尊重、理解的情怀来写这些小人物的,心比天高,不甘于当奴才的晴雯固然值得尊重,但适应环境游刃有余的标准丫鬟袭人也并 不讨厌。甚至赵姨娘、王善保家的等中年女人,属于宝玉超级讨厌的类型,其可叹可悲可怜亦有缘由。
可以说,《红楼梦》中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尊重。 宝玉、黛玉作为《红楼梦》的男一号、女一号,在这部书里,他们是“大人物”。但这样侯门的金枝玉叶,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史中,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挣脱不了大时代的枷锁。
宝、黛之所以能心心相印,这对恋人为什么那样可爱,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灵魂是自由的,他们珍惜自己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不愿意受到俗世规则的羁绊, 他们也尊重所有人的人格。
宝玉眼里,没有主子和奴仆之分,只有可爱不可爱之分;宝钗八面玲珑,下人喜其宽厚,但这是她处世之术,她心中主仆畛域分明,一 点也不能僭越。黛玉看起来刻薄多疑,但她待人不重其身份而重和自己是否志趣相投,她对自己的丫鬟紫鹃和薛蟠抢来的妾香菱一片真心。
具有现代人平等意识的宝、黛,如果是今日中产者一员,他们在一个平和开放民主的社会,可以成为一对过着庸常幸福生活的小夫妻。
因为有制度保障了他们自食其 力,独立生活。但在前现代社会,无论他们内心多么独立,精神上何等自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依附于官府,要么依附于家族。宝玉痛恨八股取士,痛恨官场的龌龊,向往纯净自在的生活。然而,他优渥的生活却须臾离不开他所痛恨的东西,贾府的繁荣建立在占有权力的基础上,贾府的衰落是因为权力场上的角斗失败了。
贾府一旦丧失了宝玉、黛玉所不喜的权力,两人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只有一死去,一出家。这是宝、黛的人生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那些精神自由却在现实中无法如愿的先知者的悲剧。
比如明末的李贽,辞官后潜心于学术,可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他再不敢回泉州老家,一生颠沛流离,寄寓在僧寺或朋友家。 有一个和曹公同时代的苏州文人沈三白,写了一本被林语堂赞叹不已的《浮生六记》。
沈三白和他的妻子芸娘相爱相知,犹如贾宝玉和林黛玉。三白和芸娘比宝黛幸运得多,他们得以结缡,并育有儿女,两人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后时光,芸娘曾女扮男装和夫君一起游虎丘。
他们的世界,似乎要比宝黛所在的大观园宽阔得多。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追求自由独立的三白夫妇不容于大家族,几乎是被沈父赶出家门。三白未能入仕,那种性格又不是一个合适的师爷或西宾,最终生活潦倒,芸娘英年早逝。
读《浮生六记》,最震撼我的便是《坎坷记愁》一章。宝玉、黛玉若真能走到一起,建立小家庭,他们还会有年少时“双玉读《西厢》”的快乐么?没有了大家族的庇护,他们的生存状况或许还不如沈三白与芸娘。
自由的精神,独立的生活,是需要一种合适的土壤承载的。宝、黛那个时代显然没有这样的土壤。我看《红楼梦》,为宝黛爱情悲剧而伤心,更为他俩所在的那块土壤而伤心。 至于宝黛之外的那些奴才,他们要追求自由和独立更是痴人说梦了。
焦大这样年老功高的仆人,指责主子也是大逆不道的。晴雯、芳官这样的丫鬟更不能容于大观园。宝玉不能理解姑娘未出嫁冰清玉洁,一出嫁就俗不可耐。这是沉重的生活使然,少女时代暂居在娘家,可以有各种梦想,一旦出嫁就是“归”,归位于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晴雯要生存下去,迟早会变成刘姥姥或周大家的。而男性的奴仆呢?最好的结局是在大观园谋个不错的位置,当个顺奴了却终生。如果连这个愿望都不能满足,那么在贾府衰败时,他们很可能和外面的强盗勾连在一起,打起主子的主意,比如卖了巧儿掳了妙玉。
《红楼梦》中除了薛蟠转述在平安州遇险柳湘莲搭救那一段外,很少直接写到强盗的世界。在大观园内,花红柳绿,俊男靓女徜徉其间吟诗作画,可这个繁华平和的大观园外面,恐怕到处是“平安州”。
所以我说,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连奴才都做不稳的人,他们只能做暴民。奴才没有自由,那么暴民能呢?除了当炮灰的暴民外,成功的暴民当了主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奴役原来的同道者,建造起属于自己的大观园。
从大观园到梁山水泊,便是中国残酷的历史循环。 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是在2005年应某报副刊之邀所写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存在电脑中已四个春秋,其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谈《红楼梦》的书也出了许多,我总觉得自己那些文章过于生涩,不敢结集出版。
2008年年底,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调入语文出版社,终于过上“四书”生涯:即读书、写书、编书、卖书。
本来按照业界潜规则,编辑的书不应在本社出版,以避嫌疑。但承蒙社长王旭明不弃,一再鼓励我将这些文字留在本社出版。我想也算是古代武林里带艺投师吧。如果拙著出版后,没有辱没本社的声名,那将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闲看水浒》的前言中,我说过要“告别梁山”。我也希望中国人能告别大观园。只有大观园外,不再是梁山水泊的秩序和规则,贾宝玉和林黛玉才能率领那些可爱的男女,走出大观园,而不至于被吞噬。
《闲话红楼》出栏记
从春及冬,整整四季十二月,我和大家一起看红楼,话红楼,此时得说声再见了。
当然,我想不必有“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凄楚,因为在一起话红楼总有结束的时候,而各自归家看红楼却永没有结束的时候。
曹雪芹写就《红楼梦》这部不朽的作品二百多年了,他并非是要靠这些文字名闻天下,从而赢得什么肥马轻裘,终其一生,他没有脱离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他生前是潦倒而孤独的,只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创造那么多美丽的生命,如宝玉、黛玉、宝钗、湘云、晴雯等,以抚慰自己。
两百多年来,多少王侯将相、巨贾大儒已在历史的尘埃中湮没不闻,而曹翁笔下那些虚构的人物,却有着比真正历史人物还要强大的生命力。尽管书中的黛玉焚稿断痴情,晴雯也含恨病亡,但在许多读者心目中,这些美丽圣洁生命还活着。当夜深人静之时,如果我们捧一卷《红楼》,对着孤灯独坐,我们似乎会真切地听到,黛玉葬花的歌吟;会看到,湘云醉卧海棠中的娇媚。
在寂寞中死去的曹翁,他创作的《红楼》时,恐怕没想到要给后来一些人提供饭碗,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将曹翁和他的《红楼》存进银行吃利息,甚至在“学术规范”等等的名义下,欲将一部属于全民族的文学作品,当成某种要有入门资格才能研究品读的禁脔。我想,这非曹翁本意,亦非宝哥哥、薛姐姐、林妹妹之意吧。
在和大家一起闲话红楼的时候,窗外有关“主流红学家”和“在野红学家”笔战正酣,如此笔战干曹翁何事,又干红楼诸人物何事?无非是一些靠此吃饭的学者们,自说自话地要代替贾府的管家、仆人,把自己当成大观园的守门人,凭他们的喜好来决定谁能进园子去看看林妹妹或薛姐姐。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许多美奂美仑的园林,如今被人圈起来,以保护的名义向游人收取不菲的门票;如今这座只存在于曹翁笔下的园子,难道也有人想收取门票?
我想自己和许多喜爱《红楼》的人一样,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红学家”,只是因为爱里面一个个美丽年轻、千姿百态的生命,便想亲近他们。我们只就《红楼》的文本发表自己的感想,至于林妹妹和宝姐姐的原型究竟是谁,他们真正的归宿如何,我想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无关紧要。那么就文本发表自己的感想,哪个人又有资格来甄别谁是谁非呢?即使曹翁再世,恐怕也不会做此无聊之事。
那些谁代表正宗红学的争论与我和大多数读者无关,我们只想用心去感受,红楼中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无奈无力,以及青春将逝,繁花落尽的哀愁。
我以为,《红楼》中没有几个特别可恶的人,不用说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就是贾母、王夫人、凤姐这些对丫鬟们命运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也颇有可取之处。但贾府的败亡是一定的,和当家者的见识、能力以及品行没有太大的关系。
即使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给贾府当家,也不能改变“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结局。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少数的有钱阶级不论是土地或流动资产多,不论致富原因是在朝为官或财运特别好,都没有办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多边贸易。政府本身也没有促进投资的收入或服务措施。”这就是黄氏以他的“大历史观”看待中国传统社会的结论,用在看《红楼》也很贴切。
说到底,大观园不是九霄云外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宫玉阙,宝哥哥和一群姐妹们结社饮食,聚会斗酒乃至争风吃醋也罢,他们这些快乐生活的存在必然依靠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大观园本身没有任何抗风险的能力,大观园中的姐妹们那就更是这样了。这个大观园毁灭了,另外的新贵族又在大肆建造另外的大观园,如此循环下去。因此我国百姓,特别有一种“看你起高楼,看你宴宾客,看你楼塌了”的宿命感。
因此,我们关注大观园,我们更关注大观园以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