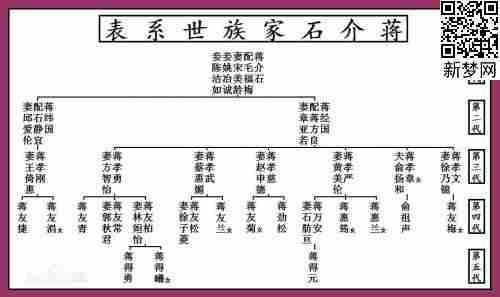【蒋勋的婚姻】蒋勋:好的婚姻关系里 离不开这一点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语言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准度,才能够真正传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与亲近的人,如夫妻之间,所使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语言?
关于夫妻之间的语言,《水浒传》里的“乌龙院”有很生动的描绘。人称“及时雨”的宋江看到路边一个老婆子牵着女儿要卖身葬父,立刻伸出援手,但他不愿趁人之危,娶女孩为妾,老婆子却说非娶不可,两个人推來送去,宋江最后还是接受了。

他买下乌龙院金屋藏娇,偶尔就去陪陪这个叫做阎惜姣的女孩,因为怕人说背后话,常常是偷偷摸摸。阎惜姣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跟了一个糟老头,又怕兮兮的,爱来不来,很不甘心。
一日宋江事忙,派了学生张文远去探视阎惜姣,两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好起來了,变成张文远常常去找阎惜姣。流言传进了宋江的耳朵,打定主意去乌龙院探查。

阎惜姣对宋江是既感恩又憎恨,感恩他出钱葬父,又憎恨大好青春埋在他手里,所以对他说话便不客气。
那天宋江进來时,阎惜姣正在绣花,不理宋江,让宋江很尴尬,不知要做什么,只能在那里走來走去,后來他不得不找话,他就说:“大姐啊,妳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大姐”是夫妻之间的昵称,可是让一个中年男子唤一个小女孩“大姐”,就非常有趣了。)阎惜姣白了他一眼,觉得他很无聊,故意回他:“杯子啊!”宋江说:“明明是鞋子,你怎么说是杯子呢?”阎惜姣看着他:“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要问?”

这部小说就是把语言玩得这么妙。想想看,我们和家人、朋友之间,用了多少像这样的语言?有时候你其实不是想问什么,而是要打破一种孤独感或是冷漠,就会用语言一直讲话。
宋江又问:“大姐,你白天都在做什么?”他当然是在探阎惜姣的口风,阎惜姣回答:“我干什么?我左手拿了一个蒜瓣,右手拿一杯凉水,我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话,阎惜姣要传达的就是“无聊”两字,却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语言拐弯抹角地陈述。

像这样不是很有意义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水浒传》是一本真实的好小说,可是我不敢多看,因为它也是一本很残酷的书,写人性写到血淋淋,不让人有温暖的感觉,是撕开來的、揭发的,它让人看到人性荒凉的极致。
相较之下,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把这种无意义的语言模式诠释得温暖许多。他有一部电影《早安》,剧情就是重复着早安、晚安的问候。
接触过日本文化的朋友就会知道,日本人的敬语、礼数特别多,一见面就要问好,电影里有一个小孩就很纳闷,大人为什么要这么无聊,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事实上,这些礼数敬语建立了一个不可知的人际网路,既不亲,也不疏,而是在亲疏之间的礼节。
但这种感觉蛮孤独的。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于是我们用的语言变得很尴尬。在电影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温暖”,因为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復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水浒传》的乌龙院那段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两者都是无意义语言。我称它为“无意义语言”,是因为拿掉这些语言,并不会改变说话的内容,但是拿掉这些语言后,生命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
《水浒传》是用较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如拿掉吧!最后宋江在乌龙院里杀了阎惜姣,是被逼迫的,使他必须以悲剧的方式,了结这一段无聊的生活、不可能维系的婚姻关系。
而小津安二郎则是让一个男子在火车上爱上一个女子,在剧末他走到她身边,说:“早安!”说完,抬头看天,再说:“天气好啊!”就这样结束,让你觉得无限温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讲。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性,我们常常会觉得文学应该是借语言和文字去传达作者的意思、理想、人生观。是,的确是,但绝不是简单的平铺直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