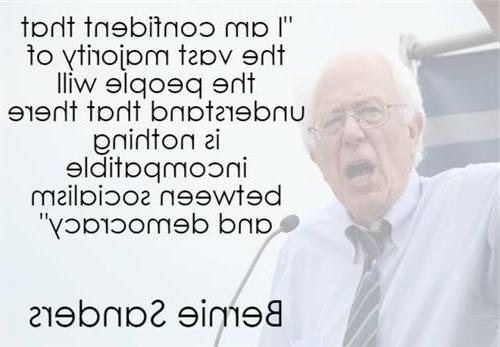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 田国强: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及其有为政府的大辩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大家各自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当下中国经济及其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辩证互动关系,从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即改革何去何从。

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在笔者看来有三:一是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否坚持的问题。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里?三是林毅夫等人所极力推崇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能否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三个问题又都涉及一个更为本质问题,就是:要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改革(从而治理)的逻辑,政府职能的基准定位到底应该是有边界的有限政府,还是无边界的有为政府?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能否长远发展、改革何去何从及如何深化改革,才能让改革成功和经济持续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现代化。

按照中国国学智慧给我们的启迪,要将一件事情做成,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将改革这样决定国势、格局的大事做成,要看行事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明道”、“树势”、“优术”及“择时”这样综合治理的四要素。因此,我们在研究、研判中国改革与发展,让改革或政策或某个制度安排具有可行性,可操作的同时避免大的风险,作为学者在给出政策建议时,需要从道、势、术、时这四个维度进行考察、检验和研判,从而我们必须要做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纵观林、张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一系列辩论和他们以往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尽管他们都有许多合理的、有新意的观点和论断,但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讨论、辩论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导致各说各话,使得对话少有交集、无法聚焦,更无法达成共识和深入下去。
在一些ABC的初级层面上纠缠,没有实质效果,这大大减低了讨论争鸣的效果,真不像是在进行学术讨论,倒好像是在做秀一样。二是,在给出论断的逻辑性、科学性、严谨性及学术性上有较大欠缺,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的观点偏颇、走极端,似乎不知道任何一个理论或论断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适应所有情况、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论断往往有扩大化和夸大的问题存在,显得特别不严谨,而严谨性是严肃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
比如,在这次争论中,一个过度夸大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要建立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另一个过度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和完全否定产业政策,认为市场不会失灵。这样的讨论方式在学术性及其思想性方面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我在此之前和林毅夫教授围绕其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概念进行了几个回合的商榷的时候,对他的一个最大批评就是他的理论及其结论基于一些到现在都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如有为政府这个概念,这样必然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林所采用的概念定义不清晰,边界游移不定,不同的场合给出不同的定义,很让笔者感到意外。因为林毅夫教授是在全球最顶尖经济系,也是自由市场派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理应有良好的理论、逻辑、严谨的分析训练;其次,你无论怎么指出和着重强调,他好像总会忘得干干净净,下次仍得让你重新再说一遍。
这次看了11月9日他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公开辩论后,更加确认林毅夫在讨论问题时非常不严谨,对自己观点的阐述逻辑层次不清、概念模糊,并且不时地根据需要改变定义,对于这些缺点,张维迎也指出来了。
尽管质疑声四起,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指出了这点,林毅夫仍不为所动,仍然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这样的辩论方式,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及和他辩论的困难性。
可能笔者是学数学出身,攻读博士是在以严格、严谨训练学生著称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一直又是从事微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讨论问题的不严谨性特别在意,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林毅夫在辩论中存在的这个弊病。
作为学者,我非常赞同林毅夫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所提倡的辩论方式:“辩论不是口头的,因为,口头辩论不容易聚焦于逻辑和经验事实。写出来最好,通过文章,大家可以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这样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清楚。
”所以,笔者写成此文,在下面具体讨论他们的对与错,我会毫不遮掩地指出林、张两位可能有问题的地方,真正希望做到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以便读者辨析。
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张维迎给出的论断是学术方面不严谨的问题,那么林毅夫不仅是学术方面有问题,更是思想性、把握改革的方向性和学术讨论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一、林毅夫的对与错
我读了林毅夫教授不少的文章和论著,我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观点有不少合理的部分(比如政府对产业政策应该因势利导的看法,我原则上是赞同的,不同意之处是要慎用,特别是不能任意扩大化),其研究的问题,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面对、重视和解决的,但他的认识有许多误区和不正确的地方,得出了一些没有严谨逻辑分析的结论或犯了结论扩大化的错误。下面提出10点看法和林毅夫商榷。
1.应通过控制实验科学分析法来辨析什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差异因素。
林毅夫认为,中国能够在30多年里实现高速发展,归功于政府的主导,认为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从而形成了其要构建有为政府的核心结论。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异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做对比(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是没有可比性的)。
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林毅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以此找出两个因子之间确定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找出差异因素。我在多篇文章中实际上已给予了回答: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成就之外,仍然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得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了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
按照控制实验科学方法的说法,也就是,除了固定的因素(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等)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对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市场化改革中才取得的。
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尽管许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怎么能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归结为是由于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造成的呢?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犯了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从而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结论,怎么可能由此得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从而解决改革何去何从的核心问题呢?由于遗忘了这样的科学比较方法,凡是人们谈论到新因素的时候,就指责为不重视甚至是在否定那些原来就有的固定因素,从而被林毅夫贴上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
林毅夫之所以得不到这样的结论就显得一点不奇怪了。
2.讨论问题不能在对方已经澄清后仍曲解他人的观点。
在这方面,让笔者感到十分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对方指出澄清后,林毅夫仍会曲解混淆他人的观点,使得对方不得不停留在解释说明、再被忽视、再解释说明的循环中,使得讨论无法深入和继续下去。
比如,林毅夫将东欧等国休克疗法式的“三化”与中国分阶段渐进式“三化”改革总是混淆在一起进行比较批判,以此说明中国的“三化”改革不是导致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从而将赞成中国式的“三化”改革的人上纲上线到是在赞成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者。
尽管包括张维迎、文贯中及笔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反复澄清,指出了他这样的混淆和曲解之处后,林毅夫仍是如此,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中,仍是一如既往地采用这种不科学、混淆曲解的说法。
这样的混淆,在林毅夫的文章和讲话中比比皆是。比如,我已经在拙作《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中特别指出,对提倡有限政府的人被认为是“不注重过程和手段,只注重目标,这完全是误解”,“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要以目标代替过程,代替手段,也不是只强调目标不强调过程,不强调手段,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不能迷失市场化方向,强调要在市场导向的大前提下通过松绑放权改革,通过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做加法的改革,通过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来逼近有限政府的国家治理目标”。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怎么会傻到将目标和过程手段混为一谈,或不讲过程手段而使目标成为黄粱美梦般的目标呢?尽管反复澄清,但林毅夫仍在《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中将提倡“三化”的人认作为是在赞成休克疗法,认为是把“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对市场有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把这种扭曲取消掉,经济就会发展好”。
如果讨论、争鸣老是这样兜圈子,对增加共识有什么帮助呢?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希望林毅夫今后再谈论问题时,应针对问题进行讨论,别人已经澄清的看法,就不要再进行曲解或歪曲了。
3.讨论问题的前提是概念和定义一定要明确,不能多变,否则会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
从学术讨论要有效和要有意义的角度看,首先需要做到的基本前提是:每人所给出的概念和定义一定要明确,否则会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定义在不同场合会给出不同的定义。在和我的讨论时是一个定义,而在这次和张维迎讨论时,却又给出另外一个定义。
不久前,在给我的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中,他修改了王勇允许政府事后乱为的可能性(好心办错事)的情况,排除了王勇的既允许有为政府事后乱为、同时又排除事后乱为的逻辑矛盾的情况,排除了事后乱为的可能性;但在这次和张维迎的讨论中,却又恢复成和王勇一样的定义,允许事后乱为(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