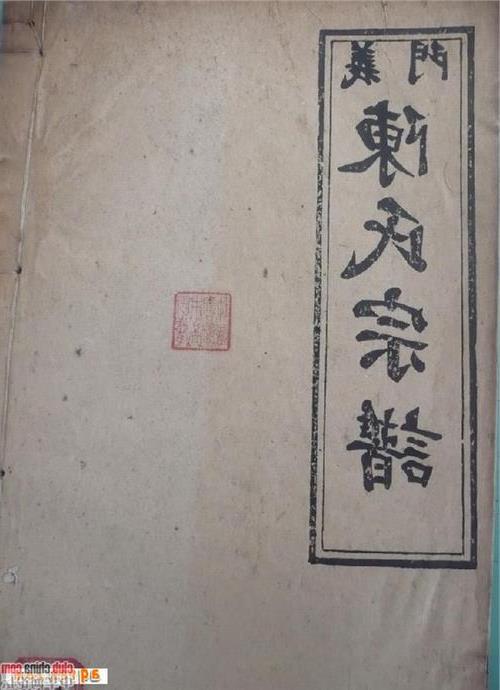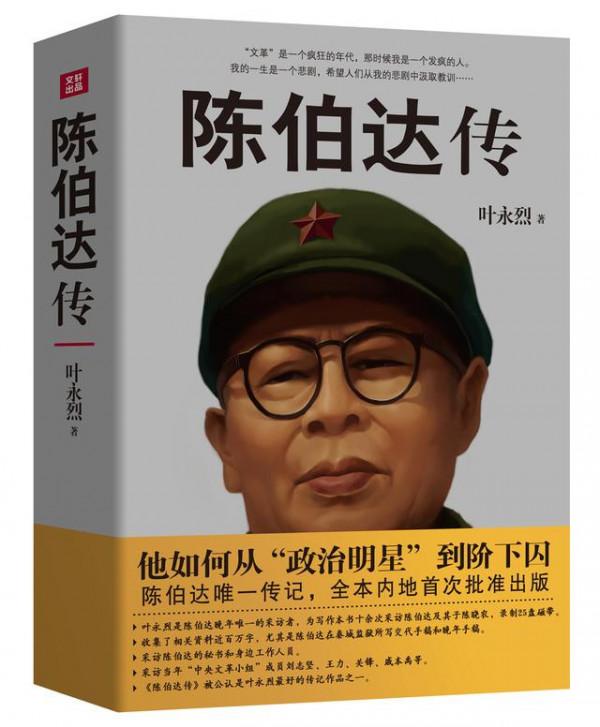【裘法祖带陈孝平请罪】陈孝平:裘法祖院士教我做人、做事、做学问
编者按:本文是裘法祖教授的学生陈孝平在裘教授2008年6月去世后不久,写的回忆恩师的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华外科杂志》2008年8月第46卷第16期。
裘法祖(1914.12.6—2008.6.14)简介: 浙江杭州人,18岁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1936年赴德国求学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一等最优秀成绩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1985年获得联邦德国政府授予的大十字勋章。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外科学奠基人之一,我国腹部外科和器官移植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作者陈孝平简介:现任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肝脏外科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53年6月出生,籍贯安徽阜南。197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同济医院普通外科从事医疗工作,在裘法祖、吴孟超和汤钊猷等前辈的工作基础上,在肝胆胰外科领域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3月获2016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裘老离开我们这些天以来,我时常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谆谆教诲,想起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我始终不愿相信他已经永久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奉献一生、挚爱一生的祖国医疗卫生、医疗教育和医疗科研事业。
自从我1979年考上裘法祖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继而于1982年又成为他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后,我开始有机会长期接触到裘教授。我为能在这样一位大师的精心栽培下成长、能在大师身边工作而一直感到无比幸运。
对病人——妙手仁心
记得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湖北松滋有个小姑娘,姓袁,当时只有9岁。这个小姑娘因为患有先天性胆道狭窄,求治了多家医院。医院要么不收治,要么是无力治疗。她的家人抱着仅存的一线希望来到了武汉同济医院(当时名称是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小姑娘来的时候已经面黄肌瘦,气息奄奄了。裘教授当即为小姑娘作了检查,之后马上就安排了手术。
裘教授仁心妙手,用他的高超医术又一次挽救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大恩难言谢,知恩必报答。小姑娘来自贫困的山村,他的家人用山里人特有的质朴方式感激裘教授。小姑娘的父亲说,是裘教授和共产党给了自己孩子新的生命,所以他执意将小姑娘的名字改了,叫做“裘党生”。
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了幸福的母亲:拥有了自己美满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
1996年,党生又一次来到了同济医院,这次来是因为她的病复发了,而且病情发生了变化,比以前更为复杂。裘教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手术,和我一起为党生治疗。在裘党生术后恢复期间,裘教授还亲自去探望她。
裘法祖教授看望术后康复中的裘党生(右一为本文作者)
党生家里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困难,而手术以后病人又需要长期口服利胆药,裘教授就坚持每两个月给她寄去足够的药品。开始的时候,党生坚决不同意裘教授这么做,她把药费都寄还给了裘教授。
为此,裘教授特别难过。他马上写信告诉党生:“既然你把名字改了,叫做裘党生,那么你就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就是我的女儿,父亲照顾自己的女儿是理所应当的。这20多年来我也没怎么照顾你,现在尽这点责任,也是应该的呀。”我是这个感人故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其实,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就在裘老过世的前一个月,他不顾94岁的高龄,亲自为“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受伤患者会诊。
2008年5月24日,裘法祖教授为汶川地震伤员会诊
裘教授热心帮助病人从来不求回报,他对病人的妙手仁心常常让我感佩不已。我时常提醒自己,医者父母心,要像裘教授一样拥有一颗至大至仁的爱心。裘教授常常教导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以心换心、将心比心,尤其是病人和医生之间更是如此。我们外科医生责任重大,一旦开始手术,病人就处于了麻醉状态,这个时候病人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医生的手里。而此时,对于信任我们以致性命相托的病人,医生怎么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裘教授常说,做人要老老实实,我不要求你们做最聪明的医生,我只要你们做最老实的医生,最老实的医生才是最聪明的医生。做老实的医生就是要对病人、对自己老老实实、一丝不苟,这样的医生才是患者信任和尊重的医生,这样的医生也才是真正具有回春妙手和仁爱真心的医生。
裘教授要求外科医生们在给病人手术后的当天晚上,一定要去病房查看病人。尽管这可能会延长医生的工作时间,增加医生的工作量,但是这却是对病人的一种心理安慰,也是对病人的一种负责的态度。而由此创立的三次查房制度也在同济医院外科一直沿袭下来。现在,我们一直秉承着裘老的精神,无论工作到多么晚,一定要到病房去探视手术后的病人。
对学生——严格真心
我是在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考上裘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的。当初报考之时,就是因为我非常仰慕裘教授的医术和医德才坚决从家乡安徽考到了武汉,并且因为出色的专业课成绩有幸成为了裘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继而成为他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特别想见到裘教授。开玩笑地说,裘教授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呢!那个时候的心态和现在的年轻人追星,做“粉丝(fans)”差不多,只不过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般狂热。
不过,裘教授的工作一直很繁忙,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机会能见到他。后来,另一位老师吴在德教授接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裘教授培养学生的主要原则就是要做到“三会”:即一会看病开刀,二会讲述手术经验、给学生上课和作学术报告,三会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三会”,就觉得十分新鲜。因为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做个外科医生只要会给病人看病和开刀就可以了,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要求做到会讲、会写。这个“三会”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裘教授在医疗教育和医疗科研方面的敏锐眼光与超越常人的胆识和魄力。
裘教授也因为这个“三会”而被同仁誉为出了名的对学生严格。教学“三会”为我的事业和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我未来的发展拓宽了思路。
而这个“三会”也成为后来卫生部培养临床博士研究生的标准之一。以后,我就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在这三个方面的能力。艰苦的努力有时会得到意料中的惊喜。那个我毕生难忘的时刻终于出现了,裘教授主动来见我了!
1982年,《武汉医学院学报》(外文版)约稿用全英文撰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现状”。这篇论文受到了编辑的好评,裘教授也十分关注。他在仔细阅读了我的论文之后作了认真的修改,甚至连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一篇论文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裘教授的批注。
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师做学问的严谨,对学生的严格和对学生的真正关怀。后来,我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裘教授都是反反复复地改了三、四遍后才定稿。
裘教授指导年轻外科医生临床学习有他个人的特色,那就是“放手不放眼”,也就是说大胆放手让学生去做,但是导师并不是不管不顾,而是要在一旁观察,随时指出手术中的关健和要点,并及时纠正手术中出现的错误。从我做动物的肝脏实验开始,一直到安排专门的病房进行临床培训,裘教授总是经常在旁边认真观看、亲自指导。
裘教授的这种“收放”教学法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易学易记,既能给予学生充分的手术自主权,又能及时发现手术中的失误并立即纠正,让学生们获益良多。
在和裘教授长期的工作和生活的接触过程中,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心中,并且在各方面表现出来。这些年我在业务上也有了一些的成绩:参与了全国外科学教材第五版的编写,并且担任了七年制和八年制《外科学》的主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肝胆胰突出贡献奖和第二届全国教学名师。
每当我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因为如果没有裘教授对我的严格要求,没有他那颗隐藏在严厉外表下的对学生的炽热真心,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其实,裘教授对他所有的学生都很严格。如果你工作上出现错误,他会严厉地批评你;如果你满足现状不努力学习,他会毫不留情地指责你。但是大家都能够真心地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越是对你严厉的老师越是在付出他的真心关怀你!裘教授常说,做他的学生不容易,可我说当学生导师的裘教授更不容易,因为裘教授是在呕心沥血地培养我们呀!
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对每一位脚踏实地、追求上进的青年医生,裘教授都会热情帮助。每年都会有很多青年医生给裘教授写信,而裘教授一旦发现其中有值得帮助的好苗子,他都会不遗余力地送去真诚的关怀。
对学术——永无止境
裘教授常常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否则就会走上歪路。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做人要老老实实、懂得知足;做工作千万不要只追求速度而不要质量,欲速则不达,所以我们做事要踏踏实实、懂得不知足;求取学问千万不要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所以我们对待学术要严谨求实,懂得知不足。
裘教授曾多次告诉我,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当时中国医学界热衷于分门别派。比如说,有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的南派和北派之说,有以留学国度不同作为划分标准的德日派、英美派之说。对于这种做法,裘教授并不很认同。他说中国应该只有一个学派,那就是中华医学派,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应该团结在中华医学会的周围,以不断发展祖国的医疗卫生、教育和科研事业为己任,而不是要搞林林总总的派别,分门别派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态度,是不利于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的。
对于裘教授的这种态度,医学界的同仁们甚为服膺。
吾爱吾师。
裘教授常常提醒我们,要在学术上追求永无止境,精益求精,他首先就给后辈们做了一个好榜样。裘教授自己就是一个在学术上不断要求精进的人。
1932年至1936年裘教授就读于上海同济医科大学,后来为了精进学业,裘教授远赴德国慕尼黑,在异国他乡艰难求学,荣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裘教授率先将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等,并给各专科的发展予以精心的扶植。
50年代,裘教授在我国较早开展分流术和断流术。为了中国医学教育发展的正规化,裘教授与黄家胭、吴阶平等一起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自己的教科书《外科学》。
20世纪60年代,因为敏锐地感知基础性实验研究对于临床工作的重要性,裘教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腹部外科实验室;20世纪70年代,裘教授根据国际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中心和专业病房,开展器官移植工作。
裘教授还创建了“责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被称为“裘氏手术”),大大提高了在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效果。到本世纪,裘教授对当今医学领域进行的分子生物学革命也十分熟悉,即使不能亲力亲为,他也支持建立了医院的“临床医学分子研究中心”。
70多年来,裘教授改进新术式不下数十种,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他主张“医学归于大众”,早在1948年就创办了全国知名的科普杂志《大众医学》。他是《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还担任《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等数十种国内外权威学术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
吾更爱真理。
裘教授一生提携后辈,甘当人梯。每当他看到晚辈们取得成绩时比他自己取得成绩还要高兴。裘教授常说,做他的学生一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总是鞭策我们说,他现在年龄大了,在接受新知识和创新方面不如年轻人了;但他要在有生之年多发现和培养一些人才,这是延续他学术生命的最好办法。他鼓励我们说,如果学生仅仅只是停留在他的水平上,那么这个学科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了。只有学生比他强,这个学科才会有前途。
是的,裘老正是把做学问的最终要义,为学术的真正精华告诉了我们。正如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样,我们也不能步趋前人,因循守旧。我挚爱我的恩师裘法祖教授,但我更挚爱裘老不懈追求真理的一片热诚。
对家人——毫无私心
裘教授对他的病人以心交心,不求回报;对青年学生严格热诚,真心关怀。从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可以说,裘教授以他的一颗真心对他人付出了人间大爱,可是他对自己的家人却从不溺爱,毫不偏私。
裘教授有两个子女就读我们同济医学院,可是他们毕业以后并没有如很多人所料留在同济医院工作。其中一个去了经济相对比较落后、条件相对比较艰苦的十堰地区,成为了湖北省郧阳医学院的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
按理说,凭着裘教授崇高的社会地位、精湛的医疗技术、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仁厚的爱心,要把自己的子女调回身边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裘教授没有这么做。而且,当时很多领导、同事提出将他儿子或女儿调到身边工作,他都一一婉言拒绝了。到裘教授晚年退休的时候,医院的领导多次表示要把他的儿子调到同济来,裘教授始终也没有同意。
也许有人会说裘教授这么做似乎有点不近人情,或者说有点迂腐和固执。可是我并不这么看,因为我很了解我的恩师。更重要的是,他的子女非常理解,因为裘教授一生清廉节俭,他常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做子女的有责任维护自己父亲的一生廉洁。
其实,在裘教授看来,只要你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孜孜不倦地做学问,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只要能救死扶伤、解除患者的痛苦,挽救患者的生命,哪里的病人都是我们的亲人。裘老不是不爱他的孩子,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着他们。他这位伟大的父亲是后辈们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关于裘老的回忆如同潮水般涌来,似乎怎么也流淌不尽。要说的、要写的实在太多太多了。裘老奉献一生爱尽天下,在他的学生眼里,他不仅是个好医生、好教授、好学者,更是一个好长者。在他的病人眼中,他不仅是个回春神医,更是他们可以托付性命的至爱亲朋。我不想说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因为他从未离开;我更愿相信天堂里多了一位纯真善良的白衣使者,永远守护着他挚爱的人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