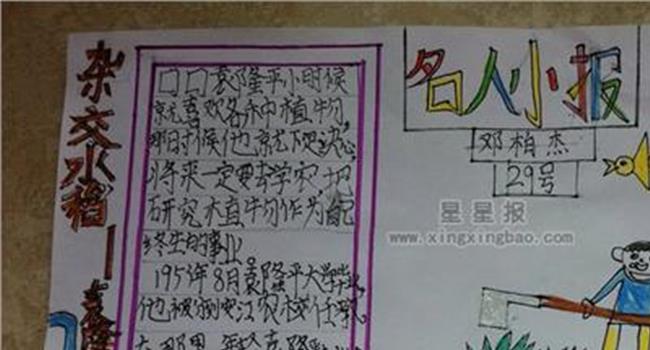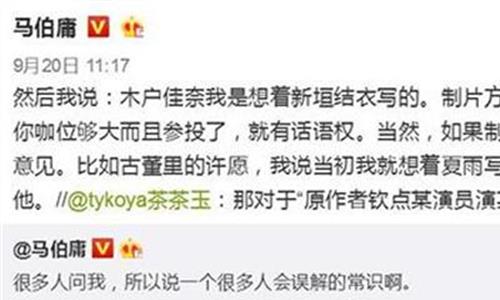马伯庸哪里人 马伯庸“马亲王”的真相
说起马伯庸,相信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祥瑞玉兔,家宅平安!”这源于他写作初期,在某论坛上为自己炮制的一则“神话”。据说,马伯庸成立了“西肃慎代天启运后清诸上神圣千年上等开明大帝国”,自号“太祖盛武文圣德仁昭明高贤景匡弘直帝”,简称“后清”,“一个没有太监与坑的伟大国家”,实际上基本含义是作品连载不会中断(网络上经常用“作者太监了”来形容作品连载中断)。

接近他的人都有厄运,除非高呼“祥瑞御免”,方能逃过此劫。原是句玩笑话,竟然成了他的标签,网友们也多称呼他为“马亲王”。
最近,“马亲王”甚至开始为这标签苦恼。据说,有影视公司想要改编他的小说,听说此事立刻作罢,生怕引火上身。

当见到马伯庸时,现实生活中的他与对“亲王”的想象差距很大。江湖传言,马伯庸是鬼才,有摘叶伤人之功夫,善挠文青之痒处,行文诡异。而马伯庸则自嘲:我就是个老实的胖子,与世无争,谦虚谨慎,朴实刚健,更谈不上什么鬼才。

唯一可称道的,只是敢把自己古怪念头公之于世的勇气罢了。如果有三两好友同台酬唱,千百看客围观喝彩,那是最好不过;要是没有,浅斟独唱也不失风雅。什么门派、文青之类,沧海一声笑置之就是……
其实他说的一点不假,不要相信“谣言”。
因其新书《三国配角演义》面试,与他相约采访。安排采访时间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他虽然已经出版了《她死在QQ上》《风起陇西》《三国机密》《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笔冢随录》《三国机密:潜龙在渊》《古董局中局》等十余本作品,但至今仍是一家外企的白领,请假不那么方便。
当日,“马亲王”穿戴朴素,初次见面还很拘谨,一阵寒暄之后,依然紧绷,直至采访即将结束,他在微博上幽默冷峻的气质才逐渐显露。
“我是业余文学爱好者”
马伯庸出生于内蒙古、成长在桂林、上海上学、新西兰留学、北京人脑子的80后,从小到大转学13次,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商学院毕业到新西兰留学,专业都是市场。目前他的工作也是在一家外企市场部门“写PPT、写调研、写报告”,朝九晚五。
对于,文学、写作,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作家,准确来说,我甚至还不算是一个写手。我被大家知道不是因为我的小说,在这方面我只能算三流,而是我的恶搞。
恶搞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新文学形式,以荒谬、荒诞、荒唐为基调,介于玩笑与真正的幽默之间。我在这方面,还算有些天赋,写了些让人看了觉得荒诞的东西。如果非要说我是什么人,那么就说‘业余文学爱好者’吧。”
马伯庸对于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从小时候就开始了。他出生在内蒙赤峰,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松园的小书店,“我小时候常去那里租漫画看,前几年回去还开着,都二十多年了。”当他问起老板,小时候曾租借过的漫画时,他看到那些老漫画书被一捆捆扔在后面。他以两元一本的价格全部买下,“收购了一两百本,大多是现在绝迹的珍本,运回家里,躺在床上一本本翻阅,幸福得一塌糊涂。”
他的阅读就如他的写作一样,涉猎到的题材非常广泛,“科幻、奇幻、恐怖、武侠、战争、历史都写过,但往往只持续一段时间的兴趣,然后就立刻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对每个题材都涉及过,但每个都没有深入挖掘,只在表层晃荡。
”他曾如此形容他的作品:“如果把我称做《风起陇西》亲生父母的话,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贾克,祖母则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罗贯中与陈寿,外祖母是丹·布朗。”克里斯提昂·贾克以《谋杀金字塔》为代表的埃及历史小说,弗·福塞斯以《豺狼的日子》为代表的政治谍战小说,丹·布朗以《达·芬奇密码》为代表的阴谋悬疑小说,从各个方面构成了马伯庸的资源。
1997年,马伯庸开始上网,“上外附近一家盲人按摩中心旁边有个网吧,每小时20元,每次去我都要省下一周的早饭钱。时间宝贵,看到好的小说,我就会立即下载到3.5英寸软盘,然后到学校里机房看,机房1元一小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开始关注一些网络论坛,“多在BBS泡着,泡久了偶尔尝试着编一些好玩的故事,希望博别人几声赞叹。发到论坛,反响不错。”
他最初引起注意的是一系列戏仿他人的小文章,比如《三篇作文》,分别以田中芳树、村上春树、王小波的文笔,写“一只小船”、“送伞”和“记一次难忘的劳动”,令人捧腹,由此也形成了他的另一文风:混搭。例如以西方翻译腔的风格写三国,“诸葛亮是如此惊讶,以至于他半天说不出话”;或是以东方武侠的风格写中世纪欧洲,“一名教士跃至半空,刷刷刷甩出三剑,将对手迫退,然后长啸一声”。
“我最擅长的就是模仿各种不同的文体。从中学时代起,我帮人写入团申请书,写入党申请书,写思想汇报,写英雄楷模的学习报告,还帮我妈写过十六大的学习心得。”马伯庸说。上班后,同事知道他笔头好,逢年过节,公司有什么活动,就会拉他去写个串场词,或是帮领导写一篇20分钟的发言稿。
对于马伯庸来说,写作是一种放松,越是吵闹的环境状态越好,感觉像是上课时,自己突然偷跑出去玩一会儿,那种兴奋和快感不言而喻。
他的成名作《她死在QQ上》的问世也带有某种戏剧性。马伯庸笑称,这部作品最先是在盗版书中问世的,“2002年我在新西兰留学时,为了哄当时的女友开心,在写论文的间隙写了这个故事。
我不会甜言蜜语,只能编个鬼故事哄哄女孩子,并把当时特别流行的QQ作为故事的背景和载体。”起初,马伯庸为这个故事起名《QQ怪谈》,结构上借鉴的是铃木光司的七夜怪谈,发表在论坛上,在同学间传阅,慢慢便不了了之了。
马伯庸突然在一个小书摊儿看到一本叫《笔仙》的小说集,里面有四个故事,最后一个叫《她死在QQ上》,“后来我才知道后来有位转帖者擅自把名字改为《她死在QQ上》,立刻流行开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版权的问题,只是觉得挺荣幸,自己的东西被出版成书了。不过必须承认,这个故事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文笔近乎白描,乏味淡薄。现在回过头看,只能算是幼稚的早期作品。不过这么一篇缺点多多的东西,在网络上的流行程度居然超过了我的所有其他作品。正式出版前曾被盗版过几次,甚至被改编成漫画和广播剧。大概因为题材很讨巧。”
“写作应该是一桩乐事”
每天7点起床,此前坐着地铁上下班,现在添置了汽车,写作只是马伯庸下班回家后的“业余活动”,“就像是其他人吃火锅、玩游戏、看美剧一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休闲手段。在忙碌了一天PPT和工作报表以后回到家里,打开电脑,点开WORD开始写东西,我会感觉到非常惬意,不觉得累,反而非常放松。
我一向认为,写作应该是一桩乐事,不是苦差事,兴起而作,兴尽而止,这样的状态是最舒服的。”
因为天天上班,他的作息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1点准时睡觉,,很少会有写得兴奋而停不了笔的情况。不过他说:“与很多人不同,我写作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包括中午休息、上班路上等,有时灵感来了,在地铁上我也会掏出手机写上几句。我们领导都知道我在干别的事,但只要不影响工作,他们也不会说啥。我出了新书会给领导送,领导看没看,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网络作家的出现,让跟多人加入到这个庞大的行列当中,其中不乏身家百万的佼佼者。马伯庸出道多年,其作品也常常登上畅销榜单,但他希望依然坚持这样的写作状态,“有过几次动摇,觉得要不要把写作作为自己的主业。
我是做市场的,最喜欢拿各种东西分析,我觉得写作还是作为业余爱好比较好。对我来说,写作是兴趣,保持一个业余的状态,我的心态会比较好,不想写了,也有正当工作。如果我把它当作本职工作,每天只要打开电脑就是上班,没有节假日,这样对我来说很痛苦,而且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好。
万元写手的出现,给网络作家们提供一个榜样,证明在这一领域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很滋润。不过没我什么事儿就是了……我每天写上两三千字就已经累得要死。”
马伯庸希望自己像马克·吐温、钱钟书一样,把写作当成乐趣,把读者当成损友,不用每天正襟危坐。上班时间的脑子运转模式和下班时间不一样,对于他来说,写作便是一种娱乐和休息。他很喜欢王小波的一句话:“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2010年,马伯庸的《风雨<洛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并肩,获得了当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的《宛城惊变》、《破案:孔雀东南飞》等又获得朱自清散文奖。
虽然感到自己多年的写作得到了承认,但这些奖项对马伯庸的写作没有什么影响,“我没有觉得我既然得了奖,就算是一个正经作家,要写一些正经东西,我没有这种使命感”,对于他而言,他的写作仍然是小众的,只有圈内人才能会心一笑,“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和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的想法,我喜欢的趣味,我的读者会喜欢;我在字里行间埋下一枚彩蛋,和我有共鸣的读者会很快把它挖出来。
他们在我笑的段落大笑,在我哭的部分流泪,如果说他们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我想这种‘默契’是关键。
把自己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汇聚成语言、形成文字、攒成小说,展现给志趣相同的人,让他们会心一笑,就足够了。我写作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有趣,其他效应仅仅只是它的附带产物。”
确实,在志同道合的读者心中,马伯庸很“有趣”,睿智、多知、灵动,有多到数不清的典故和冷笑话,他的写作天马行空,充满各种奇思妙想,涉猎题材更是宽泛,“我如果局限在同一类型,很快就会觉得厌烦,时常换一下题材,一来保持新鲜感,二来也可以挑战一下自己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很刺激。”
“重构历史是件刺激的事”
在所有题材中,历史小说一直是马伯庸写作的重点,“历史小说的创作,有点像是警察站在凶案现场,他必须凭借遗留下来的线索来重新推演当时发生了什么,重构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刺激的事,所以历史小说会写得多一些。而且历史往往留有既定的样貌,如何在创作时不太过偏离这些定见,又能玩出自己的新鲜花样。”
从《风起陇西》《三国机密》,到最近刚刚出版的《三国配角演义》,马伯庸的历史小说被一些读者称为“历史可能性小说”。他以挖掘历史真相之名,行八卦之实,将真实的史料与推理悬疑相结合。
他总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出一连串被忽略的空白点,然后以丰富的想象、严谨的逻辑和细腻的文笔,将这些空白点填补得严丝合缝,令人信服。这也正是马伯庸对于自己作品的得意之处,“我在小说里边,埋了很多事实。
尽管,我可能在情节设计上发挥想象,但是落到实处,所有的地方都实有可据,都能在历史上查得到。如果有人看到一个细节,不明白,去百度查,就能在历史上找到相关的记载。看似毫无关联的记载被相互连接,对我来说最为得意,这同时也是焦头烂额的地方,把一堆散碎的,没有关系的,编成一个前后逻辑看起来正常的故事,让人焦灼。”
同样,让他获得“茅盾杯”的散文《风雨<洛神赋>》也采用了这种文体,被网友称之为“考据体”。在《风雨<洛神赋>》中,《洛神赋》这首爱情诗歌的背后浮现出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宫廷阴谋:甄宓与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非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那么简单。
为了赢得立嗣之战,曹丕特意安排甄宓去色诱曹植。甄宓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必须让曹睿封爵,诏告天下。后来成为魏明帝的曹睿,其实并非曹家后代,而是甄宓与前夫袁熙的孩子。
这篇文章的论据均有出处,例如曹睿或是袁熙之子,虽然有历史研究者提出过,已被证实不确,却不妨碍进行再创作。而马伯庸是第一个将曹睿的身世之谜,以及甄宓、曹丕、曹植三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串联起来的人,再加入适当的发挥,便演绎出了一段全新的历史故事。
对于这种近乎游戏般的写作方式,马伯庸屡试不爽,“这是伪历史,但不是伪造历史。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只要逻辑上成立,也不能说它肯定没有,不妨将其当成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作家写历史小说有两个困境。
一是太拘泥于历史本身,真实感有了,但戏剧性和趣味性就打了折扣;二是太过天马行空,以至于读者根本感觉不到历史的厚重味道。我希望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史料的碎片进行拼接,给读者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
马伯庸坦言,其实这种“考据体”也不是他的发明,“不少作家都玩过类似的花样。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就说他在图书馆发现了一卷记录,讲述了达达尼昂这个人的生平事迹。貌似是真实的历史,实则是幻想出来的故事。
我这种写法还有一个来源,就是红学的“索隐派”。索隐派的红学家最喜欢通过脂砚斋的批语和《红楼梦》前八十回透露的一些细节,来考证或者说猜测后面会发生什么故事。而且每个人弄出来的故事都不一样,既不能说他们对,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这些考证姑且不论学术上如何评价,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是很有趣味的,非常有想象力。这还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把故事产生的过程从头到尾地讲给你听。以前看索隐派的红学著作,我并不急着去想故事是真是假,只觉得像读推理小说一样,特别过瘾。”
他最为推崇的是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这是一部奇书,它把我一直喜欢的以考据的手法写奇幻的故事这种方式做到了极致,其中的细节是极其到位的,读了之后满脑子都是学术索引和史学教科书的影子,吊书袋到了一定境界。无句不有典,这就好玩了。有典故的情况下,还能玩出自己的花样,就更酷了。”
马伯庸在他的新书推荐中,这样写道:“那种在历史会有所作为,对历史产生影响,却因为种种原因却不为人知的人会进入我的视野。譬如拘于他们身份卑微或者尴尬等等政治不正确的原因,被写作者刻意抹掉的。表面看起来,他们很正常,但很可能背后藏着阴谋。”
“对三国的兴趣仿佛与生俱来”
在众多历史题材当中,马伯庸对“三国”情有独钟,他的几本代表作都是与三国时期有关的,还曾写过众多有关三国人物、三国历史、三国趣事的杂文,"微三国"更是他撰写微博冷笑话段子的常用主题,他还有一圈同样热爱三国的好友。
马伯庸说:“三国题材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里面的英雄。这里说的英雄不光指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还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配角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所有的这一切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无限的历史可能性,每次扑进去,都会有新的发现。”
追溯马伯庸对“三国”的兴趣,他说:“小时候看三国连环画,听袁阔成的三国评书,后来认识字多了,就看三国演义,评话演员张国良的三国文本,还有央视版的电视剧。我对三国兴趣很难标定一个清晰的起点,仿佛与生俱来。”
初中时期,他迷上了“三国”题材的电脑游戏,尤其是日本光荣推出的《三国志》系列。游戏中,登场亮相的三国角色多达数百名,其中不少是他以往从未注意到的冷僻人物,比如戏志才。
此人在《三国演义》中并未提及,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也只是略有记载,而在游戏中却有很高的智谋值。发现这个神秘角色后,他翻阅史料,才知晓此人的身世背景:戏志才由荀彧推荐出山,成为曹操的谋士,深受曹操器重,可惜尚未有机会施展便因病去世。
“自罗开蒙,从陈渐深”,马伯庸用这八个字概括了罗贯中和陈寿对他的影响。而他真正开始研究三国历史,则是始于网络作家赤军的一篇文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篇文章颠覆了他对诸葛亮这个人物的认识。
之后,他找来《后汉书》《华阳国志》《晋书》等史书,翻看与三国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比如有关两汉的制度、经济形势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化、职官制度、农业发展、科技水平这方面的著作。
一些老专家,比如方诗铭、白寿彝、马植杰,他们关于三国的论著对我有很多启发。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枯燥,但真心喜欢三国读起来就会很有意思。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要经常参考的。现在香港有个笔名叫陈某的漫画家,他画了一套《火凤燎原》,很好看。”
马伯庸写的第一个有关三国的小说是《街亭》,“我发现马谡不是被诸葛亮处死的,而是死在监狱里。后来我又读到一个叫郭循的小人物,他是姜维北伐的时候抓回来的,费祎很欣赏他,提拔为左将军,一直随侍左右。
结果有一次费祎喝醉了,这个郭循就拔刀把费祎刺死了。我就把这两件事搁到一起了。马谡就是基督山伯爵,他先是越狱逃跑,再改名叫郭循,因为是费祎害了他,他就找到姜维,说愿意当死士,刺杀费祎。
正好姜维想把费祎踢走,就把郭循派了过去。就是这么一个阴谋故事。这两处细节分开来没什么,合在一起就非常精彩。”他喜欢捕捉细微之处,并琢磨各种“阴谋论”,再追问下为什么。史书上一行简单的文字在他那里就是一个悬疑推理故事。经过他一番勘探,
新书《三国配角演义》中收录的几篇小说,关注的都是在大历史缝隙中的一些小人物的细节和命运。马伯庸认为:“三国已经被人说得太多了,写三国的文学作品也太多了。关羽、曹操、诸葛亮这些人物,已经被说过好多遍,再想深入挖掘不太可能,一个馍被人反复嚼过,我再去嚼,挺没劲的。
三国毕竟是一个大时代,除大人物以外,许多小人物的故事的趣味,不在大人物之下。不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非常可惜。”
马伯庸说,三国只是他钟爱的题材之一,切勿把他看作“三国专业户”。而接下来,他还会尝试三国的更多写法,譬如灵异、商战。
他刚刚完成了《古董局中局》第二部。《古董局中局》是一部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的百科式小说,刚一上市便迅速蹿红,成为2012年图书界的一匹黑马,书中涉及很多古董造假、设局案例,让人瞠目结舌。马伯庸称,《古董局中局》绝不是耸人听闻,古董行业的水很深,这本书也仅仅是揭开古董行业冰山一角,根据他的经验,古董行业赝品比例高达95%。
因为此书实在看起来太真实了,很多读者都以为马伯庸是个收藏古董的行家。但马伯庸却透露:“我在精神上玩古董,就好像我喜欢看足球,但很少下场去踢一样。我家的古董收藏为零。我喜欢去博物馆看,看到喜欢的,我会把它的每个细节都记下来,去琢磨这些细节背后有什么好玩的故事。”于是有了那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引发了中国收藏界一场不小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