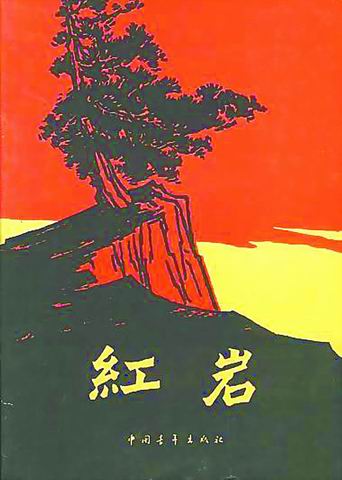白公馆渣滓洞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者讲述脱险经历
1949年,我在磁器口小学任教。11月27日晚,我住在学校对面的聚生茂酿造厂楼上,只听得枪声不断,心想又是哪里发生了事。第二天才听人说枪声是渣滓洞那边传来的,恐怕是里面关押的人被害了。当时人心惶惶,大部分老师回了家,只有我和蒋继业、黄玉华、李振容等8人继续留在学校。

11月30日一早,我和黄玉华、李振容三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从原“中美合作所”大门经白公馆、松林坡向渣滓洞走去。一路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让我们不忍卒睹。渣滓洞监狱一片狼藉,空坝上全是烧焦的烈士遗骸!孩子哭喊着找爸爸,女子哭喊着找丈夫,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无不伤心流泪,有的手巾都湿透了。

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却发现在离碾米槽不远的一间空屋里,靠墙边地下坐着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黑色长棉袄,看着像是久病的人。他稍抬头看我,我十分惊讶,竟是曾教过我高小语文的老师张泽厚(我们都是四川岳池赛龙乡人)。

1948年8月,张泽厚和弟弟张泽浩等人因岳池暴动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张老师还活着,我又惊又喜,上前问候。张老师说,渣滓洞大屠杀时,他躲到了粪坑里,特务补枪时,不少战友倒在他身上,因此虽身中多枪,却并未致命,只是小腿露在外面,伤势较重。我当即找人帮忙,卸下门板,将张老师抬到了沙磁医院(今重庆市肿瘤医院)。

12月4日,我到沙磁医院看望张泽厚老师。这时,病房里又新住进了一位脱险同志,他就是谭谟。
张老师介绍我们认识后,彼此谈起话来。谭谟向我介绍了他脱险的经历:
1927年11月27日,我在白公馆牢房里。下午两点,来了一些匪特,看样子是一些长官,全副武装,神情异常。一会儿开会,三个五个在一起,七八个聚一团,看样子今晚怕是要出什么事。不久,每个牢房的门加上了锁。屋子里的同志们静静地等着。
大约下午三点,徐远举找匪特开会布置屠杀任务。不久,杨进兴带杨钦典闯进牢门,对原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说周(养浩)主任请你们谈话,马上去。李副官也去。他们从石板路走下,到步云桥就听到砰砰的枪声,我想定是黄显声、李副官两人被杀害了。后杨进兴将屠杀名单交值班看守员杨钦典,令其照名单分批提人。
紧接着,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出了牢房,许晓轩、刘国鋕等人也一一被提出。我从牢房被提出来后,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步地走,走到马路旁,叫我们上了卡车。车往山上开了一段后在松林坡附近停下,特务叫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排成单行,站成横排。他们早已在此挖好了尸坑,准备好了机枪,向我们一一扫射。我听枪声随即倒下,受了伤但未到致命处。我倒在难友身上,又有难友覆盖在我身上,呼吸十分困难。
扫射完毕后,刽子手又从尸坑里取下每个人的手铐,检查每个死难者,然后匆匆离去。我紧闭着眼睛,突然听到一个刽子手说,还有一个人未射到。我当时心跳不已,忍受着剧痛一动不动。再隔了些时间,见没有什么动静,我才抬起头来看特务是否走了。
见周围没有异样,我拖着受伤的身躯爬出了尸坑。怎样走才好?往前走,有岗哨,特务是否还埋伏着?为了安全,我只有往后面山坡上走。走到山上,快天亮了,杂草一人多高。我在草丛中坐着,蹲着,有时又睡着,又冷又饿。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耳边响起了镰刀割草的声音。转眼间,那个割草的人已割到我的脚边,他拔腿就跑。我想,要是他告诉特务我就全完了,只有转移地方。
我继续向山上爬,爬到顶处,四下一看,前面有一幢房子,我慢慢走向那屋子。这像一家小工厂,里面有十几个工人,我向他们说明原因,请他们暂时收下我。他们看我说话老实,又像个久病的人,就收下了我。住了两天,我对他们说,27号那天晚上白公馆、渣滓洞里杀害了很多人,可能有未拿走的枪、子弹,你们应该捡点回来。
于是,几个工人到杨家山、电台军火库、白公馆等地到处查看,真的找到了几支烂枪、子弹。我叫他们擦好枪,教他们怎样用枪。我想,如果匪特又来了,我们好对付他们。
又过了两天,我和工人们商量:今天我要下山,分两起走,你们走前面,我走后面,各走各的,途中不打招呼,如果遇到盘查的人,各管各。工人们先走到两路口处(现在的烈士墓车站),果然遇到地方组织的盘查人员询问来去之处。
“我们从山上来,到磁器口去。”听了工人的回话,盘查人员没有放行,而是让他们“各人回去,不准过去”。我走到盘查站,他们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我说:“从山上来,到磁器口去看病。”盘查人员看我头发很长,脸色苍白,手还捂着肚腹,像个病人,就说:“你快去快回。”
我从磁器口往马路上走,边走边问哪儿有医院。走了快两个小时,才到重庆大学里面的沙磁医院。我向医院负责人说明情况,他们研究后同意收下我住院医治。
我真是九死一生,是从难友们的尸堆里逃出的幸存者。
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特追述此段往事以志不忘,向那些逝去的革命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