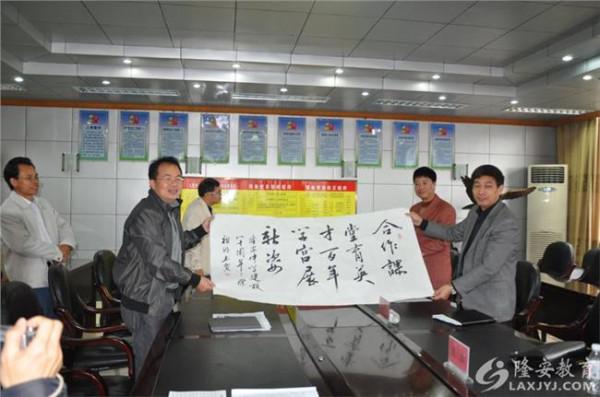谭其骧的学生 东湖更东:隆中“题词”是谭其骧先生晚年的学术败笔
东湖更东:隆中“题词”是谭其骧先生晚年的学术败笔
(欢迎指正)
提要: 1990年3月,谭其骧先生应襄樊有关人士的要求,写下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 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北周省邓县 此后隆中遂属襄阳”(原件无标点)的题词。其中“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 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依据的是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但把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说成属于南阳郡邓县,明显与诸多史籍中秦汉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的定论不合;另外,“省邓”不是在北周,而应是之前的西魏;“省邓”后隆中也并没有“遂属襄阳”,而应该是划入长湖郡的义安县或旱停县。
所以,谭其骧先生的隆中“题词”竟一无是处,不能不说是他晚年的一处学术败笔。而谭先生围绕“题词”的某些说法和做法,颇显得轻率粗疏和过度迎合,实在有失大家风范。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卓有建树的重量级专家。由谭先生主持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堪称皇皇巨著。谭先生在学术上的功业贡献有目共睹,自当受到世人的敬重。
然而 “明月无瑕岂容易”(杜甫诗句)。谭先生晚年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为隆中所作“题词”,以及围绕“题词”的某些说法和做法,颇显得轻率粗疏和过度迎合,有失大家风范,令人很不理解。尊重专家权威不等于迷信盲从,在倡导学术民主的当代,我们不必为尊者讳,本着求真求是探求真相的目的,指出谭先生晚年的学术败笔并予以纠正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相信也不会损害先生平生事业皓月之明也。
隆中“题词”内容证据不确,实难成立
在襄阳隆中景区武侯祠前,立着一块石碑,上刻谭其骧先生手书“题词”: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 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北周省邓县 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一九九○年三月 谭其骧 ”
据悉,这个“题词”是谭先生于1990年3月在接受襄樊人士访谈时应来访者要求当即写下的。当时正值南阳、襄阳因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而激烈论争中。襄樊方面拿到“题词”如获至宝,将其勒石并栽立在隆中景区中心的武侯祠门前,其意不言自明,无非是借助谭先生大名而自增砝码,并企图以定于一尊的方式逼使对方噤声息音,结束这场学术争辩。
这样做功利算计虽然重了些,倒也可以理解。而作为著名学者的谭先生,此举就未免有些儿唐突失当了。谭先生似以挥戈退日的鲁阳公自任,企图发一声响便喝令不同意见者退避。无论如何,这是有悖于百家争鸣、广开言路、繁荣学术精神的。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胡适先生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即便是谭先生这样的大家,也要遵从学术规范,如果他的“题词” 缺少论据、不符合史实,就不能让人信服,同样不能成立。
为了便于论述,不妨将“题词”拆分为两部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为前半部分;“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为后半部分。笔者将分别予以讨论。
很明显,“题词”前半部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是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的翻版。
《汉晋春秋》是东晋曾任荆州刺史别驾、荥阳太守的习凿齿所著私史。谭先生为了强调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可信度,特意指出:“正史不一定都可信,非正史不一定就不可信”。
这话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这只不过表明可信与否不在于是否正史,并不能说明非正史的《汉晋春秋》就比正史的《三国志》更可信。许多人不认可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这段话另有充分理由,而并非拘泥于它不是正史。
首先,习凿齿在此问题上说话自相矛盾、前后矛盾。习凿齿在先前的著作《襄阳耆旧记》中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
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见《诸葛亮集》中华书局版216页)可是习先生晚年著《汉晋春秋》时,不加任何说明,却变成了“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 隆中被他一会儿说是“襄阳”,一会儿说是“南阳”,两相牴牾,这样的话自然不足凭信。
第二,隆中从来不曾属邓县。隆中在汉水以南,说它属“南阳之邓县”,与南阳郡和南郡在秦汉时划界不合。《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
初置南阳郡”下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晋书》地理志:“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太平寰宇记.邓州》(宋.乐史著)引《楚地记》:“汉江之北为南阳郡,汉江之南为南郡。
”都把南阳郡与南郡在襄阳附近的这一段的分界线说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这样的划界习凿齿也是承认的,他在《襄阳耆旧记》中同样明明白白地写道:“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当代《襄阳县志》也承认此划界,在邓城县历史沿革中写道:“邓县建于秦朝,以当地古邓国境而得名,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两汉时属荆州刺史部南阳郡。”诸多古籍中关于两汉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的成说与习凿齿“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实是龃龉不合,无法令人相信。
第三,谭先生说:“习凿齿是相当有名的学者,他又是襄阳人,去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隆中时不过百数十年”。谭先生的意思,他提供的“这么早的史料”,所以应该“可信”。
我也认为,习凿齿作为有史著传世的学者,对两郡界线当然心知肚明。但这并不代表他会依照事实说真话。其重要原因正与他“是襄阳人”有关系。这位被后世称为诸葛亮“异代相知”的习先生出于一种政治理念(希望权臣桓温之流像诸葛亮那样既是能臣又能作忠臣),他在对诸葛亮表现出极度景仰崇敬和大力歌颂褒扬的同时,还极力想将其拉到襄阳来以荣耀乡里,这种做法乃当时之风尚。
国际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指出:“东汉后半期,地方意识逐渐浮现……。
地方性的自我意识,也见之于州郡人士自我揄扬,对其他地域则叽嘲贬抑。这一类的文献,大多已佚失,只在史传中偶见篇名及片段,例如《冀州记》、《襄阳耆旧记》……”(见许倬云《万古江河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117页)。
许先生专门点到《襄阳耆旧记》并非偶然,说明习凿齿正是热衷此道之人。为了借诸葛亮之余晖以荣耀乡里,他在《汉晋春秋》谎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以求与《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的自述合榫,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习凿齿“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之说,只是他的私心愿想,而并非信史。当然,习凿齿对两晋间反复上演的权臣谋逆篡夺深恶痛绝、希望重建皇权正统秩序以维持政局稳定,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所以笔者对习先生的撒谎不想过于责备,认为他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给历史开了个玩笑,不应简单与一般的造假说谎赞同视之,但此语既出竟给后人造成一桩聚讼千年的公案,恐怕也是习主薄始料所未及的。
以上三点应能说明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的说法不足征信,谭先生“题词”前半部分根本不能让人信服。
再来分析“题词”的后半部分。
与前半不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是谭先生首创的论断。谭先生并没有作相应的慎密论证,而是含糊其词地解释说:“那么,什么时候隆中归属襄阳的呢?据我推断,应在北周时。因为邓县宋齐时犹存,至北周省。
邓县既省,其地很可能便就近并入襄阳。”其实,谭先生在这里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东汉时称邓县的这块地方,虽然“宋齐时犹存”,但旋即纳入北朝版图而处在西魏境内,并被西魏改属邓城郡,称安养县。就是说,西魏时已经没有了邓县。
到北周初,此地仍称安养县,只是于北周天和五年(公元570年)由属邓城郡改属襄州。王仲犖先生《北周地理志》载:“河南郡 治安养……安养 今湖北襄樊市北 西魏置 《元和郡县志》:西魏于此立安养县,属邓城郡,周天和五年,改属襄州。
”既然邓县在西魏时已经裁撤,到北周时根本无邓可省,谭先生“北周省邓县”就只能是错判了。这是其一;其二,此后“隆中遂属襄阳”也不对。根据王仲犖先生《北周地理志》,可以判断北周时隆中一带应该划入长湖郡的义安县或旱停县(义安县的可能大些),而绝对不会是襄阳县。
到隋时这两县都改入常平,仍然未归入襄阳县。(见王仲犖《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 474-475页)
综上所述,谭其骧先生的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所包含的三个要素:隆中东汉属“南阳郡邓县”、“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竟一无是处,全都站不住脚,谭先生匆忙间所作题词,实在是他晚年的学术败笔。
谭先生围绕隆中“题词”的情绪化言论有失大家风范
谭其骧先生的隆中“题词”虽只有35个字,却是迄今为止“襄阳说”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涉及面最宽的论述。习凿齿《汉晋春秋》最早说出“隆中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也只说有“亮家”,而谭先生直接认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
不仅如此,谭先生“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的论断此前也无人这样说过。众所周知,为景区题词,是有身份的人一种特有的发表见解或抒发胸臆的话语权,具宣示世人,留布久远之意。
如此重要的立论、如此庄重的形式,仅有这35字浓缩观点的“题词”是不够的,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详尽论述和翔实举证,以服世人。然而我们能见到的仅仅是《谭其骧论诸葛亮躬耕地》的报导(见丁宝斋《诸葛亮躬耕何处》第57-60页;另见《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第3-6页,署名金泰)。
1990年3月17日《文汇报》上刊登有谭其骧先生内容雷同的发言。这就是能够看到的谭先生围绕隆中“题词”的全部诠释了。
笔者反反复复、认认真真阅读了谭先生的这些“诠释”后,没有见到心平气和的论述,也没有见到翔实有力的举证,见到的倒是情绪化的的话语,含糊其词的推断和有失常态的迎合,还有以势压人、不容不同意见存在的粗暴态度,这大异于谭先生一贯的治学严谨、主张“知出乎争”的风格,实在有失大家风范。
对谭其骧先生的以上的“诠释”,笔者大惑不解之处起码有三:
笔者大惑不解处其一,谭先生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还是在襄阳的问题”,“向来没有疑义”,甚至直接说出“我希望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不要再争论下去了”。这就有一语定谳,堵住人口不许再发表不同观点之意,实与学术民主背道而驰。
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还是在襄阳的问题真的“向来没有疑义”吗?
事实并非如此。就在襄阳方面编印的《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中,简修炜教授的论文《诸葛亮躬耕地的定位要历史地全面考察》就指出:“然而,在诸葛亮十年躬耕地的定位问题上,存在着襄阳与南阳之争。
这一争辩,大概从元代就开始了。”其实,产生争辩远比元代更早。只是到了元明两代,产生了官方的正式意见,南阳卧龙岗遂有了敕修碑刻,这是有文献可考、有实物为凭的。不过颇有意思的是,诸葛亮躬耕地望虽然一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南阳襄阳之争,但在多数时间里,只是各说各话,鲜有直接交锋,南阳卧龙岗和襄阳古隆中作为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地可以说是并行于世,两地香火皆旺,前人分别留下大量凭吊诗文。
直到清季顾嘉蘅在南阳知府任上时,争论有升级势头,为止争息讼,这才引出他“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名联,是劝导各方识大体,显大量,重大节,薄争竞之意。可以说,如果“向来没有疑义”就不会有此楹联。
可是谭先生却无视这些事实,硬说什么:“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还是在襄阳的问题,有人说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好像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悬案没解决。我认为这是向来没有疑义的问题。只要学历史的,都会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历史上并没有悬案”。
好一个“只要学历史的,都会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历史上并没有悬案”,这样一来,史念海先生就不是学历史的了,黎东方先生也不是学历史的了,唐嘉宏先生、王子今先生等全都不是学历史的了,凡主张“南阳说”的统统不是学历史的了,连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简修炜教授虽然主张“襄阳说”,却认为“从元代就开始”“存在着襄阳与南阳之争”,他也不是学历史的了。
这叫什么话?忒霸道点了吧?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至今迄无定论,这是客观事实,熟视无睹不是科学态度。“南阳说”出自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巍巍五字,历千年而不凿,岂能一笔抹杀;“襄阳说”虽占上风,可漏洞百出,质疑声从末停息。
何况学则须疑,不疑不学,做学问就要在不疑处有疑,能在一般人认为没有疑义、没有悬案的地方发现问题,而在有疑问、有悬案的地方积极探索,这才是应有的进取精神。以为可以穷尽真理,甚至设置新的学术禁区,不准质疑,不准探索,扼制不同意见发表,绝对不是正确态度。
笔者大惑不解处其二,谭先生仓促间表态《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有差错”,“要修改”,身为主编的他却没有任何歉意和自我批评的表示,一句“参加编绘《图集》的人很多”,已经流露出诿过于人的意思,谭先生这样说既与事实不符,也于编德有亏。
据丁宝斋文章透露,他在访谈谭先生时反映:“1975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荆州刺史部中,今隆中一带明显地划在南郡辖区以内。”一方面“南阳说”者以此为据,“证明诸葛亮躬耕地不在今日的襄阳隆中,而在今南阳市内”;另一方面,“各地学者囿于谭其骧先生是当代权威的历史地理专家,均未发表意见。
因此,请谭先生本人就诸葛亮躬耕地和隆中辖属问题发表意见”。对此,谭先生当即表态:“参加编绘《图集》的人很多。
我郑重声明,《图集》东汉部分对此画得不太清楚,是有差错的,以后再版时要修改。”谭先生这段话颇值得玩味。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发轫于1955年,1986年告竣,历时31年,先后参与编绘工作的单位有十几个,人员逾百,其中不乏顶级专家。
中间曾于1974年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内部试行本,1982-1988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重大的集体劳动成果,襄樊当地人出于地方利益提出疑义,谭先生居然于仓促间贸然认错,承诺修改,这样做是很不严肃、很不严谨的。
特别是谭先生在此强调“参加编绘《图集》的人很多”,显然是表白身为主编的他并不知情或还没有注意到,这就有诿过于人的意思了。其实,只要认真思索一下,谭先生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笔者对此不能不产生几个疑问:
一是那么多专家历时那么久编绘,从内部发行到正式出版,要经过反复多次审核,特别是必须经过主编谭先生认可并签字才能付印,涉及到的《图集》东汉部分当然不会例外,然而谭先生与相关编绘人员此前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看出问题,非要等到相关利益方襄阳人找上门来即完成瞬间“顿悟”,而且谭先生一句“参加编绘《图集》的人很多”就把责任一推了之!
这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也根本不可能是这样。谭先生自己的文章《怀念吴晗同志》曾经把编图责任制说得明白:“吴晗同志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是编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我们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他(吴晗)也相信我对工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不止一次在会上当众郑重宣布:‘委员会不接受没有你(谭其骧)签字的图稿,所有图稿,最后都要由你主编审查通过后签字,才由委员会交付出版社。
集体搞的著作不赋于主编以裁决权是不行的,我们这套图必须认真实行主编负责制。你是主编,你得对每一幅图的内容的正确性负责。’”(见人民出版社谭其骧《长水集(续编)》505页《怀念吴晗同志》)话都说到这份上,谭先生居然还能在宣称《图集》出错的同时,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却用“参加编绘《图集》的人很多”来敷衍塞责,不禁令人齿冷。
二是负责东汉荆州刺史部编图的人员,也绝对不可能随意乱画,他们自然有其所本,多数史料、包括习凿齿的著作都承认两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原画法只是遵从成说,何错之有?
三是当初怎么画,应该是经过一定程序的,要修改,也应该通过一定的程序,主编如此仓促间就表态认错,就决定修改,类同儿戏,还有什么编绘规范可言?
四是谭先生对襄阳丁宝斋有刻意迎合之嫌,这种迎合已经到了有求必应,不顾事实的地步。《中国历史地图集》原来对东汉荆州刺史部的画法与谭先生早年著作是一致的。谭先生在《秦郡新考》一文后所附《秦郡图》的画法,南阳郡与南郡也是以汉水为界的(见谭其骧《长水集》(上)第12页)!
汉承秦制,多种古籍都有南阳郡与南郡之界“汉因之”的注脚。笔者觉得,谭先生的旧作也完全可能是东汉荆州刺史部这部分执笔者的重要根据。谭先生已仙逝多年,要不,当面点破这一点,岂不陷谭先生于尴尬的境地?
笔者大惑不解处其三,谭先生仅凭“据我推断,应在……很可能……”就匆忙作出结论,事后也没有发表相应的论证文章,这种轻率表态,拍脑袋作学术结论的方式实不足取。
从丁宝斋文章看,谭先生的“题词”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在临时动议下兴之所至信笔书就。特别是题词的后半:“北周省邓县 此后隆中遂属襄阳”,字是写出来了,到了说明时,表达得不流畅、不清楚。
丁宝斋记述谭先生的原话倒是颇有现场感的,谭先生说:“那么,什么时候隆中归属襄阳的呢?据我推断,应在北周时。因为邓县宋齐时犹存,至北周省。邓县既省,其地很可能便就近并入襄阳。
”这中间连连出现“据我推断,应在……很可能……”之类的模糊词语,含含糊糊,没有引证任何史料作支撑。历史地理是史学中一个高难度的分枝学科。难就难在古代史料匮乏且歧异迭出。“题词”涉及到的《三国志》、《北齐书》、《周书》都没有地理志,南北朝的这些乱世短命王国,版图不大,却为了打肿脸充胖子,猛增郡县数目,以至于被讥为“百户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文宣纪》)。
加之政权更迭频繁,政区废立随意,记载残缺错乱,一个时期某州统辖哪些郡,某郡统辖哪些县,某县变动中改隶哪个郡,古代地记本来就不完整,且多有歧异,很多地方的沿革变迁要说清楚非常不容易,有的恐怕最终也说不清了。
杨守敬批评洪齮孙《补梁疆域志》有“度属自我,割隶从心,惟务补亡,不思阙殆”之叽,而他自己在《北周疆域图》后所列的州郡县目,也被后人作了相同的叽评。杨守敬绝非等闲人物,他是我国清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
他主持编纂刊刻的《历代舆地图》,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史地图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被称为中国历史沿革地理的巨著。建国初,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由范文澜、吴晗担纲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 谭先生耗费半生精力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在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基础上进行的。
如此博学且专精的杨大师,在州郡县的割隶度属方面,仍有许多解决不当的问题。谭先生应人之请,仓促间凭想当然推出并无把握的论点,重蹈“度属自我,割隶从心”的覆辙,实在是值不得。何以如此,令人费解。
本文写到这里,蓦然间想到谭先生的高足葛剑雄教授有篇《老专家 请多自重》的文章 ,文中说:“这些年不少地方在争夺历史名人的祖籍、出生地、活动地、坟墓所在地时,少不了要请一些名气大、地位高的老专家到场‘考察论证’。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年代久远,是考察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而仅有的史料往往语焉不详,或者自相矛盾,甚至根本没有可靠的史料,只有民间口头传说,所以老专家纵有广博知识、高明见解,也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
”“老专家德高望重,本身就是学界泰斗、国之瑰宝。正因为如此,即使其中的个别现象也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即使偶然失察失言,也会产生严重后果。”葛教授的文章切中肯綮,入木三分。
有人可能以为我想藉此文责难谭先生,错了,此非笔者本意。因为我知道,谭先生绝对不是葛教授非议的那种“逢场作戏,随波逐流”的“老专家”。问题的根本原因也不在这些“老专家”身上,追根溯源,某些“论证活动”背后的组织者策划者即“有些个人或部门”才是源头,是他们兴风作浪,对“老专家”不吝使出花样百出的公关手段以达到他们的既定目的,而受累受损的还是“老专家”们。
葛教授对此弊端有极其深刻、直击要害的揭露:“现在有些个人或部门名义上重视老专家,实际上却是将老专家当枪使,……甚至不顾他们的健康状况,让他们参加力不能及的繁多活动。
更为恶劣的是,提供错误信息,或设下圈套,误导老专家,以便利用他们的名义和声望营私。”
试想谭其骧先生为隆中题词时已经年近八旬,1年半前的1988年7月28日,先生患脑血栓失去过知觉,用葛剑雄教授的话说“核磁共振检查证明死神的确曾经逼近过他”(见葛剑雄《看得见的沧桑》230页),襄樊方面又是作专访,又是请题词,又是邀讲话,如此地打扰劳烦谭先生。
我们从谭先生的当时讲话语气中不难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激动亢奋情绪,这绝对有损于老人的健康。事情过后仅仅3个月的1990年6月16日,谭先生再一次中风,医生诊断“病情严重”。 1991年10月谭先生继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有能够恢复”。10个月后,1992年8月28日,谭先生魂归道山。
笔者罗列谭先生1990年前后的健康状况,没有归罪谁、追究谁责任的意思。我只想问一句,难道组织策划活动的“有些个人或部门”的当事者就不该有点自责吗?不妨想一想,一位老人,又患过脑血栓,纵然是大师,思维能不受影响吗?拿着谭先生主编的《图集》要他表态,等同是“将军”,能不是一种压力和刺激吗?表了态还不够,进而还要留下文字证据(听上去很美的名义叫题词),这样的一系列做法,恕我直言,丝毫看不出对谭先生身体健康的爱护,也丝毫看不出对谭先生学术声誉的爱护。
千古江山,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谭先生仙逝不觉已经20多个春秋。笔者每次到隆中看到刻有先生“题词”的石碑,都不禁感慨交集。哲人其萎,生前偶而留下的学术败笔已经无法改写,而其曲解史实、误导游人的作用仍然在继续,这不是谭先生的光彩,也未必是隆中的幸运。